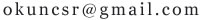什么是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是跟女权主义、妇女解放运动(女性运动)相联系的。
妇女解放运动到今天为止,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很早,大概是19世纪末左右,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是要求性别包括男女之间的平等,也就是两性的平等,当时也要求公民权、政治权利,反对贵族特权,强调男女在智力上和能力上是没有区别的。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要争取政治权利,往往被称作“女权运动”。
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一般地说,是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开始的。人们认为,最早也是起源于美国。这次运动一直持续到80年代。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的差别。把两性的差别实际上看成是在两性关系中,女性附属于男性的基础。要求各个领域对公众开放,等等。波伏娃的《第二性》即产生于这一时期。
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对于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兴起。因此,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流派。长久以来,在社会上是一个以男权意识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人们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形成的概念使得他们从男权的角度来描述这个世界,并且把这种描述混同于真理,就是说,这种描述是千真万确的,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对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提出了挑战。尽管流派众多,但基本点是争取两性平等,改变女性受歧视压迫的现状。
女性主义为何总和性相连
女性的歧视是全方位的。尽管如此性是比较突出的,带有性意味的歧视是占有中心地位的。也就是说,压迫越深反抗越强。女性对自身的反思恰恰从最激烈的地方表现是非常自然的。(引自《另类的尖叫》)
1、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渊源及主要观点
在女性主义三大主要派别长达百年的论争之后,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流派,这就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流派,有的理论家甚至将这一新流派的出现称为女性运动的“第三次浪潮”。(Coole, 184) 我想,其原因在于后现代女性主义颇具颠覆性,它不仅要颠覆男权主义秩序,而且要颠覆女性主义三大流派据以存在的基础。因
此,严格地说,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能算是与三大流派并列的第四大流派。
后现代女性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女性主义加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社会在西方逐渐成为现实之后,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现状肯定论、多元文化论以及生态主义等新思潮逐步进入了西方学术界主流。
从1960年代起,后现代理论在法国首先兴起。法国后结构主义派的主要人物有: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拉康(Jacques Lacan),利奥塔(Jean Francios Lyotard),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鲁兹(Gilles Deleuze),伽塔里(Felix Guattari),保吉拉(Jean Baudrillard)等。他们批判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语言、文化、主体概念,开创了后现代理论流派。相比之下,哈贝马斯派的批判理性还是以理性为基本原则,现代性概念还在使用。批判理论以“知识的生产”作为最主要的关注。后现代派则认为,启蒙主义已经终结,现代性要求新的科学形式和新的话语模式。
法国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有: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塞克瑟斯(Helene Cixous),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等。她们将后现代理论导向对男权制文化和生殖器中心话语的女性主义的批判。这一思潮从1968年开始出现在女性主义之中。从思想渊源看,英美女性主义一向重自由人文哲学;而法国女性主义则重后结构主义。前者与后者相比,是比较传统的和男性中心的批判理论和方法。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大多活跃于学术圈内,但她们也参与女性主义的政治运动。如果要追寻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渊源,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后现代主义大思想家福柯。每一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都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无论她们对他的思想是全盘接受,还是批判的接受。福柯是一位怀疑主义哲学大师,是怀疑主义哲学传统在20世纪的重要继承人。他主张检验知识变化的实践,而不是用标准的认识论方法去证明独一无二的理性或科学。他对现存一切秩序体制的确定性和稳固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我所分析的一切就是为了否定关于人类存在方式的普遍适用的必然性的观念。我的分析旨在揭示出现存制度的人为性质,揭示出我们还拥有多少自由的空间,还能对现存的一切做哪些改变。”(转引自Martin, 11) 此外,后现代主义大师和重要思想家拉康和德里达也受到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高度重视和大量引证。
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渊源及其主要观点做一概括,它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挑战关于解放和理性的宏大叙事,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 (grand theories)。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倾向来自后现代主义,高度概括地说,这一理论思潮的要点是反对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体系,主张只有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论才是有效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致力于批判所有那些博大宏伟和涵盖一切的现代理论,试图建立社区理论,即,将道德和政治观念建立在小范围的特殊社区的经验之上,否定因果关系与宏观社会概念。后现代理论超越意识,关注无意识和下意识的自我;关注矛盾、过程和变化;关注个人的肉体性质;拒绝男权的宏大叙事、普适性理论、客观性。有一种说法认为,“女人缺乏把握规模宏大的法则和原理的能力。”(Bacchi, 14) 对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应当对我们的社会合法性所由建立的所有法则和原理做重新的审视。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哲学建立在下列假设之一是:所谓“知识的普适性”是错误的概括。科学、宗教、法律的话语以及知识的生产都是局部的,只具有相对的价值。从启蒙思想开始,所有的宏大理论就都标榜其普遍性和性别中立的性质;那些强调两性差异的理论也自称是性别中立的。可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这些理论都是以男性为其标准的,完全忽视了女性的存在。例如在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上,认为前者是男人的天地、后者是女人的天地,这就是典型的男权制的政治思想。在政治领域完全没有女性的位置,没有女性的声音,也没有为女性留下任何空间。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解放中没有得到过什么益处,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话语,从洛克 (Locke) 到康德 (Kant),从来都没有把女性包括在内。
在西方进入后工业化社会 (丹尼·贝尔用语) 之后,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话语遭到怀疑,甚至连理论本身也遭到怀疑。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对性别、种族、阶级作宏观的分析,认为这些分类都过于概括了。由于每一个类别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这些分类都不再适用了。在她们看来,就连“女性”、“男权制”这类概念也都带有大成问题的本质主义色彩。
参考资料: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sex/1110349762_nvxingzhuyi/30.shtml
女性主义是跟女权主义、妇女解放运动(女性运动)相联系的。
妇女解放运动到今天为止,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很早,大概是19世纪末左右,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是要求性别包括男女之间的平等,也就是两性的平等,当时也要求公民权、政治权利,反对贵族特权,强调男女在智力上和能力上是没有区别的。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要争取政治权利,往往被称作“女权运动”。
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一般地说,是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开始的。人们认为,最早也是起源于美国。这次运动一直持续到80年代。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的差别。把两性的差别实际上看成是在两性关系中,女性附属于男性的基础。要求各个领域对公众开放,等等。波伏娃的《第二性》即产生于这一时期。
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对于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兴起。因此,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流派。长久以来,在社会上是一个以男权意识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人们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形成的概念使得他们从男权的角度来描述这个世界,并且把这种描述混同于真理,就是说,这种描述是千真万确的,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对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提出了挑战。尽管流派众多,但基本点是争取两性平等,改变女性受歧视压迫的现状。
女性主义为何总和性相连
女性的歧视是全方位的。尽管如此性是比较突出的,带有性意味的歧视是占有中心地位的。也就是说,压迫越深反抗越强。女性对自身的反思恰恰从最激烈的地方表现是非常自然的。(引自《另类的尖叫》)
1、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渊源及主要观点
在女性主义三大主要派别长达百年的论争之后,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流派,这就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流派,有的理论家甚至将这一新流派的出现称为女性运动的“第三次浪潮”。(Coole, 184) 我想,其原因在于后现代女性主义颇具颠覆性,它不仅要颠覆男权主义秩序,而且要颠覆女性主义三大流派据以存在的基础。因
此,严格地说,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能算是与三大流派并列的第四大流派。
后现代女性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女性主义加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社会在西方逐渐成为现实之后,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现状肯定论、多元文化论以及生态主义等新思潮逐步进入了西方学术界主流。
从1960年代起,后现代理论在法国首先兴起。法国后结构主义派的主要人物有: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拉康(Jacques Lacan),利奥塔(Jean Francios Lyotard),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鲁兹(Gilles Deleuze),伽塔里(Felix Guattari),保吉拉(Jean Baudrillard)等。他们批判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语言、文化、主体概念,开创了后现代理论流派。相比之下,哈贝马斯派的批判理性还是以理性为基本原则,现代性概念还在使用。批判理论以“知识的生产”作为最主要的关注。后现代派则认为,启蒙主义已经终结,现代性要求新的科学形式和新的话语模式。
法国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有: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塞克瑟斯(Helene Cixous),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等。她们将后现代理论导向对男权制文化和生殖器中心话语的女性主义的批判。这一思潮从1968年开始出现在女性主义之中。从思想渊源看,英美女性主义一向重自由人文哲学;而法国女性主义则重后结构主义。前者与后者相比,是比较传统的和男性中心的批判理论和方法。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大多活跃于学术圈内,但她们也参与女性主义的政治运动。如果要追寻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渊源,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后现代主义大思想家福柯。每一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都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无论她们对他的思想是全盘接受,还是批判的接受。福柯是一位怀疑主义哲学大师,是怀疑主义哲学传统在20世纪的重要继承人。他主张检验知识变化的实践,而不是用标准的认识论方法去证明独一无二的理性或科学。他对现存一切秩序体制的确定性和稳固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我所分析的一切就是为了否定关于人类存在方式的普遍适用的必然性的观念。我的分析旨在揭示出现存制度的人为性质,揭示出我们还拥有多少自由的空间,还能对现存的一切做哪些改变。”(转引自Martin, 11) 此外,后现代主义大师和重要思想家拉康和德里达也受到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高度重视和大量引证。
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渊源及其主要观点做一概括,它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挑战关于解放和理性的宏大叙事,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 (grand theories)。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倾向来自后现代主义,高度概括地说,这一理论思潮的要点是反对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体系,主张只有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论才是有效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致力于批判所有那些博大宏伟和涵盖一切的现代理论,试图建立社区理论,即,将道德和政治观念建立在小范围的特殊社区的经验之上,否定因果关系与宏观社会概念。后现代理论超越意识,关注无意识和下意识的自我;关注矛盾、过程和变化;关注个人的肉体性质;拒绝男权的宏大叙事、普适性理论、客观性。有一种说法认为,“女人缺乏把握规模宏大的法则和原理的能力。”(Bacchi, 14) 对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应当对我们的社会合法性所由建立的所有法则和原理做重新的审视。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哲学建立在下列假设之一是:所谓“知识的普适性”是错误的概括。科学、宗教、法律的话语以及知识的生产都是局部的,只具有相对的价值。从启蒙思想开始,所有的宏大理论就都标榜其普遍性和性别中立的性质;那些强调两性差异的理论也自称是性别中立的。可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这些理论都是以男性为其标准的,完全忽视了女性的存在。例如在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上,认为前者是男人的天地、后者是女人的天地,这就是典型的男权制的政治思想。在政治领域完全没有女性的位置,没有女性的声音,也没有为女性留下任何空间。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解放中没有得到过什么益处,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话语,从洛克 (Locke) 到康德 (Kant),从来都没有把女性包括在内。
在西方进入后工业化社会 (丹尼·贝尔用语) 之后,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话语遭到怀疑,甚至连理论本身也遭到怀疑。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对性别、种族、阶级作宏观的分析,认为这些分类都过于概括了。由于每一个类别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这些分类都不再适用了。在她们看来,就连“女性”、“男权制”这类概念也都带有大成问题的本质主义色彩。
参考资料: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sex/1110349762_nvxingzhuyi/30.shtml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6-05-25
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综观女性主义的理论,有些激烈如火,有些平静如水,有些主张做决死抗争,有些认可退让妥协,但是所有的女性主义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即女性主义思想泰斗波伏瓦所说的“第二性”。
全球女性主义是可能的吗?
—关于妇女史的书写
Claire G.Moses
今天,我将要讲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的历史以及女性主义在未来的可能性。当谈到女性主义的历史的时候,我将要利用我自己对美国和西欧女性主义历史的知识,但是,当我讲到未来的时候,我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女性主义是可能的吗?
让我首先解释一下:撰写女性主义历史的学者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境地——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女性主义”是不存在的;那么当我们要写女性主义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决定如何写呢?我们希望得到明确回答是武断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说这种回答是武断的?这是因为书写女性主义史的是我们当代的历史学家,而不是历史上的行动者,是我们这些当代历史学家在告诉人们谁是女性主义者什么是女性主义。说它是有意义的,是因为通过我们对历史上女性主义的建构,我们在确定着今天女性主义运动的含义。我将要解释的是:在传统的历史中,历史学家忽视了妇女在社会经济或者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但是在过去的25年中,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中的不少人研究女性主义,她们/他们根据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证明妇女几乎参与了男性所参加的所有历史活动;同时,历史学家也发现女性活动与男性活动的一些差别。
我将描述这些差别。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差别不是所有女性与男性的差别,例外总是存在的。对此,我也会简略地加以描述。首先,是关于鼓励妇女进行活动的条件。看来,至少在美国和西方,导致妇女进行行动有两条途径:第一,在教会或社区进行活动,妇女的参与是可以被接受的。第二条途径是参加解放运动,例如参加反对奴隶制的运动。看来,在这两种场合下,妇女开始理解到女性在她们的社会中被剥夺了权力。我的理解是,谈到娼妓问题的教会妇女怀着将这些妓女从她们的“罪”中拯救出来的愿望,但在拯救的过程中,教会妇女却发现后者没有维持生计的其它手段,因为其它的工作机会对妇女关上了大门。或者我们可以想象,反对奴隶制的妇女,当她们听着废奴主义领导人讲到自由的时候,她们会问自己:我们到底享受了多少自由?因为她们自己的这些领导人不听她们的意见,甚至不允许她们在公众场合谈论关于反对奴隶制的问题。
历史学家发现,妇女对于一些问题要比男性更加注意:首先是家庭问题(不管是保卫传统家庭,还是组织起来进行家庭变革,还是甚至抛弃传统的家庭);第二个关注点是:关于食物和住处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们都是可能关注的;第三个关注点是,妇女一直走在和平运动的前列。这一点可能是历史学家不同意的。但是,我想明确指出的是:妇女的确参加了许多男性参加的活动,例如,妇女参加了种族平等、经济平等运动和劳工运动等。
你们一定知道,妇女活动家既参加了右翼运动,也参加了进步运动,例如,一项近来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的德国,妇女的活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历史学家写了不少关于妇的组织方式的著作,这些组织活动与男性不同,这些活动开拓了在20世纪60年代末进步学生中非常流行的团体,并且还是非正式的团体活动的先河。她们也在只有妇女参加的团体中进行活动。不是因为谦虚,也许有人以为是这样;也不是因为男性将女性们从组织中排斥出去,而是因为她们发现在只有妇女参加的团体中,她们的组织才受到鼓励。
历史学家是不是把所有的妇女的活动都称之为“女性主义”呢?如果不是,什么样的行动在历史学家那里才称之为“女性主义”?或她们/他们把什么人称之为女性主义者?
一些历史学家说,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应该将过去那些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妇女们归为女权主义。然而,美国开始使用“女权主义”这一词汇是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而且只有那些在政府中任职或在大学中教书的职业妇女们才会使用这个词汇。我同意将这些妇女称为女权主义者,但我不认为只有那些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妇女才是活动家。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我这样的做法,而且已经使用了一种不同的历史策略,即,将今天的女权主义定义为是多阶级的、多种族的,并开始追溯这样的多元女权主义的历史根源。例如,历史学家们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欧美的那些争取妇女投票权、服装改革、已婚妇女的财产权的妇女们称为女权主义者。历史学家们也将第二国际中的女社会主义者们称为女权主义者,这些妇女组成自己的妇女组织,并努力扩大妇女的影响,但她们却不自称为女权主义者。这些女社会主义者们被今天的女权主义者赞誉为“母亲奠基者”。鉴于那些被不光彩地称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妇女权益的倡导者们,这些女社会主义者们只肯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
所以,历史学家们不但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些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妇女为女权主义者,而且也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那些争取妇女选举权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们称为女权主义。但即使这样,我仍然相信美国历史学家们对女权主义的定义太窄了,因为不管那些妇女们的奋斗目标如何,她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或中上阶级的白人。
但我不是只简单地批评美国历史家,因为我期望女权主义能有一个不同的过去。作为一名研究十九世纪法国女权主义的历史学家,我正在从事着我希望美国历史学家们所做的事。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女权主义”这个词就被广泛运用着。实际上,“广泛运用”是指那些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男男女女们,不但包括革命社会主义者,而且包括保皇党人。她们/他们对什么是女人味有着不同的观点,在奋斗目标上有着不同的排序,对于变革也有着不同的策略,但她们/他们都有着赋权妇女的共同渴望。
法国历史使我认识到,“女权主义”这一标签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有着不同的意义。
基于上述讨论,我提出如下结论:
在历史上有许多妇女活动家们,我们这些历史学家从中拿出或挑选出一部分,然后称这些提倡妇女权利的男男女女们为女权主义者。所以,正是我们历史学家们,而不是别人在构建着女权主义的含义。
例如,在书写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历史时,我们只看到了中产阶级的白人妇女,但请记住:这些妇女甚至并不知道有“女权主义”这一词汇。所以,是我们――历史学家们构建了“女权主义”的狭窄含义。在奴隶解放后,许多黑人妇女组成了妇女俱乐部来争取黑人妇女、黑人男人和所有女人,包括白人妇女和黑人妇女的权利;我们现在知道,与男人们一道分享权力的美国犹瑞克印第安部落的妇女们在十九世纪中期,经常与倡导白人选举权的活动家们相遇,而且这些妇女显然对后者产生了影响。如果我们能将这些黑人与印第安妇女们包容进来,“女权主义”将会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
我自己对女权主义的定义是很宽泛的:它既包括妇女,也包括男人,只要这些人:1)将性视为是体现社会政治地位权力的一个范畴;2)认为妇女是社会政治地位权力较低的一个群体;3)认为妇女们的被剥夺权力是能攻克的而且是应该被攻克的。
我的上面所述的要点在于:为什么我会花时间讨论历史学家们定义“女权主义”的不同方式?为什么历史家们所下定义的武断之处会引起我的注意?为什么我会在我研究法国历史的基础之上,提出,女权主义应该被广义地构建?
这些将我带到了另一个问题:全球女权主义运动和将这种运动命名为“女权主义”的可能性。全球女权主义存在吗?这样的命名有意义吗?
在国际会议中,不管何时何地,只要倡导赋权于妇女的人们聚在一起,这个问题就会浮现出来。正是在这些会议中,越来越多的妇女们开始自称为女权主义者。但与此同时,许多妇女,事实上是大多数妇女,都回避女权主义这个称呼。在美国学生中,许多妇女权利的倡导者们,甚至是那些进步的学生们、那些主修妇女研究的学生们,都不愿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学生越来越少了,即使她们/他们强烈赞同男女平等。这种现象的原因有许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必然是因为美国电影电视将女权主义者们歪曲为丑陋的、无情的、憎恨男人的、荒谬的和歇斯底里的。而且,这些媒体形象还在全世界流传。
但为 什么北美和欧洲以外的那些活动家们,甚至是进步的活动家们也否定女权主义,这里还存在着其它原因。对这些活动家而言,“女权主义”被视为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女权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相联系使得这一词汇在分析欧美以外的妇女经验时没什么用处。我曾听到,在这些活动家中,“女权主义”被漫画化为一场将所有男人都设为敌人的性/政治战争,并且强迫妇女们在为妇女平等而奋斗和争取国家解放之间做出抉择。这样的说法置女权主义历史于不顾。因为女权主义历史常常是团结的历史,融民族解放、社会公平和反种族斗争于一体,并且和这些运动的男性领导人们并肩作战。来自于欧洲和北美的女权主义者们已经将她们/他们的女权主义带给了非洲的黑人斗争;日本妇女抗议到朝鲜的“性旅游”,因为这种活动是两国性别歧视主义的象征,也是经常将妇女当作人质的帝国主义关系的继续。
女权主义的历史被忽视了,被视为是仅仅产生于西方社会的近期现象。然而,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们已经表明,女权主义并不是西方强加于亚洲、非洲、中东妇女的,而是这些国家的历史环境产生了重要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变化,从而影响了这些国家中的妇女。在十八世纪,中国爆发了关于妇女受教育权的争论;在十九世纪早期的印度、十九世纪晚期的埃及和二十世纪的日本,都爆发了妇女社会解放的运动。但是,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在那么多非欧洲国家四处开花的那段时期“被从历史中隐藏起来了”。
我再次发问:争取妇女平等的斗争的确可以在多种其它称谓下持续进行,那么,我们对自己的称谓方式真的重要吗?我的回答是:重要。它重要,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很重要;那些歪曲我们历史的人并没有被妇女平等而触动;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妇女们既因为置身于全球运动而增强力量,也在以她们各自的命名方式反思着她们对全球运动的使命。换言之,我们对自己的称谓方式重要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都参加了赋权于妇女的共同任务。
但是,如果我们想取得国际妇女运动的胜利,我们就必须从女权主义的历史学习:1、对不同的人们而言,“女权主义”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点,具有不同的意义;2、我们必须允许不同的意义出现,以满足不同语境下妇女的不同需要和目标次序;3、女权主义绝不能认为性别歧视主义是妇女生活中唯一的压迫力量。既然阶级关系、结构性的贫困、文盲、饥饿和帝国主义都在妇女所遭受的压迫中起了重要作用,女权主义就必须是包容的、流动的、愿意接受矛盾的。所以,如果我们学到了这些历史教训,那么我们将大大受益。尽管我们的策略、我们的目标次序和我们的观点可能不同,但我们知道,我们彼此支持着,我们支持着妇女,我们支持着妇女的赋权。
注:本文系克莱尔·摩赛斯(Claire G.Moses,美国马里兰大学妇女研究系主任、教授,历史系联席教授,《女性主义研究》编辑)去年十一月12日在天津师范大学的讲座,原文为英文.
2004.02.28
全球女性主义是可能的吗?
—关于妇女史的书写
Claire G.Moses
今天,我将要讲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的历史以及女性主义在未来的可能性。当谈到女性主义的历史的时候,我将要利用我自己对美国和西欧女性主义历史的知识,但是,当我讲到未来的时候,我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女性主义是可能的吗?
让我首先解释一下:撰写女性主义历史的学者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境地——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女性主义”是不存在的;那么当我们要写女性主义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决定如何写呢?我们希望得到明确回答是武断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说这种回答是武断的?这是因为书写女性主义史的是我们当代的历史学家,而不是历史上的行动者,是我们这些当代历史学家在告诉人们谁是女性主义者什么是女性主义。说它是有意义的,是因为通过我们对历史上女性主义的建构,我们在确定着今天女性主义运动的含义。我将要解释的是:在传统的历史中,历史学家忽视了妇女在社会经济或者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但是在过去的25年中,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中的不少人研究女性主义,她们/他们根据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证明妇女几乎参与了男性所参加的所有历史活动;同时,历史学家也发现女性活动与男性活动的一些差别。
我将描述这些差别。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差别不是所有女性与男性的差别,例外总是存在的。对此,我也会简略地加以描述。首先,是关于鼓励妇女进行活动的条件。看来,至少在美国和西方,导致妇女进行行动有两条途径:第一,在教会或社区进行活动,妇女的参与是可以被接受的。第二条途径是参加解放运动,例如参加反对奴隶制的运动。看来,在这两种场合下,妇女开始理解到女性在她们的社会中被剥夺了权力。我的理解是,谈到娼妓问题的教会妇女怀着将这些妓女从她们的“罪”中拯救出来的愿望,但在拯救的过程中,教会妇女却发现后者没有维持生计的其它手段,因为其它的工作机会对妇女关上了大门。或者我们可以想象,反对奴隶制的妇女,当她们听着废奴主义领导人讲到自由的时候,她们会问自己:我们到底享受了多少自由?因为她们自己的这些领导人不听她们的意见,甚至不允许她们在公众场合谈论关于反对奴隶制的问题。
历史学家发现,妇女对于一些问题要比男性更加注意:首先是家庭问题(不管是保卫传统家庭,还是组织起来进行家庭变革,还是甚至抛弃传统的家庭);第二个关注点是:关于食物和住处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们都是可能关注的;第三个关注点是,妇女一直走在和平运动的前列。这一点可能是历史学家不同意的。但是,我想明确指出的是:妇女的确参加了许多男性参加的活动,例如,妇女参加了种族平等、经济平等运动和劳工运动等。
你们一定知道,妇女活动家既参加了右翼运动,也参加了进步运动,例如,一项近来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的德国,妇女的活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历史学家写了不少关于妇的组织方式的著作,这些组织活动与男性不同,这些活动开拓了在20世纪60年代末进步学生中非常流行的团体,并且还是非正式的团体活动的先河。她们也在只有妇女参加的团体中进行活动。不是因为谦虚,也许有人以为是这样;也不是因为男性将女性们从组织中排斥出去,而是因为她们发现在只有妇女参加的团体中,她们的组织才受到鼓励。
历史学家是不是把所有的妇女的活动都称之为“女性主义”呢?如果不是,什么样的行动在历史学家那里才称之为“女性主义”?或她们/他们把什么人称之为女性主义者?
一些历史学家说,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应该将过去那些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妇女们归为女权主义。然而,美国开始使用“女权主义”这一词汇是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而且只有那些在政府中任职或在大学中教书的职业妇女们才会使用这个词汇。我同意将这些妇女称为女权主义者,但我不认为只有那些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妇女才是活动家。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我这样的做法,而且已经使用了一种不同的历史策略,即,将今天的女权主义定义为是多阶级的、多种族的,并开始追溯这样的多元女权主义的历史根源。例如,历史学家们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欧美的那些争取妇女投票权、服装改革、已婚妇女的财产权的妇女们称为女权主义者。历史学家们也将第二国际中的女社会主义者们称为女权主义者,这些妇女组成自己的妇女组织,并努力扩大妇女的影响,但她们却不自称为女权主义者。这些女社会主义者们被今天的女权主义者赞誉为“母亲奠基者”。鉴于那些被不光彩地称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妇女权益的倡导者们,这些女社会主义者们只肯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
所以,历史学家们不但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些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妇女为女权主义者,而且也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那些争取妇女选举权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们称为女权主义。但即使这样,我仍然相信美国历史学家们对女权主义的定义太窄了,因为不管那些妇女们的奋斗目标如何,她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或中上阶级的白人。
但我不是只简单地批评美国历史家,因为我期望女权主义能有一个不同的过去。作为一名研究十九世纪法国女权主义的历史学家,我正在从事着我希望美国历史学家们所做的事。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女权主义”这个词就被广泛运用着。实际上,“广泛运用”是指那些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男男女女们,不但包括革命社会主义者,而且包括保皇党人。她们/他们对什么是女人味有着不同的观点,在奋斗目标上有着不同的排序,对于变革也有着不同的策略,但她们/他们都有着赋权妇女的共同渴望。
法国历史使我认识到,“女权主义”这一标签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有着不同的意义。
基于上述讨论,我提出如下结论:
在历史上有许多妇女活动家们,我们这些历史学家从中拿出或挑选出一部分,然后称这些提倡妇女权利的男男女女们为女权主义者。所以,正是我们历史学家们,而不是别人在构建着女权主义的含义。
例如,在书写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历史时,我们只看到了中产阶级的白人妇女,但请记住:这些妇女甚至并不知道有“女权主义”这一词汇。所以,是我们――历史学家们构建了“女权主义”的狭窄含义。在奴隶解放后,许多黑人妇女组成了妇女俱乐部来争取黑人妇女、黑人男人和所有女人,包括白人妇女和黑人妇女的权利;我们现在知道,与男人们一道分享权力的美国犹瑞克印第安部落的妇女们在十九世纪中期,经常与倡导白人选举权的活动家们相遇,而且这些妇女显然对后者产生了影响。如果我们能将这些黑人与印第安妇女们包容进来,“女权主义”将会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
我自己对女权主义的定义是很宽泛的:它既包括妇女,也包括男人,只要这些人:1)将性视为是体现社会政治地位权力的一个范畴;2)认为妇女是社会政治地位权力较低的一个群体;3)认为妇女们的被剥夺权力是能攻克的而且是应该被攻克的。
我的上面所述的要点在于:为什么我会花时间讨论历史学家们定义“女权主义”的不同方式?为什么历史家们所下定义的武断之处会引起我的注意?为什么我会在我研究法国历史的基础之上,提出,女权主义应该被广义地构建?
这些将我带到了另一个问题:全球女权主义运动和将这种运动命名为“女权主义”的可能性。全球女权主义存在吗?这样的命名有意义吗?
在国际会议中,不管何时何地,只要倡导赋权于妇女的人们聚在一起,这个问题就会浮现出来。正是在这些会议中,越来越多的妇女们开始自称为女权主义者。但与此同时,许多妇女,事实上是大多数妇女,都回避女权主义这个称呼。在美国学生中,许多妇女权利的倡导者们,甚至是那些进步的学生们、那些主修妇女研究的学生们,都不愿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学生越来越少了,即使她们/他们强烈赞同男女平等。这种现象的原因有许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必然是因为美国电影电视将女权主义者们歪曲为丑陋的、无情的、憎恨男人的、荒谬的和歇斯底里的。而且,这些媒体形象还在全世界流传。
但为 什么北美和欧洲以外的那些活动家们,甚至是进步的活动家们也否定女权主义,这里还存在着其它原因。对这些活动家而言,“女权主义”被视为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女权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相联系使得这一词汇在分析欧美以外的妇女经验时没什么用处。我曾听到,在这些活动家中,“女权主义”被漫画化为一场将所有男人都设为敌人的性/政治战争,并且强迫妇女们在为妇女平等而奋斗和争取国家解放之间做出抉择。这样的说法置女权主义历史于不顾。因为女权主义历史常常是团结的历史,融民族解放、社会公平和反种族斗争于一体,并且和这些运动的男性领导人们并肩作战。来自于欧洲和北美的女权主义者们已经将她们/他们的女权主义带给了非洲的黑人斗争;日本妇女抗议到朝鲜的“性旅游”,因为这种活动是两国性别歧视主义的象征,也是经常将妇女当作人质的帝国主义关系的继续。
女权主义的历史被忽视了,被视为是仅仅产生于西方社会的近期现象。然而,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们已经表明,女权主义并不是西方强加于亚洲、非洲、中东妇女的,而是这些国家的历史环境产生了重要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变化,从而影响了这些国家中的妇女。在十八世纪,中国爆发了关于妇女受教育权的争论;在十九世纪早期的印度、十九世纪晚期的埃及和二十世纪的日本,都爆发了妇女社会解放的运动。但是,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在那么多非欧洲国家四处开花的那段时期“被从历史中隐藏起来了”。
我再次发问:争取妇女平等的斗争的确可以在多种其它称谓下持续进行,那么,我们对自己的称谓方式真的重要吗?我的回答是:重要。它重要,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很重要;那些歪曲我们历史的人并没有被妇女平等而触动;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妇女们既因为置身于全球运动而增强力量,也在以她们各自的命名方式反思着她们对全球运动的使命。换言之,我们对自己的称谓方式重要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都参加了赋权于妇女的共同任务。
但是,如果我们想取得国际妇女运动的胜利,我们就必须从女权主义的历史学习:1、对不同的人们而言,“女权主义”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点,具有不同的意义;2、我们必须允许不同的意义出现,以满足不同语境下妇女的不同需要和目标次序;3、女权主义绝不能认为性别歧视主义是妇女生活中唯一的压迫力量。既然阶级关系、结构性的贫困、文盲、饥饿和帝国主义都在妇女所遭受的压迫中起了重要作用,女权主义就必须是包容的、流动的、愿意接受矛盾的。所以,如果我们学到了这些历史教训,那么我们将大大受益。尽管我们的策略、我们的目标次序和我们的观点可能不同,但我们知道,我们彼此支持着,我们支持着妇女,我们支持着妇女的赋权。
注:本文系克莱尔·摩赛斯(Claire G.Moses,美国马里兰大学妇女研究系主任、教授,历史系联席教授,《女性主义研究》编辑)去年十一月12日在天津师范大学的讲座,原文为英文.
2004.02.28
参考资料:http://people.ku.edu/~yjli/gf/idea/feminism/0moses2.htm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