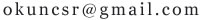1.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位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的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他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人们仍然在这个老人的诞辰纪念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这位作家。并且在纪念的同时,我们会提出很多疑问:为什么这样一位在作品中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悦,如此热爱生活,懂得幽默的老人,会在他遭难的那一天孤独绝望的走去。
我也是带着这样一个疑问,在十几年前开始追踪采访、调查、研究老舍之死这样一个沉重而有文化思想和意韵内涵的话题。我开始的想法是像一个案件调查者一样,通过追踪线索把那个历史的场景清晰地再现出来。想法好像是很简单的,只想在对受访者的不断追踪挖掘中,可能把那个历史现场还原。当时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采访的深入和自己理论的提升,我对历史的信任度和这种提升成反比。我发现当初的那个想法太单纯也太脆弱,脆弱的如同一张纸,一捅就破了。那么多受访者向我叙述的当天的历史场景我根本无法还原。我被历史搞糊涂了,面对着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冲突的历史叙述,那一天的情形好像更加支离破碎,无法将它建立起来,种种的细节无法将它统一。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老舍先生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文联被揪出来,紧接着在孔庙被批斗,回到文联又被批斗,遭受了三场批斗。在这样的批斗之后,老舍先生在第二天离家出走了。他到底是在第二天就投湖自杀了,还是在第三天投湖自杀了?时间上就有了不一样。我们姑且称作1966年8月23日那天发生的事件叫“八二三事件”,老舍先生在“八二三”那一天到底是上午来的、中午来的还是下午来的?说法各异。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说法各异。他拄没拄拐杖,哪天离家出走的?不知道。有疑点。他被打捞上来时,湖面上是不是漂满了碎纸片?不知道。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有的人特别希望有。这都是“八二三”这个历史事件带给我们的历史迷团。
作为一个采访人,作为一个追踪者,我理所当然地充满了敬意和善意去对待那些受访者。我觉得他们应该说的是实话,作为一个历史的叙述者,他们有说出他们见证的历史的真实的权利。但有可能他们在叙说历史时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间。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把他们所叙述的历史几乎一字不差的记录下来,同时对他们所做的历史的叙述作出一个自己的判断和反思。但我没有能力,没有权利,不能,不敢,也不会去说任何一个历史的叙述人和见证者所说的是谎话和不实的。我越来越觉得我扮演的是一个史官的角色,我得将我所采访的对象对历史的陈述如实地记录下来。至于他是不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是不是历史本身,我可以存疑。但我在记录历史时,必须本着一个记录者的史德如实地记录下来。我的头脑中会时刻想象一个话题:既然是某一个历史现场的见证人,他说的是不是就应该完全是真实的,不会出错?这个行为本身,严格来讲,从学术上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
现在好像口述历史变得很热,这个新东西也被炒得很热,目前在国内也很热。什么叫口述历史?这个概念是二战以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教授肯特·内文思提出的这么一个概念叫口述历史oral history。其实仔细想一想,在出现这个概念之前,口述历史的历史大概已经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在我们形成所谓的文字历史记载之前,很多历史都是口口相传的,都是由人们口述而形成的。比如像《史记》这样的历史书,关于五帝三皇呀,没有文字记载,就是司马迁收集了各种各样民间流行的传说,才记录下来这些史话。还有包括我们熟悉的,比如说鸿门宴,鸿门宴上的情景,就是司马迁描述的这个情景和当时实际鸿门宴的情景一样吗?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能相信,或者说我们愿意相信司马迁的文学描述,春秋笔法,描述的鸿门宴是真实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一幕:刘邦怎样、项羽怎样、樊郐怎样。所以,胡适先生对《史记》的一个看法就是,如果严格地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史记》就是一本历史小说,它带有很大的文学色彩。
其实这点很容易想通。比如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就是这个道理。任何历史都是文字写成的,任何历史都脱不了文学的笔法,文字的笔法。历史记载文字是个载体,它是不是真实的,能不能还原历史,这个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所在。我有一个学者朋友叫丁东。他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挺漂亮,他说“历史是一只巨大的黑箱,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黑箱的一隅”。我想说的是,我们如果能把黑箱中的那一隅给看清楚也已经相当不错了。有多少历史中的人与事,我们根本不清楚、不了解它到底怎么发生的。
我做老舍之死调查研究这个事,也想通过这个个案、这个事情本身,使口述历史的田野作业的行为在口述历史的理论上,有一些实际的意义,给人们提供一个历史线索,就是怎样认识历史,历史可能有巨大真空,有很多历史的本身是无法还原的。很多情形下我们所见到的历史可能是被人们重写过的,重塑过的。就是说,某一个事,它在历史上可能发生过,但你赋予它怎样的历史意义,有什么样的历史生命,是当代的历史学家当代的学者所做的。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才有这个话题。老说历史是当代史,历史是当代人写的历史,甚至说历史是史学家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历史学家写出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不一样。这也是很长时间来学术界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也是我们每个人,如果对历史还有兴趣还有思想的话,也应该不断地做这样一个思考:历史是什么?历史代表什么?我们相信历史吗?真实的历史什么样?我们能接近它吗?我们能还原历史吗?
拿老舍之死的叙述者来说,给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我遇到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这个例子的出现非常有趣,是大家想都想不到的。当我找到第一个自称是老舍尸体打捞者时,我欣喜若狂。我觉得终于可以把老舍之死打捞的那个现场还原了。他说的不会错,应该是真的,因为他有旁证来证明他为什么会在那个现场,为什么打捞的这个人是老舍。都说的有鼻子有眼,完全可以清晰逼真地再现现场每一个细节。
但紧接着,在我这篇访谈发表之后,看到这篇访谈的读者当中出现了第二位和第三位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有三位,而且这三个人互不相识,有两位是相识的。有意思的是,三个互不相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上了同一个人。如果说他们当中有真实的,只能有一个人真实,不可能三个人都真实。因为如果三个人都真实,那就等于那一天打捞起了三个老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三个都不真实,他们三个人捞的都不是老舍。作为一个记录历史的人,我必须把三个人所叙述的历史如实地只字不动地完全呈现在历史桌案上,作为历史的原始素材。对于他们说的对错、真伪,完全留给我们每一个人在了解这段历史后,在自己头脑中甄别判断。因为我不能在采访每一个人时做出主观判断,并且按我自己的主观取舍来说谁对谁错。这是违反史德,也是不符合口述历史理论上的做法的。
这个极端的例子提供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上的话题,就是口述史可以相信吗?所以,学术上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其实历史在它发生的一瞬间就已经过去了,无法再还原,历史在发生的一瞬间就不存在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永远不可能与见证人和叙述者的口吻相一致。有一位美国的口述史学家,在给学生们上口述史学课时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好像是在第一堂课开课之前,老师在讲台上什么话也不说,学生坐在底下很安静。进来了一个学生,是他找来的,他也不做介绍,学生就站在一边。大约站了五分钟,他让学生出去了。然后开始讲课,讲课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学生,刚才那个人大家给我描述一下。长什么样?头发是长是短?带眼镜吗?穿什么衣服?打领带吗?什么花纹?等等。
这个实验很有趣,班里的学生对这个人的描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就是刚刚发生的事,说法已经不统一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所有在场的人都说,“是我亲眼见的,肯定是真的”。为什么出现摄象机后,对口述历史的记录变的更科学了,也在这儿。比如说,我今天在这儿讲的,如果没有摄象机、录音机,大家走出门之后,你们再说傅光明讲什么时肯定不一样。大家容易对我的穿着进行描述,因为很简单。如果问讲的什么话,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机器的记录,我们可能无法还原。所以,严格地说就是,发生的那个历史无法还原。
用美国历史学家这个例子来说明太平湖的三位打捞者对这个事件的描述也是这样。三个人都说“是我亲眼见的,确实是真的”。是什么时间或是怎么接到的通知;怎么到现场;怎么处理的现场;并且还能提供旁证说,为什么我认为的这个人肯定是老舍。三个人的证据是不同的:有的人说在水中发现了老舍的一捆还没有完全湿掉的手稿,手稿上写着老舍的名字;有的说在岸边遗物当中有一张名片,名片上赫然印着老舍两字;还有一个人说,我打捞的时候,有我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生前与老舍认得,认出这是老舍。
你们看,三个人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捞上的是老舍,三个老舍。这个就让我困惑,让我疑惑。当然,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还原三个现场。因为确实不可能有三个老舍存在,只有一个。这个是由口述历史的叙述人提供的证言给口述历史理论上提出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人们对口述历史困惑的一点,也就是说,我们愿意相信口述者说的是真的这种愿望,比如说我们想要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一件事,我们特希望找到一个现场的见证人,他所描述的一定是真的。我想通过这样的调查在这一点上提供给大家一个什么信息呢。当你在面对约定俗成的某些历史的人或物时,脑子里要打一个问号,要反思这是历史的叙述者口述者他嘴里说的,可能与历史的原始记录、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一样的。探讨是谁打捞的老舍可能并没有太实际的意义,但理论上有价值。
在这背后,我们要继续提出疑问了:老舍先生作为人民艺术家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投水而死?投水为什么会在太平湖而死?这是我们应该思索在他死亡背后的所在。这么一个人民艺术家消失得无声无息,瞬间就跌入历史的黑箱,没有人知道在临死前他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巨大苦痛。在他投水之前,不管是有一天一夜,还是别的叙述者所说的时间很短,能肯定的是,他坐在湖边,面对太平湖静静的水面时,他在思考。
他在作品中有这样的描述。《老张的哲学》里写26岁的李静在死前有一段伏笔说,“自杀者面对湖水可能哭也可能笑,有时也会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而这自问自答的结果就使他坚定了死亡的决心。”我想,作为写家的老舍,在死亡前的那一刻,他肯定想了很多很多。他怎么想的,这只有让九泉之下的老舍给我们叙述了,这是无法还原的。同时,这给我们留下一个巨大的艺术想象的空间。老舍之死这个历史事件,在发生多年之后,人们开始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老舍时,最有意思的一点是,把老舍之死改编成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有书、话剧还有歌剧。它带来了很多东西,留下了很多空间,有历史的,有艺术的。
艺术家可以根据这个历史空间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去填补很多东西。比如像苏叔阳先生那个老舍之死的话剧,就是让老舍在冥界与舒乙对话。他以自己作家的思想来推测老舍在面对太平湖时想了什么,思考了什么。这是作家做的,也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也就是说,今天在想这件事时,你还得不断地自问,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老舍的读者,如果你是一个对这件事感兴趣并想从中得到一些启示的读者,你应该想一想,这样一个作家在临死前想了些什么,他可能会想什么,他想的与自己的出身成长,与作品中的人物安排以及作品中的思想等等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这其实也是我研究老舍之死的一个初衷,也是我的一份答案。我的答案不是准确的,只是对一个个体、一个个案的思考。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答案。老舍之死其实在不经意间已成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你在读了老舍之死访谈录的时候,在看了这些证言的时候,往往会有这样的感觉:历史可能是按照今天人们的想象从新编排、过滤的重塑的历史。这件事不在于老舍之死的那个现场是否能够还原,而在于我们怎样把我们今天对老舍之死的认识附到上面,赋予他活生生的历史生命。这是我们今天的人所应做的,也是后人所应做的。因为他带给我们太沉重的思想话题,如果对于这个话题没有足够深刻认识的话,我们有可能重蹈覆辙。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等等。口号容易提出来,口号之后要做什么,怎么做,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这样的思考,十几年当中不断地寻找挖掘历史的证人,虽然开始的时候我抱着一种强烈的心态,我找的每一个人肯定是真的,现在已不在乎找的人是不是真的,只要他说当天他在现场我就去找他,看他怎么说,如实记录下来,更多地更丰富地提供细节。因为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认识已经不再停留在既定的对历史文化的诠释上,还应该更多地关注历史所呈现出的多面性、复杂性,以及历史发生的过程性。虽然细节不是历史的全部,但没有细节历史是建立不起来的,是不活的、不立体的。
比如,我们现在想某些历史事件的时候,都是由种种细节把历史事件具体化了。我们可能对五六十年代的影片《甲午海战》印象非常深。一曲凝重悲怆的爱国主义悲歌。对邓世昌我们是那么的难忘。但是随着历史细节的浮出水面,随着历史档案的精细揭秘,随着我们对历史深入的了解,你会发现《甲午海战》是艺术的历史,是艺术的真实,它可能不是历史本身。央视前不久播了两个很好的片子,一个叫《庚子国变》一个叫《北洋水师》。就是用真正的历史档案、历史文献,用记录片的手段把当时的情景再现出来。
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看到电影里刘步蟾是海战时贪生怕死的一个副将。而真正的历史,恰恰是丁汝昌中炮后,刘步蟾担当起了指挥。这和历史差别极大。从艺术上讲,《甲午海战》是成功的,它带给我们的视觉的冲击、场面的悲怆都是难忘的。但它是艺术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艺术可以利用真正的历史留下的空间进行艺术的再造,但我们头脑中一定要清醒,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影视中所展现的历史,可能仅仅是艺术而不是真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是史学家的天敌。他可能设下了种种圈套,包括我们现在学习历史,我们接受的可能是戏说的历史给我们陈述的历史细节。今天我们的中小学生爱看的《康熙微服私访》、《雍正大帝》都是戏说历史。但学生们津津乐道地说那个雍正和乾隆那时什么什么事,好像影视剧里的事真是历史发生时的样子。这和历史有天壤之别。
我们现在来思考老舍先生为什么会死。关于老舍之死大体上有这样三种认识:一种认为老舍先生的死可以与屈原和田横五百壮士相提并论,是舍生取义的,是抗争的,表现出一种拼死的不屈的骨气。这可以简称为“抗争说”。还有一种说,老舍先生死因为他绝望,他在建国后一直很顺。很多人说,老舍先生一直开顺风船。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不断有创作,还有《茶馆》这样的创作高峰。因为他很顺,所以当文革来临时,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暴力的侮辱,老舍先生的心灵是脆弱的,选择了去死。还有一种认为,懂得幽默的老舍何不在那时幽默一下,就可以躲过这一劫了。
人们提出了一个假设,假如那天老舍不去文联就不会碰上那场批斗,没有那场批斗,没有挨那顿打,老舍先生心灵和精神没有遭受屈辱的创伤,他可能就不会死了。首先,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如果我们真的按照这个假设进行历史还原的话,如果老舍先生不去,是不是会不死?我觉得难。就文革的发生来说,有它历史偶然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历史的必然,偶然和必然交织在一起。作为作家的老舍,是一个政治上的门外汉,不懂政治。在他几乎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惨烈的血腥的运动批判、侮辱、毒打,是这样一位老人,以写作为生的作家无法承受的。老舍先生的死,我认为是一个必然,偶然中有它的必然。如果“八二三”躲过去了,后面还会有“九二三”“十二三”。他躲不过去,老舍在文革中是注定要死的。
老舍先生为什么要选择太平湖呢?太平湖东边离他家更近的有什刹海、后海、积水潭。这里有没有他刻意的选择?选择他死亡的归宿?我想,作为一个大作家的老舍来说,他有他的第六感,把自己的归宿刻意的选在了太平湖。可以提出一种自己的思索,把这种思索当作证据,然后与选择这个归宿的地点联系在一起。
老舍生前写了无数作品,而他大多数优秀作品的故事的发生,几乎都是在他祖上正红旗下的属地,就是北京城的西北。《四世同堂》故事的发生,就在老舍先生的出生地,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胡同。他出生在那个地方,青少年成长在那个地方,他所接受的私塾教育,以及他后来上缸瓦市教堂,作品中描述的许多人和事物以及许多情景的发生,大多数都是在那个地方。他对于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青少年时代的地方,对自己真实的故乡,精神的故乡,心灵的故乡,再熟悉不过了。
有一个现象非常有趣,这当然不单单是对老舍一个作家来说的。我们看老舍写北京的作品,除了他晚年的一部《正红旗下》,其他那几部非常棒的作品,《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老张的哲学》,写北京的都不是在北京写的,都是在北京之外写的,或者伦敦,或者济南,或者青岛,或者重庆。这是一非常有趣的文学地理现象。有许多作家,他的青少年时代决定了他以后的创作走向,也决定了他的创作风格,老舍先生也是这样。我们联系起来,比如说,莎士比亚笔下的斯特拉福德,雨果笔下的巴黎,狄更斯笔下的伦敦,甚至像哈代笔下的威塞克斯,都是作家们再熟悉不过的青年的故乡,现实的一种艺术的反观与反照,有虚构的有真实的,两者非常巧妙、非常艺术的连接在了一起。像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镇,和前面有一些区别。他们的故乡是虚构的,当然也不完全是虚构的,有真实的现实的投影。
老舍先生的北京和这些作家相比也有相同的意味。他在写的时候虽然自己不在北京,但他度过青少年时代的那个地方,已经深深地融化在他的血液中,只要他拿起笔来写北京,脑子里就全是他生活中那个地方的人情物事。像他写《四世同堂》是在重庆,抗战时期也没在北京,他就把情节安排在他出生的那个小院,小羊圈。这是一个作家的本领,他调动起了艺术家的艺术积累和储藏,而这个储藏是在青少年时代就打下来的,就注定了的。
另外呢,老舍先生当了教授之后,给自己的母亲在城里几乎与太平湖相对应的那个地方,买了一所房子,母亲在那儿住了十年。老舍先生的死,与给他母亲买房子的所在地,也有一种生与死的交汇。这都是可以思考的。老舍先生的母亲是在那儿去世了,老舍先生在写《我的母亲》这篇文章时说,当他听到把性格和生命传给他的母亲去世的噩耗时,非常悲痛。因为母亲是给他生命的人,也是把自己软中带硬的性格传给他的人。他深爱着他的母亲,当他自己完全悲观绝望或者说也要去抗争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到自己的母亲。老舍先生《我的母亲》里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叙述: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那时老舍先生在家里,八国联军进了小院四处搜查,刺刀捅到了一个箱子,后来那个箱子压着老舍先生。八国联军走了之后,妈妈发现那里面压着老舍。如果当时箱子不是空的而是有东西,可能会把小孩压死。而如果不是翻箱子时老舍掉出来,还在箱子里,可能八国联军的刺刀就会把老舍捅死了。
我也是带着这样一个疑问,在十几年前开始追踪采访、调查、研究老舍之死这样一个沉重而有文化思想和意韵内涵的话题。我开始的想法是像一个案件调查者一样,通过追踪线索把那个历史的场景清晰地再现出来。想法好像是很简单的,只想在对受访者的不断追踪挖掘中,可能把那个历史现场还原。当时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采访的深入和自己理论的提升,我对历史的信任度和这种提升成反比。我发现当初的那个想法太单纯也太脆弱,脆弱的如同一张纸,一捅就破了。那么多受访者向我叙述的当天的历史场景我根本无法还原。我被历史搞糊涂了,面对着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冲突的历史叙述,那一天的情形好像更加支离破碎,无法将它建立起来,种种的细节无法将它统一。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老舍先生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文联被揪出来,紧接着在孔庙被批斗,回到文联又被批斗,遭受了三场批斗。在这样的批斗之后,老舍先生在第二天离家出走了。他到底是在第二天就投湖自杀了,还是在第三天投湖自杀了?时间上就有了不一样。我们姑且称作1966年8月23日那天发生的事件叫“八二三事件”,老舍先生在“八二三”那一天到底是上午来的、中午来的还是下午来的?说法各异。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说法各异。他拄没拄拐杖,哪天离家出走的?不知道。有疑点。他被打捞上来时,湖面上是不是漂满了碎纸片?不知道。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有的人特别希望有。这都是“八二三”这个历史事件带给我们的历史迷团。
作为一个采访人,作为一个追踪者,我理所当然地充满了敬意和善意去对待那些受访者。我觉得他们应该说的是实话,作为一个历史的叙述者,他们有说出他们见证的历史的真实的权利。但有可能他们在叙说历史时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间。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把他们所叙述的历史几乎一字不差的记录下来,同时对他们所做的历史的叙述作出一个自己的判断和反思。但我没有能力,没有权利,不能,不敢,也不会去说任何一个历史的叙述人和见证者所说的是谎话和不实的。我越来越觉得我扮演的是一个史官的角色,我得将我所采访的对象对历史的陈述如实地记录下来。至于他是不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是不是历史本身,我可以存疑。但我在记录历史时,必须本着一个记录者的史德如实地记录下来。我的头脑中会时刻想象一个话题:既然是某一个历史现场的见证人,他说的是不是就应该完全是真实的,不会出错?这个行为本身,严格来讲,从学术上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
现在好像口述历史变得很热,这个新东西也被炒得很热,目前在国内也很热。什么叫口述历史?这个概念是二战以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教授肯特·内文思提出的这么一个概念叫口述历史oral history。其实仔细想一想,在出现这个概念之前,口述历史的历史大概已经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在我们形成所谓的文字历史记载之前,很多历史都是口口相传的,都是由人们口述而形成的。比如像《史记》这样的历史书,关于五帝三皇呀,没有文字记载,就是司马迁收集了各种各样民间流行的传说,才记录下来这些史话。还有包括我们熟悉的,比如说鸿门宴,鸿门宴上的情景,就是司马迁描述的这个情景和当时实际鸿门宴的情景一样吗?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能相信,或者说我们愿意相信司马迁的文学描述,春秋笔法,描述的鸿门宴是真实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一幕:刘邦怎样、项羽怎样、樊郐怎样。所以,胡适先生对《史记》的一个看法就是,如果严格地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史记》就是一本历史小说,它带有很大的文学色彩。
其实这点很容易想通。比如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就是这个道理。任何历史都是文字写成的,任何历史都脱不了文学的笔法,文字的笔法。历史记载文字是个载体,它是不是真实的,能不能还原历史,这个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所在。我有一个学者朋友叫丁东。他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挺漂亮,他说“历史是一只巨大的黑箱,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黑箱的一隅”。我想说的是,我们如果能把黑箱中的那一隅给看清楚也已经相当不错了。有多少历史中的人与事,我们根本不清楚、不了解它到底怎么发生的。
我做老舍之死调查研究这个事,也想通过这个个案、这个事情本身,使口述历史的田野作业的行为在口述历史的理论上,有一些实际的意义,给人们提供一个历史线索,就是怎样认识历史,历史可能有巨大真空,有很多历史的本身是无法还原的。很多情形下我们所见到的历史可能是被人们重写过的,重塑过的。就是说,某一个事,它在历史上可能发生过,但你赋予它怎样的历史意义,有什么样的历史生命,是当代的历史学家当代的学者所做的。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才有这个话题。老说历史是当代史,历史是当代人写的历史,甚至说历史是史学家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历史学家写出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不一样。这也是很长时间来学术界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也是我们每个人,如果对历史还有兴趣还有思想的话,也应该不断地做这样一个思考:历史是什么?历史代表什么?我们相信历史吗?真实的历史什么样?我们能接近它吗?我们能还原历史吗?
拿老舍之死的叙述者来说,给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我遇到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这个例子的出现非常有趣,是大家想都想不到的。当我找到第一个自称是老舍尸体打捞者时,我欣喜若狂。我觉得终于可以把老舍之死打捞的那个现场还原了。他说的不会错,应该是真的,因为他有旁证来证明他为什么会在那个现场,为什么打捞的这个人是老舍。都说的有鼻子有眼,完全可以清晰逼真地再现现场每一个细节。
但紧接着,在我这篇访谈发表之后,看到这篇访谈的读者当中出现了第二位和第三位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有三位,而且这三个人互不相识,有两位是相识的。有意思的是,三个互不相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上了同一个人。如果说他们当中有真实的,只能有一个人真实,不可能三个人都真实。因为如果三个人都真实,那就等于那一天打捞起了三个老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三个都不真实,他们三个人捞的都不是老舍。作为一个记录历史的人,我必须把三个人所叙述的历史如实地只字不动地完全呈现在历史桌案上,作为历史的原始素材。对于他们说的对错、真伪,完全留给我们每一个人在了解这段历史后,在自己头脑中甄别判断。因为我不能在采访每一个人时做出主观判断,并且按我自己的主观取舍来说谁对谁错。这是违反史德,也是不符合口述历史理论上的做法的。
这个极端的例子提供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上的话题,就是口述史可以相信吗?所以,学术上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其实历史在它发生的一瞬间就已经过去了,无法再还原,历史在发生的一瞬间就不存在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永远不可能与见证人和叙述者的口吻相一致。有一位美国的口述史学家,在给学生们上口述史学课时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好像是在第一堂课开课之前,老师在讲台上什么话也不说,学生坐在底下很安静。进来了一个学生,是他找来的,他也不做介绍,学生就站在一边。大约站了五分钟,他让学生出去了。然后开始讲课,讲课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学生,刚才那个人大家给我描述一下。长什么样?头发是长是短?带眼镜吗?穿什么衣服?打领带吗?什么花纹?等等。
这个实验很有趣,班里的学生对这个人的描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就是刚刚发生的事,说法已经不统一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所有在场的人都说,“是我亲眼见的,肯定是真的”。为什么出现摄象机后,对口述历史的记录变的更科学了,也在这儿。比如说,我今天在这儿讲的,如果没有摄象机、录音机,大家走出门之后,你们再说傅光明讲什么时肯定不一样。大家容易对我的穿着进行描述,因为很简单。如果问讲的什么话,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机器的记录,我们可能无法还原。所以,严格地说就是,发生的那个历史无法还原。
用美国历史学家这个例子来说明太平湖的三位打捞者对这个事件的描述也是这样。三个人都说“是我亲眼见的,确实是真的”。是什么时间或是怎么接到的通知;怎么到现场;怎么处理的现场;并且还能提供旁证说,为什么我认为的这个人肯定是老舍。三个人的证据是不同的:有的人说在水中发现了老舍的一捆还没有完全湿掉的手稿,手稿上写着老舍的名字;有的说在岸边遗物当中有一张名片,名片上赫然印着老舍两字;还有一个人说,我打捞的时候,有我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生前与老舍认得,认出这是老舍。
你们看,三个人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捞上的是老舍,三个老舍。这个就让我困惑,让我疑惑。当然,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还原三个现场。因为确实不可能有三个老舍存在,只有一个。这个是由口述历史的叙述人提供的证言给口述历史理论上提出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人们对口述历史困惑的一点,也就是说,我们愿意相信口述者说的是真的这种愿望,比如说我们想要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一件事,我们特希望找到一个现场的见证人,他所描述的一定是真的。我想通过这样的调查在这一点上提供给大家一个什么信息呢。当你在面对约定俗成的某些历史的人或物时,脑子里要打一个问号,要反思这是历史的叙述者口述者他嘴里说的,可能与历史的原始记录、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一样的。探讨是谁打捞的老舍可能并没有太实际的意义,但理论上有价值。
在这背后,我们要继续提出疑问了:老舍先生作为人民艺术家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投水而死?投水为什么会在太平湖而死?这是我们应该思索在他死亡背后的所在。这么一个人民艺术家消失得无声无息,瞬间就跌入历史的黑箱,没有人知道在临死前他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巨大苦痛。在他投水之前,不管是有一天一夜,还是别的叙述者所说的时间很短,能肯定的是,他坐在湖边,面对太平湖静静的水面时,他在思考。
他在作品中有这样的描述。《老张的哲学》里写26岁的李静在死前有一段伏笔说,“自杀者面对湖水可能哭也可能笑,有时也会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而这自问自答的结果就使他坚定了死亡的决心。”我想,作为写家的老舍,在死亡前的那一刻,他肯定想了很多很多。他怎么想的,这只有让九泉之下的老舍给我们叙述了,这是无法还原的。同时,这给我们留下一个巨大的艺术想象的空间。老舍之死这个历史事件,在发生多年之后,人们开始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老舍时,最有意思的一点是,把老舍之死改编成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有书、话剧还有歌剧。它带来了很多东西,留下了很多空间,有历史的,有艺术的。
艺术家可以根据这个历史空间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去填补很多东西。比如像苏叔阳先生那个老舍之死的话剧,就是让老舍在冥界与舒乙对话。他以自己作家的思想来推测老舍在面对太平湖时想了什么,思考了什么。这是作家做的,也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也就是说,今天在想这件事时,你还得不断地自问,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老舍的读者,如果你是一个对这件事感兴趣并想从中得到一些启示的读者,你应该想一想,这样一个作家在临死前想了些什么,他可能会想什么,他想的与自己的出身成长,与作品中的人物安排以及作品中的思想等等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这其实也是我研究老舍之死的一个初衷,也是我的一份答案。我的答案不是准确的,只是对一个个体、一个个案的思考。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答案。老舍之死其实在不经意间已成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你在读了老舍之死访谈录的时候,在看了这些证言的时候,往往会有这样的感觉:历史可能是按照今天人们的想象从新编排、过滤的重塑的历史。这件事不在于老舍之死的那个现场是否能够还原,而在于我们怎样把我们今天对老舍之死的认识附到上面,赋予他活生生的历史生命。这是我们今天的人所应做的,也是后人所应做的。因为他带给我们太沉重的思想话题,如果对于这个话题没有足够深刻认识的话,我们有可能重蹈覆辙。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等等。口号容易提出来,口号之后要做什么,怎么做,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这样的思考,十几年当中不断地寻找挖掘历史的证人,虽然开始的时候我抱着一种强烈的心态,我找的每一个人肯定是真的,现在已不在乎找的人是不是真的,只要他说当天他在现场我就去找他,看他怎么说,如实记录下来,更多地更丰富地提供细节。因为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认识已经不再停留在既定的对历史文化的诠释上,还应该更多地关注历史所呈现出的多面性、复杂性,以及历史发生的过程性。虽然细节不是历史的全部,但没有细节历史是建立不起来的,是不活的、不立体的。
比如,我们现在想某些历史事件的时候,都是由种种细节把历史事件具体化了。我们可能对五六十年代的影片《甲午海战》印象非常深。一曲凝重悲怆的爱国主义悲歌。对邓世昌我们是那么的难忘。但是随着历史细节的浮出水面,随着历史档案的精细揭秘,随着我们对历史深入的了解,你会发现《甲午海战》是艺术的历史,是艺术的真实,它可能不是历史本身。央视前不久播了两个很好的片子,一个叫《庚子国变》一个叫《北洋水师》。就是用真正的历史档案、历史文献,用记录片的手段把当时的情景再现出来。
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看到电影里刘步蟾是海战时贪生怕死的一个副将。而真正的历史,恰恰是丁汝昌中炮后,刘步蟾担当起了指挥。这和历史差别极大。从艺术上讲,《甲午海战》是成功的,它带给我们的视觉的冲击、场面的悲怆都是难忘的。但它是艺术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艺术可以利用真正的历史留下的空间进行艺术的再造,但我们头脑中一定要清醒,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影视中所展现的历史,可能仅仅是艺术而不是真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是史学家的天敌。他可能设下了种种圈套,包括我们现在学习历史,我们接受的可能是戏说的历史给我们陈述的历史细节。今天我们的中小学生爱看的《康熙微服私访》、《雍正大帝》都是戏说历史。但学生们津津乐道地说那个雍正和乾隆那时什么什么事,好像影视剧里的事真是历史发生时的样子。这和历史有天壤之别。
我们现在来思考老舍先生为什么会死。关于老舍之死大体上有这样三种认识:一种认为老舍先生的死可以与屈原和田横五百壮士相提并论,是舍生取义的,是抗争的,表现出一种拼死的不屈的骨气。这可以简称为“抗争说”。还有一种说,老舍先生死因为他绝望,他在建国后一直很顺。很多人说,老舍先生一直开顺风船。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不断有创作,还有《茶馆》这样的创作高峰。因为他很顺,所以当文革来临时,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暴力的侮辱,老舍先生的心灵是脆弱的,选择了去死。还有一种认为,懂得幽默的老舍何不在那时幽默一下,就可以躲过这一劫了。
人们提出了一个假设,假如那天老舍不去文联就不会碰上那场批斗,没有那场批斗,没有挨那顿打,老舍先生心灵和精神没有遭受屈辱的创伤,他可能就不会死了。首先,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如果我们真的按照这个假设进行历史还原的话,如果老舍先生不去,是不是会不死?我觉得难。就文革的发生来说,有它历史偶然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历史的必然,偶然和必然交织在一起。作为作家的老舍,是一个政治上的门外汉,不懂政治。在他几乎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惨烈的血腥的运动批判、侮辱、毒打,是这样一位老人,以写作为生的作家无法承受的。老舍先生的死,我认为是一个必然,偶然中有它的必然。如果“八二三”躲过去了,后面还会有“九二三”“十二三”。他躲不过去,老舍在文革中是注定要死的。
老舍先生为什么要选择太平湖呢?太平湖东边离他家更近的有什刹海、后海、积水潭。这里有没有他刻意的选择?选择他死亡的归宿?我想,作为一个大作家的老舍来说,他有他的第六感,把自己的归宿刻意的选在了太平湖。可以提出一种自己的思索,把这种思索当作证据,然后与选择这个归宿的地点联系在一起。
老舍生前写了无数作品,而他大多数优秀作品的故事的发生,几乎都是在他祖上正红旗下的属地,就是北京城的西北。《四世同堂》故事的发生,就在老舍先生的出生地,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胡同。他出生在那个地方,青少年成长在那个地方,他所接受的私塾教育,以及他后来上缸瓦市教堂,作品中描述的许多人和事物以及许多情景的发生,大多数都是在那个地方。他对于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青少年时代的地方,对自己真实的故乡,精神的故乡,心灵的故乡,再熟悉不过了。
有一个现象非常有趣,这当然不单单是对老舍一个作家来说的。我们看老舍写北京的作品,除了他晚年的一部《正红旗下》,其他那几部非常棒的作品,《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老张的哲学》,写北京的都不是在北京写的,都是在北京之外写的,或者伦敦,或者济南,或者青岛,或者重庆。这是一非常有趣的文学地理现象。有许多作家,他的青少年时代决定了他以后的创作走向,也决定了他的创作风格,老舍先生也是这样。我们联系起来,比如说,莎士比亚笔下的斯特拉福德,雨果笔下的巴黎,狄更斯笔下的伦敦,甚至像哈代笔下的威塞克斯,都是作家们再熟悉不过的青年的故乡,现实的一种艺术的反观与反照,有虚构的有真实的,两者非常巧妙、非常艺术的连接在了一起。像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镇,和前面有一些区别。他们的故乡是虚构的,当然也不完全是虚构的,有真实的现实的投影。
老舍先生的北京和这些作家相比也有相同的意味。他在写的时候虽然自己不在北京,但他度过青少年时代的那个地方,已经深深地融化在他的血液中,只要他拿起笔来写北京,脑子里就全是他生活中那个地方的人情物事。像他写《四世同堂》是在重庆,抗战时期也没在北京,他就把情节安排在他出生的那个小院,小羊圈。这是一个作家的本领,他调动起了艺术家的艺术积累和储藏,而这个储藏是在青少年时代就打下来的,就注定了的。
另外呢,老舍先生当了教授之后,给自己的母亲在城里几乎与太平湖相对应的那个地方,买了一所房子,母亲在那儿住了十年。老舍先生的死,与给他母亲买房子的所在地,也有一种生与死的交汇。这都是可以思考的。老舍先生的母亲是在那儿去世了,老舍先生在写《我的母亲》这篇文章时说,当他听到把性格和生命传给他的母亲去世的噩耗时,非常悲痛。因为母亲是给他生命的人,也是把自己软中带硬的性格传给他的人。他深爱着他的母亲,当他自己完全悲观绝望或者说也要去抗争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到自己的母亲。老舍先生《我的母亲》里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叙述: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那时老舍先生在家里,八国联军进了小院四处搜查,刺刀捅到了一个箱子,后来那个箱子压着老舍先生。八国联军走了之后,妈妈发现那里面压着老舍。如果当时箱子不是空的而是有东西,可能会把小孩压死。而如果不是翻箱子时老舍掉出来,还在箱子里,可能八国联军的刺刀就会把老舍捅死了。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8-06-02
老舍(1899~1966), 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青、鸿来、□予、舍、非我等笔名。满族,正红旗人。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第2个回答 2008-05-23
老舍是淹死的
老舍很幽默
老舍很幽默
第3个回答 2008-05-27
第4个回答 2008-05-23
老舍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生于北京。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 京城的炮火中。母亲也是旗人.靠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1918年夏天,他以优秀的成绩由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到北京第十七小学去当校长。1924年夏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中文讲师。在英期间开始文学创作。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第一部作品,由1926年7月起在《小说月报》杂志连载,立刻震动文坛。以后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赵子口》和《二马》。奠定了老舍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地位。
1930年老舍回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授。这个时期创作了《猫城记》、《离婚》、《骆驼样子》等长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中篇小说,《微神》等短篇小说。1944年开始,创作近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
他担任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副主席兼北京文联主席,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1966年“文革”中不堪躏辱投湖自尽。
老舍1899年2月3日诞生于北京西城的小羊圈胡同,按农历算恰是腊月二十三,就是民间传说灶王爷上天的日子,所以家人给他起了一个喜庆的名字--"庆春"。那一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很有名的,按中国传统纪年叫"戌"年,"戊戌变法"或是"戊戌政变"就发生在那一年。按农历说,应当是狗年,腊月是在年根儿上,所以姑母又给他起了一个不太好听的小名--"小狗尾巴"。
他的父亲属"正红旗",是镇守皇城的旗兵,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死于战乱。
那时庆春刚一岁半。父亲早亡,这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只能靠母亲和姐姐为别人洗衣服做活勉强维持生活。
他的童年是在清贫与寂寞中度过的。那窄小狭长的胡同,凸凹不平的肮脏空地,枝干扭曲的老树,灰皮剥落的矮院墙,便构成了他的整个世界,也造就了他自尊自信、刚毅敏感的个性。对于母亲、对于童年,他自己曾说过:"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袜子,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庆春长到9岁了,还不识一个字,因为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学。做小买卖或是当个学徒,也许是最现实的选择。然而,就在这时,一位善良者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个人的名字叫刘寿绵,庆春称他为"刘大叔"。那天他来串门,极偶然地问起:"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听母亲回答完,他立马说:"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
第二天,庆春便"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跟着刘大叔迈进了学校的门坎。那是一所私塾,设在离他家不远的一座破道士庙里。又黑又冷的大殿里,一块肮脏的黄布遮挡着色彩斑驳的神像,孔老夫子的牌位就摆在供桌上。三十来个年龄参差不齐的学生面西而坐,对着的西墙上有一块黑板--那倒是与一般私塾稍有不同的地方。然而,给庆春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充溢在那庙里的各种气味:刺鼻的大烟味儿,隔壁制糖作坊传过来的糖精味儿,还有厕所茅坑里沤出来的屎尿味儿。所以,这里似乎也可以被称作是"三味书屋"了。老师姓李,是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在刘大叔的指教下,庆春拜了孔圣人和老师,便正式成了这里的学生。"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是庆春启蒙的第一课。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生于北京。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 京城的炮火中。母亲也是旗人.靠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1918年夏天,他以优秀的成绩由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到北京第十七小学去当校长。1924年夏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中文讲师。在英期间开始文学创作。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第一部作品,由1926年7月起在《小说月报》杂志连载,立刻震动文坛。以后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赵子口》和《二马》。奠定了老舍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地位。
1930年老舍回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授。这个时期创作了《猫城记》、《离婚》、《骆驼样子》等长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中篇小说,《微神》等短篇小说。1944年开始,创作近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
他担任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副主席兼北京文联主席,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1966年“文革”中不堪躏辱投湖自尽。
老舍1899年2月3日诞生于北京西城的小羊圈胡同,按农历算恰是腊月二十三,就是民间传说灶王爷上天的日子,所以家人给他起了一个喜庆的名字--"庆春"。那一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很有名的,按中国传统纪年叫"戌"年,"戊戌变法"或是"戊戌政变"就发生在那一年。按农历说,应当是狗年,腊月是在年根儿上,所以姑母又给他起了一个不太好听的小名--"小狗尾巴"。
他的父亲属"正红旗",是镇守皇城的旗兵,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死于战乱。
那时庆春刚一岁半。父亲早亡,这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只能靠母亲和姐姐为别人洗衣服做活勉强维持生活。
他的童年是在清贫与寂寞中度过的。那窄小狭长的胡同,凸凹不平的肮脏空地,枝干扭曲的老树,灰皮剥落的矮院墙,便构成了他的整个世界,也造就了他自尊自信、刚毅敏感的个性。对于母亲、对于童年,他自己曾说过:"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袜子,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庆春长到9岁了,还不识一个字,因为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学。做小买卖或是当个学徒,也许是最现实的选择。然而,就在这时,一位善良者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个人的名字叫刘寿绵,庆春称他为"刘大叔"。那天他来串门,极偶然地问起:"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听母亲回答完,他立马说:"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
第二天,庆春便"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跟着刘大叔迈进了学校的门坎。那是一所私塾,设在离他家不远的一座破道士庙里。又黑又冷的大殿里,一块肮脏的黄布遮挡着色彩斑驳的神像,孔老夫子的牌位就摆在供桌上。三十来个年龄参差不齐的学生面西而坐,对着的西墙上有一块黑板--那倒是与一般私塾稍有不同的地方。然而,给庆春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充溢在那庙里的各种气味:刺鼻的大烟味儿,隔壁制糖作坊传过来的糖精味儿,还有厕所茅坑里沤出来的屎尿味儿。所以,这里似乎也可以被称作是"三味书屋"了。老师姓李,是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在刘大叔的指教下,庆春拜了孔圣人和老师,便正式成了这里的学生。"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是庆春启蒙的第一课。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