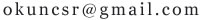帮忙翻译,100分,不要机器翻译
(三)印度河流域
公元前2600-1900年,今巴基斯坦和印度西部出现了“城市文明”,覆盖25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城市规划正规严谨,是经济和政治中心,出现统一的文字、神话、象征符号等,但缺乏战争征服的迹象,似乎是贸易和政治联盟。城墙有可能有防洪功能。Jonathan Mark Kenoyer等认为这些城市可能是城邦,既不是酋邦,也不是受国王或任何集权把头的控制。商人、地主和宗教领袖等精英构成聚落的领导层[4]。宗教服务于维系城市的各种社群。
公元前1900年以降后600年间,由于河流的改道,贸易路线的废弃,原先的贸易-政治联盟的文明被轻而易举地侵蚀而衰落,文明中心向今印度北部的恒河流域。这时印度-雅利安人从礼教、语言和文化方面全面取代原生文明。
印度河谷文明的全貌远没有弄清,就目前的资料看,也可能是一种“续生型”模式。
(四)中国文明的特色
中国文明起源是以黄河、长江、辽河三大流域为单独发展基础,在多样性的生态环境里造就了不同文化选择的文明起源多元中心。各中心社会复杂化的具体机制不尽相同,北方半干旱半湿润地区,灌溉水利工程大约是社会复杂化的机制,处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带的长江流域则以洪水控制体系为社会分层的机制。不论南北地区,由于社会内部分层由来已久,加上中国文明起源主要集中在东部二级台阶以下的平原地区,实际无大的地理阻隔和大的破碎地理单元,政体倾向于至少在文化区内的集权化。所以,中国文明过程更趋向于从酋邦社会向成熟的早期国家过渡,不大有机会进入到两河流域式的“原始民主制”城邦。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面向太平洋,背倚欧亚大陆,幅员辽阔,发展空间绝对比尼罗河和两河流域要宽广的多。因而中国的文明模式更容易倾向于中心辐射型,而不是埃及和两河香肠式的模式。
中国历来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命脉,贸易在古代一直未能占领社会经济主体的地位。因此中国文明进程中,“城市革命”可能不是最首要的。因此中国缺乏形成古印度“城市文明”的土壤。
随着龙山时代尧、舜、禹酋邦在黄河从黄土高原向华北大平原跌落的出口上稳稳地站住脚跟后,黄河在此无法随意摆动又给黄河中游带来可预测的丰富的水利。这个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选择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进。而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下游良渚文化和早先的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因选择了非可持续发展道路而先后崩溃或原地踏步,最终促成以黄河中游一枝独秀的局面形成。中国文明一体化进程正式启动,中国文明蛛网式核心辐射型模式诞生。
中原文明核心形成后,采纳大河文化心态,汇聚千流,吸纳百川,使中原文化具有水一样优良的融合性、渗透性。开禹贡九道,将原各文明起源中心的优秀精华吸纳于中原,集四方成就之大成,方使中国文明生生不熄。禹贡九州的分划、五服、九牧、十八岳的官僚体制充分显示出中原文明核心辐辏八方的外交型行政管理手段,同埃及内向型官僚体制迥然不同。
中国文明起源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多样化,造就了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一体化后又长期地充分保留了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从文化、政治、宗教、思想、哲学等诸多方面为文明核心源源不断地提供多样化的养分,以保持中国文明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这是埃及、两河甚至印度所缺乏的,这也正是中国文明这个唯一一个从诞生之日至今从未被打断的文明成功的秘诀。
总之,中国的文明起源模式是多元一体化的蛛网辐辏模式,从其起源到形成,一直带有集权色彩,完全不同于市民做主的“原始民主制”城邦政体制度。
기원전 2600-1900이 파키스탄과 인도 서부 도시 문명 "에서"토지의 250,000 평방 마일을 취재했다. 마을 기획 엄격한 공식 경제와 정치의 중심, 통일 텍스트, 신화, 기호 등등의 등장하지만, 표지판의 부족을 정복하기 위해 전쟁의 무역 및 정치적 동맹이 될 것으로 보인다. 이미 홍수 벽 기능이있을 수있습니다. 조나단 마크 Kenoyer, 그리고 다른 도시는 도시 - 상태, Chiefdom 마찬가지가 될 수도없고 그것은 국왕이나 중앙 통제의 머리에 따라 달라질 수있습니다. 상인, 지주와 종교 지도자 등 엘리트 거주지 [4의 리더십을 구성]. 도시에 종교적인 서비스는 다양한 커뮤니티를 유지하도록하겠습니다.
기원전 600 년 뒤 1900 년에 내려, 하천의 양동 작전으로 인해, 무역 경로를 쉽게와 북부 인도의 갠지스 강 유역의 중심이 문명의 쇠퇴 침식되고 원래 무역 - 문명의 정치적 동맹을 포기했다. 이번에 인도 - 아리아 윤리, 문화, 언어 및 원시 문명을 바꿉니다.
현재까지 인도 문명 밸리에서 정보를 선명하게, 건강 "모델의"갱신이 될 수있습니다.
(D)를 중국 문명의 특성
황하 중국 문명의 기원, 양쯔 강, Liaohe 강 유역에 근거하여 별도의 개발을위한 세 가지 서로 다른 문화의 생태 환경에 다양성을 문명의 기원의 여러 시설 중 하나를 선택하여 만들어집니다. 구체적인 메커니즘의 사회적 센터의 복잡 북쪽 준결승에서 - 건조한 잠수함 - 습한 지역, 관개 물에 대한 사회적 메커니즘이 다르다 합병증, 습한 아열대 기후 지역에있는 사회 충화의 메커니즘에 대한 양쯔 강 유역 홍수 통제 시스템이있다. 에 관계없이 북쪽과 남쪽의, 층화 사회는 오랜 세월 동안, 그리고 중국 문명 일반 영역 아래의 보조 수준의 동쪽 부분에 집중되어의 기원으로,이 지역에서 정치 문화, 적어도 현실 없다는 주요 지리적 장벽과 지리적 단위의 단편화하는 경향이 이 집중. 따라서이 과정에서 중국인을 Chiefdom 문명 사회에서 더욱 성숙하고 조기 전환을 국가로, 기회가 메소포타 미아에 진입 - 스타일은 원래 "도시의"민주주의 - 상태가 없어 어렵다.
중국은 아시아의 동쪽 부분에, 태평양 직면하고있는, Beiyi 유라시아 대륙의 광대한 영토와 공간의 개발보다 더 광범위한 나일강과 메소포타 미아이다. 중국 문명의 모델, 따라서 더 많은 방사선을하는 경향 - 센터,하지 이집트와 두 개의 소시지의 강물 - 패턴처럼.
중국어 농업 항상 있었던 - 주요 사회 경제적 지위의 직업에서 고대 무역 수 없다 경제 기반의 혈액왔다. 따라서, 중국 문명의 과정에서, "혁명의 도시"가 될 수없습니다 가장 중요하다. 따라서 중국의 고대 인도의 부족의 형성, "도시 문명,"토양.
야오밍과 함께, Shun에, 유 Chiefdom the 뢰스 고원에서 노란 리버华北大平原수출에서 개최와 함께 굳게 내린 룽산 시대 황하 중간에 스윙을 무료로 될 수 없다는 황하의 물 한 재산도 예측을 가져왔다 이른다. 한 지속 가능한 발전의 경로를 선택, 꾸준히 발전의 중심에 문명의 기원. 이 가운데 양쯔강 Shijiahe 문화, Liangzhu 문화의 하단에 도달하면 도달 및 이전 버전은 Liaohe 리버 밸리 Hongshan 문화에, 이외의 결과로 - 지속 가능한 발전의 길을 선택하고 전혀 진전이나 붕괴, 그리고 중간에 결국 황하에 도달하기 위해서는 상황의 형성에 빛나다. 중국 문명과 통합 과정을 공식적으로, 중국 문명, 웹의 핵심 - 탄생을 시작 요골 패턴.
중부 평원 강물의 정신력을 채택, 함께 수천 개의 스트림을 가져, 하천, 그래서 문명을 흡수, 문화의 핵심 형태가 통합의 수질, 침투성으로 중앙 평원 문화. 오픈 9 Yugong, 문명의 기원, 우수성의 원래 센터 문명인의 삶과 생활을 위해 중앙 평원, 4 중주의 성공 - 아성, 중국의 측면에서 최선의 유치로하지 않습니다. 규슈, 5, 9, 축산, 그리고 관료 Dake에 18 사단 Yugong 외국 - 이집트와 P는 플러스 행정 수단, 내적인 - 찾고 관료의 중앙 평원 문명 유입의 핵심 보여주는 매우 다르다.
중국 문명의 기원과 다양성의 생태 환경, 문명의 기원의 다양성을 만들어; 오래 - 용어 통합을 누른 다음 장소의 문화적 다양성, 문화의 핵심을 문명의, 종교적 이념, 정치 철학 및 기타 여러 측면의 전체 유지하도록 하기 위해서는 이집트, 두 하천과 인도도 부족, 중국 문명의 유일한이다 소개된 중국 문명의 불후의 활력을 유지하기 위해 계속 두들겨 결코 영양소의 다변화를 제공 문명의 성공을 끄기.
한마디로 중국 문명의 기원 멀티 모델의 통합 - 유입의 웹 패턴은 원산지에서 중앙 색상의 형성에 가본 사람으로부터 완전히 타의 차이가, "원래 민주주의"시 정부의 시스템입니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