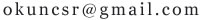仇恨会激发一个人的斗志吗??
我家在浙江农村,去年底,家里的几间小厂房被大火烧了!也算天灾,我也认了,但是我家隔壁的一户邻居(好几代前,还是一家),竟然不过来慰问一下(虽然以前,因为地基闹过点小矛盾),现在说实话看到这一家子就来气,我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连路上见面,也不慰问一下~~~~!!!!-----大家可能觉得我的想法幼稚,没错我才23岁,有时候没什么经验
当然我说的"斗志"不是和他们,打斗!我要努力,为自己奋斗
沙 巴 军 曹
一个夏天的夜晚,荷西与我正从家里出来,预备到凉爽的户外去散步,经过
炎热不堪的一天之后,此时的沙漠是如此的清爽而怡人。在这个时候,邻近的沙
哈拉威人都带着孩子和食物在外面晚餐,而夜,其实已经很深了。
等我们走到快近小镇外的坟场时,就看见不远处的月光下有一群年轻的沙哈
拉威人围着什么东西在看热闹,我们经过人堆时,才发觉地上趴着一个动也不动
的西班牙军人,样子像死去了一般,脸色却十分红润,留着大胡子,穿着马靴,
看他的军装,知道是沙漠军团的,身上没有识别阶级的符号。
他趴在那儿可能已经很久了,那一群围着他的人高声的说着阿拉伯话,恶作
剧的上去朝他吐口水,拉他的靴子,踩他的手,同时其中的一个沙啥拉威人还戴
了他的军帽好似小丑一般的表演着喝醉了的人的样子。
对于一个没有抵抗力的军人,沙哈拉威人是放肆而大胆的。“荷西,快回去
把车开来。”我对荷西轻轻的说,又紧张的向四周张望着,在这时候我多么希望
有另外一个军人或者西班牙的老百姓经过这里,但是附近没有一个人走过。
荷西跑回家去开车时,我一直盯着那个军人腰间挂着的手枪,如果有人解他
的枪,我就预备尖叫,下一步要怎么办就想不出来了。那一阵西属撒哈拉沙漠的
年轻人,已经组成了“波里沙里奥人民解放阵线”,总部在阿尔及利亚,可是镇
上每一个年轻人的心几乎都是向着他们的,西班牙人跟沙哈拉威人的关系已经十
分紧张了,沙漠军团跟本地更是死仇一般。
等荷西飞也似的将车子开来时,我们排开众人,要把这个醉汉拖到车子里去
。这家伙是一个高大健壮的汉子,要抬他到车里去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等到我们
全身都汗湿了,才将他在后座放好,关上门,口里说着对不起,慢慢的开出人群
,车顶上仍然被人碰碰的打了好几下。
在快开到沙漠军团的大门时,荷西仍然开得飞快,营地四周一片死寂。“荷
西,闪一闪灯光,按喇叭,我们不知道口令,要被误会的,停远一点。”荷西的
车子在距离卫兵很远的地方停下来了,我们赶快开了车门出去,用西班牙文大叫
:“是送喝醉了的人回来,你们过来看!”两个卫兵跑过来,枪子咔答上了膛,
指着我们,我们指指车里面,动也不动。这两个卫兵朝车里一看,当然是认识的
,马上进车去将这军人抬了出来,口里说着:“又是他!”
这时,高墙上的探照灯刷一下照着我们,我被这种架势吓得很厉害,赶快进
车里去。
荷西开车走时,两个卫兵向我们敬了一个军礼,说:“谢啦!老乡!”我在
回来的路上,还是心有余悸,被人用枪这么近的指着,倒是生平第一次,虽然那
是自己人的部队,还是十分紧张的。有好几天我都在想着那座夜间警备森严的营
区和那个烂醉如泥的军人。过了没多久,荷西的同事们来家里玩,我为了表示待
客的诚意,将冰牛奶倒了一大壶出来。
这几个人看见冰牛奶,像牛喝水似的呼一下就全部喝完了,我赶紧又去开了
两盒。
“三毛,我们喝了你们怎么办?”这两个人可怜兮兮的望着牛奶,又不好意
思再喝下去。
“放心喝吧!你们平日喝不到的。”
食物是沙漠里的每一个人都关心的话题,被招待的人不会满意,跟着一定会
问好吃的东西是哪里来的。
等荷西的同事在那一个下午喝完了我所有盒装的鲜奶,见我仍然面不改色,
果然就问我这是哪儿买来的了。
“嘿!我有地方买。”我得意的卖着关子。
“请告诉我们在哪里!”
“啊!你们不能去买的,要喝上家里来吧!”
“我们要很多,三毛,拜托你讲出来啊!”
我在沙漠军团的福利社买的。”“军营?你一个女人去军营买菜?”他们叫
了起来,一副老百姓的呆相。“军眷们不是也在买?我当然跑去了。”
“可是你是不合规定的老百姓啊!”
“在沙漠里的老百姓跟城里的不同,军民不分家。”我笑嘻嘻的说。“军人
,对你还有礼貌吗?”
“太客气了,比镇上的普通人好得多了。”
“请你代买牛奶总不会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的,要几盒明天开单子来吧!”
第二天荷西下班回来,交给我一张牛奶单,那张单子上列了八个单身汉的名
字,每个人每星期希望我供应十盒牛奶,一共是八十盒。我拿着单子咬了咬嘴唇
,大话已经说出去了,这八十盒牛奶要我去军营买,却实在是令人说不出口。
在这种情形下,我情愿丢一次脸,将这八十盒羞愧的数量一次买清,就不再
出现,总比一天去买十盒的好。
隔了一天,我到福利社里去买了一大箱十盒装的鲜乳,请人搬来放在墙角,
打一个转,再跑进去,再买一箱,再放在墙角,过了一会儿,再进去买,这样来
来去去弄了四次,那个站柜台的小兵已经晕头转向了。
“三毛,你还要进进出出几次?”
“还有四次,请忍耐一点。”
“为什么不一次买?都是买牛奶吗?”
“一次买不合规定,太多了。”我怪不好意思的回答着。“没关系,我现在
就拿给你,请问你一次要那么多牛奶干嘛?”“别人派我来买的,不全是我的。
”
等我把八大箱牛奶都堆在墙角,预备去喊计程车时,我的身边刷一下停下了
一辆吉普车,抬头一看,吓了一跳,车上坐着的那个军人,不就是那天被我们抬
回营区去的醉汉吗?
这个人是高大的,精神的,制服穿得很合身,大胡子下的脸孔看不出几岁,
眼光看人时带着几分霸气又嫌过分的专注,胸膛前的上衣扣一直开到第三个扣子
,留着平头,绿色的船形军帽上别着他的阶级——军曹。
我因为那天晚上没有看清楚他,所以刻意的打量了他一下。他不等我说话,
跳下车来就将小山也似的箱子一个一个搬上了车,我看牛奶已经上车了,也不再
犹豫,跨上了前座。
“我住在坟场区。”我很客气的对他说。
“我知道你住在那里。”他粗声粗气的回答我,就将车子开动了。我们一路
都没有说话,他的车子开得很平稳,双手紧紧的握住方向盘,等车子经过坟场时
,我转过头去看风景,生怕他想起来那个晚上酒醉失态被我们捡到的可怜样子会
受窘。到了我的住处,他慢慢的煞车,还没等他下车,我就很快的跳下来了,因
为不好再麻烦这个军曹搬牛奶,我下了车,就大声叫起我邻近开小杂货店的朋友
沙仑来。
沙仑听见我叫他,马上从店里趿着拖鞋跑出来了,脸上露着谦卑的笑容。等
他跑到吉普车面前,发现有一个军人站在我旁边,突然顿了一下,接着马上低下
了头赶快把箱子搬下来,那个神情好似看见了凶神一般。这时,送我回来的军曹
,看见沙仑在替我做事,又抬眼望了一下沙仑开的小店,突然转过眼光来鄙夷的
盯了我一眼,我非常敏感的知道,他一定是误会我了,我胀红了脸,很笨拙的辩
护着:“这些牛奶不是转卖的,真的!请相信我,我不过是——。”他大步跨上
了车子,手放在驾驶盘上拍了一下,要说什么又没说,就发动起车子来。
我这才想起来跑了过去,对他说:“谢谢你,军曹!请问贵姓?”他盯住我
,好似已经十分忍耐了似的对我轻轻的说:“对沙哈拉威人的朋友,我没有名字
。”
说完就把油门一踏,车子飞也似的冲了出去。
我呆呆的望着尘埃,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被人冤枉了,不给我解释的余地
,问他的名字,居然被他无礼的拒绝了。
“沙仑,你认识这个人?”我转身去问沙仑。
“是。”他低声说。“干什么那么怕沙漠军团,你又不是游击队?”
“不是,这个军曹,他恨我们所有的沙哈拉威人。”
“你怎么知道他恨你?”
“大家都知道,只有你不知道。”
我刻意的看了老实的沙仑一眼,沙仑从来不说人是非,他这么讲一定有他的
道理。从那次买牛奶被人误会了之后,我羞愧得很久不敢去军营买菜。隔了很久
,我在街上遇见了福利社的小兵,他对我说他们队上以为我走了,又问我为什么
不再去买菜,我一听他们并没有误会我的意思,这才又高兴的继续去了。
运气就有那么不好,我又回军营里买菜的第一天,那个军曹就跨着马靴大步
的走进来了,我咬着嘴唇紧张的望着他,他对我点点头,说一声:“日安!”就
到柜台上去了。
对于一个如此不喜欢沙哈拉威人的人,我将他解释成“种族歧视”,也懒得
再去理他了,站在他旁边,我专心向小兵说我要买的菜,不再去望他。
等我付钱时,我发觉旁边这个军曹翻起袖子的手臂上,居然刻了一大排纹身
刺花,深蓝色的俗气情人鸡心下面,又刺了一排中号的字——“奥地利的唐璜”
。
我奇怪得很,因为我本来以为刺花的鸡心下面一定是一个女人的名字,想不
到却是个男人的。
“喂!‘奥地利的唐璜’是谁?是什么意思?”
等那个军曹走了,我就问柜台上沙漠军团的小兵。
“啊!那是沙漠军团从前一个营区的名字。”
“不是人吗?”“是历史上加洛斯一世时的一个人名,那时候奥地利跟西班
牙还是不分的,后来军团用这名字做了一个营区的称呼,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可是,刚刚那个军曹,他把这些字都刻在手臂上哪!”
我摇了摇头,拿着找回来的钱,走出福利社的大门去。
在福利社的门口,想不到那个军曹在等我,他看见了我,头一低,跟着我大
步走了几步,才说:“那天晚上谢谢你和你先生。”“什么事?”我不解的问他
。
“你们送我回去,我——喝醉了。”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个人真奇怪,突然来谢我一件我已忘记了的事情,上次他送我回去时怎么
不谢呢?
“请问你,为什么沙哈拉威人谣传你恨他们?”我十分鲁莽的问他。“我是
恨。”他盯住我看着,而他如此直接的回答使我仍然吃了一惊。“这世界上有好
人也有坏人,并不是那一个民族特别的坏。”我天真的在讲一句每一个人都会讲
的话。
军曹的眼光掠向那一大群在沙地上蹲着的沙哈拉威人,脸色又一度专注得那
么吓人起来,好似他无由的仇恨在燃烧着他似的可怖。我停住了自己无聊的话,
呆呆的看着他。
他过了几秒钟才醒过来,对我重重的点了一下头,就大步的走开去。这个刺
花的军曹,还是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他的手臂,却刻着一整个营区的名称,而
这为什么又是好久以前的一个营区呢?有一天,我们的沙哈拉威朋友阿里请我们
到离镇一百多里远的地方去,阿里的父亲住在那儿的一个大帐篷里,阿里在镇上
开计程车,也只有周末可以回家去看看父母。
阿里父母住的地方叫“魅赛也”,可能在千万年前是一条宽阔的河,后来枯
干了,两岸成了大峡谷似的断岩,中间河床的部份有几棵椰子树,有一汪泉水不
断的流着,是一个极小的沙漠绿洲。这样辽阔的地方,又有这么好的淡水,却只
住了几个帐篷的居民,令我十分不解。在黄昏的凉风下,我们与阿里的父亲坐在
帐篷外,老人悠闲的吸着长烟斗,红色的断崖在晚霞里分外雄壮,天边第一颗星
孤伶伶的升起了。
阿里的母亲捧着一大盘“古斯格”和浓浓的甜茶上来给我们吃。我用手捏着
“古斯格”把它们做成一个灰灰的面粉团放到口里去,在这样的景色下,坐在地
上吃沙漠人的食物才相称。“这么好的地方,又有泉水,为什么几乎没有人住呢
?”我奇怪的问着老人。“以前是热闹过的,所以这片地方才有名字,叫做‘魅
赛也’,后来那件惨案发生,旧住着的人都走了,新的当然不肯再搬来,只余下
我们这几家在这里硬撑着。”
“什么惨案?我怎么不知道?是骆驼瘟死了吗?”我追问着老人。老人望了
我一眼,吸着烟,心神好似突然不在了似的望着远方。“杀!杀人!血流得当时
这泉水都不再有人敢喝。”
“谁杀谁?什么事?”我禁不住向荷西靠过去,老人的声音十分神秘恐怖,
夜,突然降临了。
“沙哈拉威人杀沙漠军团的人。”老人低低的说,望着荷西和我。“十六年
前,‘魅赛也’是一片美丽的绿洲,在这里,小麦都长得出来,椰枣落了一地,
要喝的水应有尽有,沙哈拉威人几乎全把骆驼和山羊赶到这里来放牧,扎营的帐
篷成千上万——”老人在诉说着过去的繁华时,我望着残留下来的几棵椰子树,
几乎不相信这片枯干的土地也有过它的青春。
“后来西班牙的沙漠军团也开来了,他们在这里扎营,住着不走——。”老
人继续说。
“可是,那时候的撒哈拉沙漠是不属于任何人的,谁来都不犯法。”我插嘴
打断他。
“是,是,请听我说下去——”老人比了一个手势。
“沙漠军团来了,沙哈拉威人不许他们用水,两方面为了争水,常常起冲突
,后来——”
我看老人不再讲下去,就急着问他:“后来怎么了?”
“后来,一大群沙哈拉威人偷袭了营房,把沙漠军团全营的人,一夜之间在
睡梦里杀光了。统统用刀杀光了。”
我张大了眼睛,隔着火光定定的望着老人,轻轻的问他:“你是说,他们统
统被杀死了?一营的人被沙哈拉威人用刀杀了?”“只留了一个军曹,他那夜喝
醉了酒,跌在营外,醒来他的伙伴全死了,一个不留。”
“你当时住在这里?”我差点没问他:“你当时参加了杀人没有?”“沙漠
军团是最机警的兵团,怎么可能?”荷西说。
“他们没有料到,白天奔驰得太厉害,卫兵站岗又分配得不多,他们再没有
料到沙哈拉威人拿刀杀进来。”
“军营当时扎营在哪里?”我问着老人。
“就在那边!”老人用手指着泉水的上方,那儿除了沙地之外,没有一丝人
住过的痕迹。“从那时候起,谁都不喜欢住在这里,那些杀人的当然逃了,一块
好好的绿洲荒废成这个样子。”
老人低头吸烟,天已经暗下来了,风突然厉裂的吹拂过来,夹着呜呜的哭声
,椰子树摇摆着,帐篷的支柱也吱吱的叫起来。我抬头望着黑暗中远方十六年前
沙漠军团扎营的地方,好似看见一群群穿军装的西班牙兵在跟包着头举着大刀的
沙哈拉威人肉搏,他们一个一个如银幕上慢动作的姿势在刀下倒下去,成堆的人
流着血在沙地上爬着,成千无助的手臂伸向天空,一阵阵无声的呐喊在一张张带
血的脸上嘶叫着,黑色的夜风里,只有死亡空洞的笑声响彻在寂寞的大地上——
我吃了一惊,用力眨一下眼睛,什么都不见了,四周安详如昔,火光前,坐
着我们,大家都不说话。
我突然觉得寒冷,心里闷闷不乐,这不只是老人所说的惨案,这是一场血淋
淋的大屠杀啊!
“那个唯一活着的军曹——就是那个手上刺着花,老是像狼一样盯着沙哈拉
威人的那一个?”我又轻轻的问。“他们过去是一个团结友爱的营,我还记得那
个军曹酒醒了在他死去的兄弟尸体上像疯子一样扑跌发抖的样子。”
我突然想到那个人手上刺着营名的纹身。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我问着。
“那件事情之后,他编在镇上的营区去,从那时候他就不肯讲名字,他说全
营的弟兄都死了,他还配有名字吗?大家都只叫他军曹。”过去那么多年的旧事
了,想起来依然使我毛骨悚然,远处的沙地好似在扭动一般。
“我们去睡吧!天黑了。”荷西大声大气的说,然后一声不响的转进帐篷里
去。这件已成了历史的悲剧,在镇上几乎从来没有被人提起过,我每次看见那个
军曹,心里总要一跳,这样惨痛的记忆,到何年何月才能在他心里淡去?
去年这个时候,这一片被世界遗忘的沙漠突然的复杂起来。北边摩洛哥和南
边毛里塔尼亚要瓜分西属撒哈拉,而沙漠自己的部落又组成了游击队流亡在阿尔
及利亚,他们要独立,西班牙政府举棋不定,态度暧昧,对这一片已经花了许多
心血的属地不知要弃还是要守。
那时候,西班牙士兵单独外出就被杀,深水井里被放毒药,小学校车里找出
定时炸弹,磷矿公司的输送带被纵火,守夜工人被倒吊死在电线上,镇外的公路
上地雷炸毁经过的车辆——这样的不停的骚乱,使得镇上风声鹤唳,政府马上关
闭学校,疏散儿童回西班牙,夜间全面戒严,镇上坦克一辆一辆的开进来,铁丝
网一圈一圈的围满了军事机关。
可怕的是,在边界上西班牙三面受敌,在小镇上,竟弄不清这些骚乱是哪一
方面弄出来的。
在那种情形下,妇女和儿童几乎马上就回西班牙了,荷西与我因没有牵挂,
所以按兵不动,他照常上班,我则留在家里,平日除了寄信买菜之外,公共场所
为了怕爆炸,已经很少去了。一向平静的小镇开始有人在贱卖家具,航空公司门
口每天排长龙抢票,电影院、商店一律关门,留驻的西国公务员都发了手枪,空
气里无端的紧张,使得还没有发生任何正面战争冲突的小镇,已经惶乱不安了。
有一个下午,我去镇上买当日的西班牙报纸,想知道政府到底要把这块土地
怎么办,报纸上没有说什么,每天都说一样的话,我闷闷的慢步走回家,一路上
看见很多棺木放在军用卡车里往坟场开去,我吃了一惊,以为边界跟摩洛哥人已
经打了起来。顺着回家的路走,是必然经过坟场的。沙哈拉威人有两大片自己的
坟场,沙漠军团的公墓却是围着雪白的墙,用一扇空花的黑色铁门关着,墙内竖
着成排的十字架,架下面是一片片平平的石板铺成的墓。我走过去时,公墓的铁
门已经开了,第一排的石板坟都已挖出来,很多沙漠军团的士兵正把一个个死去
的兄弟搬出来,再放到新的棺木里去。
我看见那个情形,就一下明白了,西班牙政府久久不肯宣布的决定,沙漠军
团是活着活在沙漠,死着埋在沙漠的一个兵种,现在他们都将他们的死人都挖了
起来要一同带走,那么西班牙终究是要放弃这片土地了啊!
可怖的是,一具一具的尸体,死了那么多年,在干燥的沙地里再挖出来时,
却不是一堆白骨,而是一个一个如木乃伊般干瘪的尸身。军团的人将他们小心的
抬出来,在烈日下,轻轻的放入新的棺木,敲好钉子,贴上纸条,这才搬上了车
。
因为有棺材要搬出来,观看的人群让了一条路,我被挤到公墓的里面去,这
时,我才发觉那个没有名字的军曹坐在墙的阴影下。看见死人并没有使我不自在
,只是钉棺木的声音十分的刺耳,突然在这当时看见军曹,使我想起,那个夜晚
碰到他酒醉在地上的情形,那夜也是在这坟场附近,这么多年的一件惨事,难道
至今没有使他的伤痛冷淡下来过?
等到第三排公墓里的石板被打开时,这个军曹好似等待了很久似的站了起来
,他大步的走过去,跳下洞里,亲手把那具没有烂掉的尸体像情人一般的抱出来
,轻轻的托在手臂里,静静的注视着那已经风干了的脸,他的表情没有仇恨和愤
怒,我看得见的只是一片近乎温柔的悲怆。
大家等着军曹把尸身放进棺木里去,他,却站在烈日下,好似忘了这个世界
似的。“是他的弟弟,那次一起被杀掉的。”一个士兵轻轻的对另外一个拿着十
字锹的说。
好似有一世纪那么长,这个军曹才迈着步子走向棺木,把这死去了十六年的
亲人,像对待婴儿似的轻轻放入他永远要睡的床里去。这个军曹从门口经过时,
我转开了视线,不愿他觉得我只是一个冷眼旁观的好事者,他经过围观着的沙哈
拉威人时,突然停了一下,沙哈拉威人拉着小孩子们一逃而散。
一排排的棺木被运到机场去,地里的兄弟们先被运走了,只留下整整齐齐的
十字架在阳光下发着耀眼的白色。
那一个清晨,荷西上早班,得五点半钟就出门去,我为着局势已经十分不好
了,所以当天需要车子装些包裹寄出沙漠去,那天我们说好荷西坐交通车去上班
,把车子留下来给我,但是我还是清早就开车把荷西送到搭交通车的地方去。
回程的公路上,为了怕地雷,我一点都不敢抄捷径,只顺着柏油路走,在转
入镇上的斜坡口,我看到汽油的指示针是零了,就想顺道去加油站,再一看表,
还只是六点差十分,我知道加油站不会开着,就转了车身预备回家去。就在那时
距我不远处的街道上,突然发出轰的一声极沉闷的爆炸的巨响,接着一柱黑烟冒
向天空,我当时离得很近,虽然坐在车里,还是被吓得心跳得不得了,我很快的
把车子往家里开去,同时我听见镇上的救护车正鸣叫着飞也似的奔去。
下午荷西回家来问我:“你听见了爆炸声吗?”
我点点头,问着:“伤了人吗?”
荷西突然说:“那个军曹死了。”
“沙漠军团的那个?”我当然知道不会有别人了。“怎么死的?”“他早晨
开车经过爆炸的地方,一群沙哈拉威小孩正在玩一个盒子,盒子上还插了一面游
击队的小布旗子,大概军曹觉得那个盒子不太对,他下了车往那群小孩跑去,想
赶开他们,结果,其中的一个小孩拔出了旗子,盒子突然炸了——。”
“死了几个沙哈拉威小孩?”
“军曹的身体抢先扑在盒子上,他炸成了碎片,小孩子们只伤了两个。”我
茫然的开始做饭给荷西吃,心里却不断的想到早晨的事情,一个被仇恨啃啮了十
六年的人,却在最危急的时候,用自己的生命扑向死亡,去换取了这几个他一向
视做仇人的沙哈拉威孩子的性命。为什么?再也没有想到他会是这样的死去。第
二天,这个军曹的尸体,被放入棺木中,静静的葬在已经挖空了的公墓里,他的
兄弟们早已离开了,在别的土地上安睡了,而他,没有赶得上他们,却静静的被
埋葬在撒哈拉的土地上,这一片他又爱而又恨的土地做了他永久的故乡。
他的墓碑很简单,我过了很久才走进去看了一眼,上面刻着——“沙巴·桑
却士·多雷,一九三二——一九七五。”
我走回家的路上,正有沙哈拉威的小孩们在广场上用手拍着垃圾桶,唱着有
板有眼的歌,在夕阳下,是那么的和平,好似不知道战争就要来临了一样。
一个夏天的夜晚,荷西与我正从家里出来,预备到凉爽的户外去散步,经过
炎热不堪的一天之后,此时的沙漠是如此的清爽而怡人。在这个时候,邻近的沙
哈拉威人都带着孩子和食物在外面晚餐,而夜,其实已经很深了。
等我们走到快近小镇外的坟场时,就看见不远处的月光下有一群年轻的沙哈
拉威人围着什么东西在看热闹,我们经过人堆时,才发觉地上趴着一个动也不动
的西班牙军人,样子像死去了一般,脸色却十分红润,留着大胡子,穿着马靴,
看他的军装,知道是沙漠军团的,身上没有识别阶级的符号。
他趴在那儿可能已经很久了,那一群围着他的人高声的说着阿拉伯话,恶作
剧的上去朝他吐口水,拉他的靴子,踩他的手,同时其中的一个沙啥拉威人还戴
了他的军帽好似小丑一般的表演着喝醉了的人的样子。
对于一个没有抵抗力的军人,沙哈拉威人是放肆而大胆的。“荷西,快回去
把车开来。”我对荷西轻轻的说,又紧张的向四周张望着,在这时候我多么希望
有另外一个军人或者西班牙的老百姓经过这里,但是附近没有一个人走过。
荷西跑回家去开车时,我一直盯着那个军人腰间挂着的手枪,如果有人解他
的枪,我就预备尖叫,下一步要怎么办就想不出来了。那一阵西属撒哈拉沙漠的
年轻人,已经组成了“波里沙里奥人民解放阵线”,总部在阿尔及利亚,可是镇
上每一个年轻人的心几乎都是向着他们的,西班牙人跟沙哈拉威人的关系已经十
分紧张了,沙漠军团跟本地更是死仇一般。
等荷西飞也似的将车子开来时,我们排开众人,要把这个醉汉拖到车子里去
。这家伙是一个高大健壮的汉子,要抬他到车里去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等到我们
全身都汗湿了,才将他在后座放好,关上门,口里说着对不起,慢慢的开出人群
,车顶上仍然被人碰碰的打了好几下。
在快开到沙漠军团的大门时,荷西仍然开得飞快,营地四周一片死寂。“荷
西,闪一闪灯光,按喇叭,我们不知道口令,要被误会的,停远一点。”荷西的
车子在距离卫兵很远的地方停下来了,我们赶快开了车门出去,用西班牙文大叫
:“是送喝醉了的人回来,你们过来看!”两个卫兵跑过来,枪子咔答上了膛,
指着我们,我们指指车里面,动也不动。这两个卫兵朝车里一看,当然是认识的
,马上进车去将这军人抬了出来,口里说着:“又是他!”
这时,高墙上的探照灯刷一下照着我们,我被这种架势吓得很厉害,赶快进
车里去。
荷西开车走时,两个卫兵向我们敬了一个军礼,说:“谢啦!老乡!”我在
回来的路上,还是心有余悸,被人用枪这么近的指着,倒是生平第一次,虽然那
是自己人的部队,还是十分紧张的。有好几天我都在想着那座夜间警备森严的营
区和那个烂醉如泥的军人。过了没多久,荷西的同事们来家里玩,我为了表示待
客的诚意,将冰牛奶倒了一大壶出来。
这几个人看见冰牛奶,像牛喝水似的呼一下就全部喝完了,我赶紧又去开了
两盒。
“三毛,我们喝了你们怎么办?”这两个人可怜兮兮的望着牛奶,又不好意
思再喝下去。
“放心喝吧!你们平日喝不到的。”
食物是沙漠里的每一个人都关心的话题,被招待的人不会满意,跟着一定会
问好吃的东西是哪里来的。
等荷西的同事在那一个下午喝完了我所有盒装的鲜奶,见我仍然面不改色,
果然就问我这是哪儿买来的了。
“嘿!我有地方买。”我得意的卖着关子。
“请告诉我们在哪里!”
“啊!你们不能去买的,要喝上家里来吧!”
“我们要很多,三毛,拜托你讲出来啊!”
我在沙漠军团的福利社买的。”“军营?你一个女人去军营买菜?”他们叫
了起来,一副老百姓的呆相。“军眷们不是也在买?我当然跑去了。”
“可是你是不合规定的老百姓啊!”
“在沙漠里的老百姓跟城里的不同,军民不分家。”我笑嘻嘻的说。“军人
,对你还有礼貌吗?”
“太客气了,比镇上的普通人好得多了。”
“请你代买牛奶总不会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的,要几盒明天开单子来吧!”
第二天荷西下班回来,交给我一张牛奶单,那张单子上列了八个单身汉的名
字,每个人每星期希望我供应十盒牛奶,一共是八十盒。我拿着单子咬了咬嘴唇
,大话已经说出去了,这八十盒牛奶要我去军营买,却实在是令人说不出口。
在这种情形下,我情愿丢一次脸,将这八十盒羞愧的数量一次买清,就不再
出现,总比一天去买十盒的好。
隔了一天,我到福利社里去买了一大箱十盒装的鲜乳,请人搬来放在墙角,
打一个转,再跑进去,再买一箱,再放在墙角,过了一会儿,再进去买,这样来
来去去弄了四次,那个站柜台的小兵已经晕头转向了。
“三毛,你还要进进出出几次?”
“还有四次,请忍耐一点。”
“为什么不一次买?都是买牛奶吗?”
“一次买不合规定,太多了。”我怪不好意思的回答着。“没关系,我现在
就拿给你,请问你一次要那么多牛奶干嘛?”“别人派我来买的,不全是我的。
”
等我把八大箱牛奶都堆在墙角,预备去喊计程车时,我的身边刷一下停下了
一辆吉普车,抬头一看,吓了一跳,车上坐着的那个军人,不就是那天被我们抬
回营区去的醉汉吗?
这个人是高大的,精神的,制服穿得很合身,大胡子下的脸孔看不出几岁,
眼光看人时带着几分霸气又嫌过分的专注,胸膛前的上衣扣一直开到第三个扣子
,留着平头,绿色的船形军帽上别着他的阶级——军曹。
我因为那天晚上没有看清楚他,所以刻意的打量了他一下。他不等我说话,
跳下车来就将小山也似的箱子一个一个搬上了车,我看牛奶已经上车了,也不再
犹豫,跨上了前座。
“我住在坟场区。”我很客气的对他说。
“我知道你住在那里。”他粗声粗气的回答我,就将车子开动了。我们一路
都没有说话,他的车子开得很平稳,双手紧紧的握住方向盘,等车子经过坟场时
,我转过头去看风景,生怕他想起来那个晚上酒醉失态被我们捡到的可怜样子会
受窘。到了我的住处,他慢慢的煞车,还没等他下车,我就很快的跳下来了,因
为不好再麻烦这个军曹搬牛奶,我下了车,就大声叫起我邻近开小杂货店的朋友
沙仑来。
沙仑听见我叫他,马上从店里趿着拖鞋跑出来了,脸上露着谦卑的笑容。等
他跑到吉普车面前,发现有一个军人站在我旁边,突然顿了一下,接着马上低下
了头赶快把箱子搬下来,那个神情好似看见了凶神一般。这时,送我回来的军曹
,看见沙仑在替我做事,又抬眼望了一下沙仑开的小店,突然转过眼光来鄙夷的
盯了我一眼,我非常敏感的知道,他一定是误会我了,我胀红了脸,很笨拙的辩
护着:“这些牛奶不是转卖的,真的!请相信我,我不过是——。”他大步跨上
了车子,手放在驾驶盘上拍了一下,要说什么又没说,就发动起车子来。
我这才想起来跑了过去,对他说:“谢谢你,军曹!请问贵姓?”他盯住我
,好似已经十分忍耐了似的对我轻轻的说:“对沙哈拉威人的朋友,我没有名字
。”
说完就把油门一踏,车子飞也似的冲了出去。
我呆呆的望着尘埃,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被人冤枉了,不给我解释的余地
,问他的名字,居然被他无礼的拒绝了。
“沙仑,你认识这个人?”我转身去问沙仑。
“是。”他低声说。“干什么那么怕沙漠军团,你又不是游击队?”
“不是,这个军曹,他恨我们所有的沙哈拉威人。”
“你怎么知道他恨你?”
“大家都知道,只有你不知道。”
我刻意的看了老实的沙仑一眼,沙仑从来不说人是非,他这么讲一定有他的
道理。从那次买牛奶被人误会了之后,我羞愧得很久不敢去军营买菜。隔了很久
,我在街上遇见了福利社的小兵,他对我说他们队上以为我走了,又问我为什么
不再去买菜,我一听他们并没有误会我的意思,这才又高兴的继续去了。
运气就有那么不好,我又回军营里买菜的第一天,那个军曹就跨着马靴大步
的走进来了,我咬着嘴唇紧张的望着他,他对我点点头,说一声:“日安!”就
到柜台上去了。
对于一个如此不喜欢沙哈拉威人的人,我将他解释成“种族歧视”,也懒得
再去理他了,站在他旁边,我专心向小兵说我要买的菜,不再去望他。
等我付钱时,我发觉旁边这个军曹翻起袖子的手臂上,居然刻了一大排纹身
刺花,深蓝色的俗气情人鸡心下面,又刺了一排中号的字——“奥地利的唐璜”
。
我奇怪得很,因为我本来以为刺花的鸡心下面一定是一个女人的名字,想不
到却是个男人的。
“喂!‘奥地利的唐璜’是谁?是什么意思?”
等那个军曹走了,我就问柜台上沙漠军团的小兵。
“啊!那是沙漠军团从前一个营区的名字。”
“不是人吗?”“是历史上加洛斯一世时的一个人名,那时候奥地利跟西班
牙还是不分的,后来军团用这名字做了一个营区的称呼,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可是,刚刚那个军曹,他把这些字都刻在手臂上哪!”
我摇了摇头,拿着找回来的钱,走出福利社的大门去。
在福利社的门口,想不到那个军曹在等我,他看见了我,头一低,跟着我大
步走了几步,才说:“那天晚上谢谢你和你先生。”“什么事?”我不解的问他
。
“你们送我回去,我——喝醉了。”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个人真奇怪,突然来谢我一件我已忘记了的事情,上次他送我回去时怎么
不谢呢?
“请问你,为什么沙哈拉威人谣传你恨他们?”我十分鲁莽的问他。“我是
恨。”他盯住我看着,而他如此直接的回答使我仍然吃了一惊。“这世界上有好
人也有坏人,并不是那一个民族特别的坏。”我天真的在讲一句每一个人都会讲
的话。
军曹的眼光掠向那一大群在沙地上蹲着的沙哈拉威人,脸色又一度专注得那
么吓人起来,好似他无由的仇恨在燃烧着他似的可怖。我停住了自己无聊的话,
呆呆的看着他。
他过了几秒钟才醒过来,对我重重的点了一下头,就大步的走开去。这个刺
花的军曹,还是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他的手臂,却刻着一整个营区的名称,而
这为什么又是好久以前的一个营区呢?有一天,我们的沙哈拉威朋友阿里请我们
到离镇一百多里远的地方去,阿里的父亲住在那儿的一个大帐篷里,阿里在镇上
开计程车,也只有周末可以回家去看看父母。
阿里父母住的地方叫“魅赛也”,可能在千万年前是一条宽阔的河,后来枯
干了,两岸成了大峡谷似的断岩,中间河床的部份有几棵椰子树,有一汪泉水不
断的流着,是一个极小的沙漠绿洲。这样辽阔的地方,又有这么好的淡水,却只
住了几个帐篷的居民,令我十分不解。在黄昏的凉风下,我们与阿里的父亲坐在
帐篷外,老人悠闲的吸着长烟斗,红色的断崖在晚霞里分外雄壮,天边第一颗星
孤伶伶的升起了。
阿里的母亲捧着一大盘“古斯格”和浓浓的甜茶上来给我们吃。我用手捏着
“古斯格”把它们做成一个灰灰的面粉团放到口里去,在这样的景色下,坐在地
上吃沙漠人的食物才相称。“这么好的地方,又有泉水,为什么几乎没有人住呢
?”我奇怪的问着老人。“以前是热闹过的,所以这片地方才有名字,叫做‘魅
赛也’,后来那件惨案发生,旧住着的人都走了,新的当然不肯再搬来,只余下
我们这几家在这里硬撑着。”
“什么惨案?我怎么不知道?是骆驼瘟死了吗?”我追问着老人。老人望了
我一眼,吸着烟,心神好似突然不在了似的望着远方。“杀!杀人!血流得当时
这泉水都不再有人敢喝。”
“谁杀谁?什么事?”我禁不住向荷西靠过去,老人的声音十分神秘恐怖,
夜,突然降临了。
“沙哈拉威人杀沙漠军团的人。”老人低低的说,望着荷西和我。“十六年
前,‘魅赛也’是一片美丽的绿洲,在这里,小麦都长得出来,椰枣落了一地,
要喝的水应有尽有,沙哈拉威人几乎全把骆驼和山羊赶到这里来放牧,扎营的帐
篷成千上万——”老人在诉说着过去的繁华时,我望着残留下来的几棵椰子树,
几乎不相信这片枯干的土地也有过它的青春。
“后来西班牙的沙漠军团也开来了,他们在这里扎营,住着不走——。”老
人继续说。
“可是,那时候的撒哈拉沙漠是不属于任何人的,谁来都不犯法。”我插嘴
打断他。
“是,是,请听我说下去——”老人比了一个手势。
“沙漠军团来了,沙哈拉威人不许他们用水,两方面为了争水,常常起冲突
,后来——”
我看老人不再讲下去,就急着问他:“后来怎么了?”
“后来,一大群沙哈拉威人偷袭了营房,把沙漠军团全营的人,一夜之间在
睡梦里杀光了。统统用刀杀光了。”
我张大了眼睛,隔着火光定定的望着老人,轻轻的问他:“你是说,他们统
统被杀死了?一营的人被沙哈拉威人用刀杀了?”“只留了一个军曹,他那夜喝
醉了酒,跌在营外,醒来他的伙伴全死了,一个不留。”
“你当时住在这里?”我差点没问他:“你当时参加了杀人没有?”“沙漠
军团是最机警的兵团,怎么可能?”荷西说。
“他们没有料到,白天奔驰得太厉害,卫兵站岗又分配得不多,他们再没有
料到沙哈拉威人拿刀杀进来。”
“军营当时扎营在哪里?”我问着老人。
“就在那边!”老人用手指着泉水的上方,那儿除了沙地之外,没有一丝人
住过的痕迹。“从那时候起,谁都不喜欢住在这里,那些杀人的当然逃了,一块
好好的绿洲荒废成这个样子。”
老人低头吸烟,天已经暗下来了,风突然厉裂的吹拂过来,夹着呜呜的哭声
,椰子树摇摆着,帐篷的支柱也吱吱的叫起来。我抬头望着黑暗中远方十六年前
沙漠军团扎营的地方,好似看见一群群穿军装的西班牙兵在跟包着头举着大刀的
沙哈拉威人肉搏,他们一个一个如银幕上慢动作的姿势在刀下倒下去,成堆的人
流着血在沙地上爬着,成千无助的手臂伸向天空,一阵阵无声的呐喊在一张张带
血的脸上嘶叫着,黑色的夜风里,只有死亡空洞的笑声响彻在寂寞的大地上——
我吃了一惊,用力眨一下眼睛,什么都不见了,四周安详如昔,火光前,坐
着我们,大家都不说话。
我突然觉得寒冷,心里闷闷不乐,这不只是老人所说的惨案,这是一场血淋
淋的大屠杀啊!
“那个唯一活着的军曹——就是那个手上刺着花,老是像狼一样盯着沙哈拉
威人的那一个?”我又轻轻的问。“他们过去是一个团结友爱的营,我还记得那
个军曹酒醒了在他死去的兄弟尸体上像疯子一样扑跌发抖的样子。”
我突然想到那个人手上刺着营名的纹身。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我问着。
“那件事情之后,他编在镇上的营区去,从那时候他就不肯讲名字,他说全
营的弟兄都死了,他还配有名字吗?大家都只叫他军曹。”过去那么多年的旧事
了,想起来依然使我毛骨悚然,远处的沙地好似在扭动一般。
“我们去睡吧!天黑了。”荷西大声大气的说,然后一声不响的转进帐篷里
去。这件已成了历史的悲剧,在镇上几乎从来没有被人提起过,我每次看见那个
军曹,心里总要一跳,这样惨痛的记忆,到何年何月才能在他心里淡去?
去年这个时候,这一片被世界遗忘的沙漠突然的复杂起来。北边摩洛哥和南
边毛里塔尼亚要瓜分西属撒哈拉,而沙漠自己的部落又组成了游击队流亡在阿尔
及利亚,他们要独立,西班牙政府举棋不定,态度暧昧,对这一片已经花了许多
心血的属地不知要弃还是要守。
那时候,西班牙士兵单独外出就被杀,深水井里被放毒药,小学校车里找出
定时炸弹,磷矿公司的输送带被纵火,守夜工人被倒吊死在电线上,镇外的公路
上地雷炸毁经过的车辆——这样的不停的骚乱,使得镇上风声鹤唳,政府马上关
闭学校,疏散儿童回西班牙,夜间全面戒严,镇上坦克一辆一辆的开进来,铁丝
网一圈一圈的围满了军事机关。
可怕的是,在边界上西班牙三面受敌,在小镇上,竟弄不清这些骚乱是哪一
方面弄出来的。
在那种情形下,妇女和儿童几乎马上就回西班牙了,荷西与我因没有牵挂,
所以按兵不动,他照常上班,我则留在家里,平日除了寄信买菜之外,公共场所
为了怕爆炸,已经很少去了。一向平静的小镇开始有人在贱卖家具,航空公司门
口每天排长龙抢票,电影院、商店一律关门,留驻的西国公务员都发了手枪,空
气里无端的紧张,使得还没有发生任何正面战争冲突的小镇,已经惶乱不安了。
有一个下午,我去镇上买当日的西班牙报纸,想知道政府到底要把这块土地
怎么办,报纸上没有说什么,每天都说一样的话,我闷闷的慢步走回家,一路上
看见很多棺木放在军用卡车里往坟场开去,我吃了一惊,以为边界跟摩洛哥人已
经打了起来。顺着回家的路走,是必然经过坟场的。沙哈拉威人有两大片自己的
坟场,沙漠军团的公墓却是围着雪白的墙,用一扇空花的黑色铁门关着,墙内竖
着成排的十字架,架下面是一片片平平的石板铺成的墓。我走过去时,公墓的铁
门已经开了,第一排的石板坟都已挖出来,很多沙漠军团的士兵正把一个个死去
的兄弟搬出来,再放到新的棺木里去。
我看见那个情形,就一下明白了,西班牙政府久久不肯宣布的决定,沙漠军
团是活着活在沙漠,死着埋在沙漠的一个兵种,现在他们都将他们的死人都挖了
起来要一同带走,那么西班牙终究是要放弃这片土地了啊!
可怖的是,一具一具的尸体,死了那么多年,在干燥的沙地里再挖出来时,
却不是一堆白骨,而是一个一个如木乃伊般干瘪的尸身。军团的人将他们小心的
抬出来,在烈日下,轻轻的放入新的棺木,敲好钉子,贴上纸条,这才搬上了车
。
因为有棺材要搬出来,观看的人群让了一条路,我被挤到公墓的里面去,这
时,我才发觉那个没有名字的军曹坐在墙的阴影下。看见死人并没有使我不自在
,只是钉棺木的声音十分的刺耳,突然在这当时看见军曹,使我想起,那个夜晚
碰到他酒醉在地上的情形,那夜也是在这坟场附近,这么多年的一件惨事,难道
至今没有使他的伤痛冷淡下来过?
等到第三排公墓里的石板被打开时,这个军曹好似等待了很久似的站了起来
,他大步的走过去,跳下洞里,亲手把那具没有烂掉的尸体像情人一般的抱出来
,轻轻的托在手臂里,静静的注视着那已经风干了的脸,他的表情没有仇恨和愤
怒,我看得见的只是一片近乎温柔的悲怆。
大家等着军曹把尸身放进棺木里去,他,却站在烈日下,好似忘了这个世界
似的。“是他的弟弟,那次一起被杀掉的。”一个士兵轻轻的对另外一个拿着十
字锹的说。
好似有一世纪那么长,这个军曹才迈着步子走向棺木,把这死去了十六年的
亲人,像对待婴儿似的轻轻放入他永远要睡的床里去。这个军曹从门口经过时,
我转开了视线,不愿他觉得我只是一个冷眼旁观的好事者,他经过围观着的沙哈
拉威人时,突然停了一下,沙哈拉威人拉着小孩子们一逃而散。
一排排的棺木被运到机场去,地里的兄弟们先被运走了,只留下整整齐齐的
十字架在阳光下发着耀眼的白色。
那一个清晨,荷西上早班,得五点半钟就出门去,我为着局势已经十分不好
了,所以当天需要车子装些包裹寄出沙漠去,那天我们说好荷西坐交通车去上班
,把车子留下来给我,但是我还是清早就开车把荷西送到搭交通车的地方去。
回程的公路上,为了怕地雷,我一点都不敢抄捷径,只顺着柏油路走,在转
入镇上的斜坡口,我看到汽油的指示针是零了,就想顺道去加油站,再一看表,
还只是六点差十分,我知道加油站不会开着,就转了车身预备回家去。就在那时
距我不远处的街道上,突然发出轰的一声极沉闷的爆炸的巨响,接着一柱黑烟冒
向天空,我当时离得很近,虽然坐在车里,还是被吓得心跳得不得了,我很快的
把车子往家里开去,同时我听见镇上的救护车正鸣叫着飞也似的奔去。
下午荷西回家来问我:“你听见了爆炸声吗?”
我点点头,问着:“伤了人吗?”
荷西突然说:“那个军曹死了。”
“沙漠军团的那个?”我当然知道不会有别人了。“怎么死的?”“他早晨
开车经过爆炸的地方,一群沙哈拉威小孩正在玩一个盒子,盒子上还插了一面游
击队的小布旗子,大概军曹觉得那个盒子不太对,他下了车往那群小孩跑去,想
赶开他们,结果,其中的一个小孩拔出了旗子,盒子突然炸了——。”
“死了几个沙哈拉威小孩?”
“军曹的身体抢先扑在盒子上,他炸成了碎片,小孩子们只伤了两个。”我
茫然的开始做饭给荷西吃,心里却不断的想到早晨的事情,一个被仇恨啃啮了十
六年的人,却在最危急的时候,用自己的生命扑向死亡,去换取了这几个他一向
视做仇人的沙哈拉威孩子的性命。为什么?再也没有想到他会是这样的死去。第
二天,这个军曹的尸体,被放入棺木中,静静的葬在已经挖空了的公墓里,他的
兄弟们早已离开了,在别的土地上安睡了,而他,没有赶得上他们,却静静的被
埋葬在撒哈拉的土地上,这一片他又爱而又恨的土地做了他永久的故乡。
他的墓碑很简单,我过了很久才走进去看了一眼,上面刻着——“沙巴·桑
却士·多雷,一九三二——一九七五。”
我走回家的路上,正有沙哈拉威的小孩们在广场上用手拍着垃圾桶,唱着有
板有眼的歌,在夕阳下,是那么的和平,好似不知道战争就要来临了一样。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7-02-01
仇恨能让人有惊人的力量,但是破坏力也让人吃惊.它不但破坏被憎恨的人,更可怕的是它让携带憎恨的人万劫不复.
我跟你正好是同龄人.23岁.那我就跟你讲一个咱们的同龄人吧.
说到农村,邻里关系是不好处.
我有个把兄弟,他是重庆人,也是家住农村.他父母由于长年在矿里,已经积劳成疾了.我这个兄弟还有个妹妹.所以你看他们家很是穷苦.十里八乡的乡亲都认识他们家,也都知道他们家是最苦的.很多人很帮助他们,单他们的邻居很欺负他们.后来 我这个兄弟考上了我们学校,是西南地区绝对数一数二的学校.于是十里八乡的乡亲又都很羡慕他们家.也单是这个邻居,嫉妒他们.我这个兄弟不但不用家里的钱,他勤工俭学养自己,供妹妹读书,还寄钱给父母用.这下这个邻居就更难受了.有一次这个邻居跟我兄弟家打了起来.我兄弟当时跟你心情差不多,就非让我介绍师父教他练武术.
我对他说你要练就得练十年八载,就为了跟邻居打架?于是他就想通了.反正邻居就是没他有出息,那还有什么好憎恨呢?最多只是很瞧不起这个人而已.
你说你要有出息,这是应该的,但是目的不是报复.你用不着报复什么,因为他们对你不会构成任何威胁,而你也大可以不屑一顾他们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我跟你正好是同龄人.23岁.那我就跟你讲一个咱们的同龄人吧.
说到农村,邻里关系是不好处.
我有个把兄弟,他是重庆人,也是家住农村.他父母由于长年在矿里,已经积劳成疾了.我这个兄弟还有个妹妹.所以你看他们家很是穷苦.十里八乡的乡亲都认识他们家,也都知道他们家是最苦的.很多人很帮助他们,单他们的邻居很欺负他们.后来 我这个兄弟考上了我们学校,是西南地区绝对数一数二的学校.于是十里八乡的乡亲又都很羡慕他们家.也单是这个邻居,嫉妒他们.我这个兄弟不但不用家里的钱,他勤工俭学养自己,供妹妹读书,还寄钱给父母用.这下这个邻居就更难受了.有一次这个邻居跟我兄弟家打了起来.我兄弟当时跟你心情差不多,就非让我介绍师父教他练武术.
我对他说你要练就得练十年八载,就为了跟邻居打架?于是他就想通了.反正邻居就是没他有出息,那还有什么好憎恨呢?最多只是很瞧不起这个人而已.
你说你要有出息,这是应该的,但是目的不是报复.你用不着报复什么,因为他们对你不会构成任何威胁,而你也大可以不屑一顾他们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7-02-01
化悲痛为动力,但不要去怨恨别人。
别人怎么做是别人,你做好你,问心无愧,堂堂正正就好了。
怨恨只会让一个人更快的迷失自我,走上不归路。
摆正心态,端正态度,努力去改变自己当前的不顺才是你应该做的,你应该想着是为了父母家人生活得更好,为了自己出人头地。不要去管其他人,他怎么样都与你无关的。
仔细想想,你还年轻,还有时间有精力有能力,等到了白了头的时候后悔可就晚了!
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在给你一件东西的同时当然会从你身边带走一样,只不过有的人是先享福后吃苦,而有的是先吃苦后享福罢了。
加油吧!
能这样想就对啦,年轻人!
别人怎么做是别人,你做好你,问心无愧,堂堂正正就好了。
怨恨只会让一个人更快的迷失自我,走上不归路。
摆正心态,端正态度,努力去改变自己当前的不顺才是你应该做的,你应该想着是为了父母家人生活得更好,为了自己出人头地。不要去管其他人,他怎么样都与你无关的。
仔细想想,你还年轻,还有时间有精力有能力,等到了白了头的时候后悔可就晚了!
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在给你一件东西的同时当然会从你身边带走一样,只不过有的人是先享福后吃苦,而有的是先吃苦后享福罢了。
加油吧!
能这样想就对啦,年轻人!
第3个回答 2007-02-01
有一些人天生就是基因差!小市民基因!没办法!你看着它的时候就像看垃圾一样就行了!我所在地区这种人多了~我就是跟这些小市民和不来,它们天生也跟我和不来!我们的基因优秀嘛~
还有就是利用这一点激发自己的斗志也不错啊~我就是这样干的~
还有就是利用这一点激发自己的斗志也不错啊~我就是这样干的~
第4个回答 2007-02-01
寒山问拾得:“世间谤我,贱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答曰:“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参考资料:百度知道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