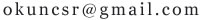爸爸是我最敬佩的人
我有一位和蔼可亲的爸爸他个子不高,中等身材,头上长满了浓密的头发,一双有神的大眼睛,好像永远都不知疲倦。也许是年纪大了,所以脸上刻满了不深不浅的皱纹。他是我尊敬的人!
爸爸是一位木匠,他对工作十分认真,经常为了工作,做工到深夜。
夜深了,时钟刚响了12声,我刚从甜梦里醒过来,屋外传来的阵阵“叭叭叭”的声音。啊!我的爸爸还在工作呢?我想爸爸长期这样下去。身体会垮下来,想到这里,我便下了床来到爸跟前,只见爸爸满头大汗,正聚精会神地工作着,他用划刀将木板割开,然后把一断长条形的方木锯成几断,最后用锤子迅速地把铁钉将木板和方木使劲地钉在一起,不一会儿就做成一张木椅子,爸爸的手艺是多么高超!”您怎么还不睡,爸爸?”。我问他,他只是随口答应我,“你去睡吧!”我真不想离开爸爸,可我又说不服他,只好呆呆地站在一旁看看,他那灵巧的手不停地工作,好像不知首疲倦,那手上的锤子好像是他的老交情了,一点儿也没锤他的手上,要是我去做,那锤子一定不会认我的。
爸爸整天这么干,但他的两眼睛依然是那么有神,这一次,爸爸又得到了一项任务,要在一个月内完成一个巨型组合柜,这一下,可把爸爸忙坏了。为了依时完成任务。爸爸没日没夜地干。放学回家,我第一眼就见爸爸蹲地上忙个不停,直到夜深了。这叭叭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响着,怎么才能使他休息一会呢?我苦苦思索。这时,爸爸看见了,问:“你怎么还不去睡?”我想到爸爸平时非常疼爱我,就故意说:”你不去睡,我也不去睡。“傻孩子,你就去睡吧。”“不,我们要一同睡。”爸爸说:“唉!真拿你没办法。”爸爸只好收拾工具,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我想了个办法,把他的工具藏了起来,爸爸很快地吃过晚饭,放下碗筷就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了,不一会儿,就听见他大声喊:叫我的工具呢?”我假装没听见。妈妈走过来,帮爸爸一齐寻找,后来,妈妈走到我的面前,问:“你看见过爸爸的工具吗?”我的脸虽然红了,但仍然沉着地说:“不知道,”爸爸露出了焦急的心情, 自言自语地说:“要是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呢?”我不忍心看到他这样子,偷偷地把他的工具藏在一个既
没找过,又明显的地方。爸爸很快地找到了。又开始了工作。
刀和锤子又在爸爸手中忙碌起来,仿佛也在不满地说:“哎,这样没完没了地干,你熬得住,我可受不了!”可爸爸却越干越起劲,啊,这是我的爸爸,他那勤劳苦干的美德,将是我永远的榜样。
爸爸,您是我最敬佩的人
爸爸一生勤劳,朴素,只知道吃苦,不懂得享受生活。爸爸是我这一生最敬佩的人!
爸爸年轻时就一直从事建筑行业工作,因为家庭原因,他只能靠自己努力。刚开始爸爸只是一个小瓦工,和泥,垒墙,给别人盖房子。在不断的工作中,他凭着自己的一股干劲,用只有初中文化的底子,学会了建筑专业的预结算及绘图等。他没上过一天建筑学校,全靠自学。那种毅力是难以想像的。没有什么基础,没有老师教,也没有任何人帮他。但他就是凭着自己对建筑的热爱,对那份工作的执着,楞是自学完了所有课程。
爸爸是我学习的榜样,当我向他请教问题时,他对每一个问题除了给我解答,还能很快在书上找到。好像他的脑子里印那些书的每一页。我真是太佩服我的爸爸了。就是上学时老师教过的课本也不一定能立刻找到,更何况是自己学习的课本呢!
爸爸,您是我最敬佩的人!我要向您学习!
最敬佩的人—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中国亿万民众中的普通一员,没有特别显赫的声望和地位。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他足以和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位开疆辟土的君主相媲美,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佩的人。
父亲出身于中国民众的最底层:农民家庭。虽然他非常喜欢读书,但初中毕业后,还是就不得不缀学务农。做为老大,他的下面还有八个弟妹要照顾。
当时的农村还在吃大锅饭。当地地少人多、土地贫瘠,生产队连年“涨肚”(当地土话,即亏损)。年终结算时,不但分不到半点钱、粮,还倒欠队里的钱。但是,人活着总要吃饭、穿衣啊。到了冬天,没农活的时候,父亲就去河里捕鱼。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轰轰烈烈,这种事情如果被抓住了,是要挨批斗的。只能偷偷地去。早晨,天不亮就出门,晚上,要等天黑透了才能回家。捕鱼的工具也很简单:用一根粗圆木,一头削尖,再包上一层铁皮,顶端钉上一根铁刺,就做成了简陋的冰穿子,再带上一张鱼网就行了。到了河中间,选择一个水深的地方,先用冰穿子破冰,在冰面上砸出一个大小合适的窟窿,然后开始下网。冬季冰下缺氧,冰面出现裂口后,如果附近有鱼,鱼就会游过来透气,这时就可以收网了。但破冰和收网的过程都很危险。万一将冰面砸出大的裂缝或砸开的面积过大,冰面就很容易塌陷。如果不小心掉进去,身上穿着的厚厚的棉祅、棉裤立刻被水浸湿,会猛然增加几十斤的重量,刺骨的冰水不用十分钟就能把人冻僵。在水下又很难找到冰口的位置。基本上,如果掉下去,就没有再上来的希望了。那时候,人穷,河也瘦。一天砸上十几个冰窟窿,也网不到几条鱼。就这样,父亲冒着危险,连续打了三年鱼,可是自己家就连过年都没舍得吃上一条,全都悄悄拿到镇上卖掉了,换回来米和盐。
父亲想买一件夏天穿的汗背心,计划了几年也没余钱买。到了夏季的三伏天,上工时,他还穿着那件秋天的大褂,热得汗流夹背。一进家门,脱了衣服,就只能光膀子,家里来客人时再穿上。
到了第四年,父亲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 ”,听说大兴安岭是个“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的富饶之地,父亲决定把全族人搬迁到那里。可是往那里跑了很多次,那边没有一个生产队愿意按纳他们。因为每个队的土地数量是固定的,人口一多,年终人均分配的口粮就会减少,所以人家都不愿意。只有一种办法叫做“以姑娘带户”,就是把自家女孩嫁给当地生产队的男孩子,这样可以让女孩子的娘家人落户。可是,这样,一般情况下,漂亮女孩只能嫁给那些有残疾的、讨不到老婆的光棍,造成不幸的婚姻。而且,也不能解决全族人的问题。
没办法,父亲决定在那里自己新组建一个生产队。他用几个月的时间,把选址、办理迁移的一切手续都办完。在1971年的春天,全族二十几户人家开始了浩浩荡荡的集体搬家。因为路途遥远,只带上了一些生产、生活必需品。包括粮食、衣物、农具、锅碗瓢盆、部分鸡鸭鹅狗。都说穷家值万贯呐!就是这样,也足够壮观的,一路上,孩儿哭,狗儿叫,从火车到汽车,人人侧目。
在到达他们的新建生产队之后,真正的创业才开始了。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坳、一块较为平坦的荒原。首先,他们要建起能住人的房子,然后要打井,修路,还要开辟出能种庄稼的农田。全体有劳动能力的一齐动手。先砍倒小树,扎了几个马架子,也就是窝棚。二十几户人家先住进去。然后再伐木、盖房。
吃饭只能在野地里。支起三块石头,架上大铁锅,折来树枝当柴烧,舀来河水,就开始煮大碴粥了。因为没有锅盖,锅底的粥已经糊了,上面的米还生着呢。风一吹过来,土沫、草叶都刮到粥里,成了不请自来的特殊调味品。当时我二周岁,已经记得很多事情。他们给了我一个断了柄的茶杯当做饭碗。虽然我饿得绕着饭锅咽口水,可是那种又夹生又糊的饭还是难以下咽。如果遇到下雨天,就吃不上饭了,只能等雨停了再做。
那时盖房子也没办法讲究。先做土坯,到大甸子(河边有草的湿地)上用平铲切割出长方形泥块,晒干了就可以切墙。河边都是河水冲刷出的淤泥,土质黏腻,中间又连着很多草茎,不易裂开,拿来砌墙较为耐用。再砍粗木做立柱和房梁,细木随便砍二斧,稍微砍直一些,就做了门窗。房顶盖苫草。房子盖好一座,就搬出一户。那时候哪有玻璃呀,所谓窗户也只是个大木头框子,小窗格都没来得及装。晚上睡觉时就挂起一幅幔帐(一种布做的帘子)当窗帘。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我忽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大人们都叫喊着冲了出去,说是狼来了,咬死了二只羊。我吓得躲在幔帐后面瑟瑟发抖,怕被狼叨了去。
运来的粮食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摞在一个马架子里。如果上面的是大碴子,就只能天天吃大碴子。吃上二、三个月,一直到大碴子吃完了,才能搬出下面的小米。唯一的好处是:全村男女老少都不必费心猜想今天吃什么饭,反正每天都是一个样。等房子盖得差不多时,父亲才发现,粮食已所剩无几。他连忙坐火车回老家去筹运粮食。父亲虽然走了没几天,可是这边的人多啊,一百多口人很快就断顿了。这时,母亲想起了一个路过这里的讨饭老人,老头把讨来的小半袋米放在这儿,让我们代为保管的。大家没办法,把这些米也吃了。那是真正的百家米啊!各个品种、各种成色的粮食混杂在一起。好在百家米吃完后,终于等来了父亲的粮食。老人再来时,我们还给他一袋新来,并对他千恩万谢,他救了我们一族人呐!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那位老人家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愿他老人家的灵魂在天国里得到安息!
新建的生产队有很多事情要办,父亲不停地往返于新建队和公社之间。二者相距60华里,交通工具只有二条腿。那时候,对他们来说,自行车比现在的高档轿车还稀奇,穷乡僻壤是难得一见的。买是没钱买,借也没处借啊!一次,为了办一件事,父亲在一天之内,在两地之间走了三个来回,到最后实在走不动了,只好折了根树枝当拐杖拄着走。妈妈给他做的千层底的布鞋,他只穿三天就磨破了底。
当时开荒种地也是异常艰辛的:伐倒树木、刨掉树根、割去杂草,再用镐头一镐一镐地翻整土地,打碎土块,整理出垄台和垄沟。然后,才能种上庄稼。这种开恳土地的方法,俗称“刨镐头荒”。因为没有铧犁和大牲口,全村大部分土地都是这样一镐一镐地刨出来的。头二年,土地还是很生,庄稼不会长得太好,只有在经过两年不停地翻整、施肥之后才会成为熟地,庄稼的长势才会好。
二爷爷从老家来看他们时,遍寻父亲不见,众人把一个瘦骨嶙峋、胡子拉碴、弯腰驼背的小老头指给他看。二爷爷当时就哭了,说:“好侄子,你受了多大罪呀!你才二十三岁呀!”
这一切的付出都没有白费,到了80年代初,那里已盖起了第二代砖瓦房,家家都有小四轮拖拉机,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普通人家年收入三、四万元。1987年,国家农业部搞了一次全国百名种粮大王抨比。结果评出的首名粮王,不在鱼米之乡的江南,而是在我们那个村附近,名叫赵宏玉。
因为附近出产铁矿石,那个村被命名为铁矿小队。直到现在,那里80%以上都是我的族人,他们都是同一个姓氏。父亲先后做过小队会计、大队会计。最后调到公社以工代干。
1981年,父亲调到公社农业经营管理站担任站长。当时各公社的农经站归条条管理,属于市农业局的派出机构。每到年头年尾,需要写计划、总结时,市农业局的小轿车就会开上四个多小时,到公社把父亲接到市局,执笔写报告,写完后再把他送回来。需要他汇总的不是一个公社的情况,而是全市二十三公社的总体农业情况。市农业局、再加上各农经站的员工有一百多人,比他学历高的人比比皆是。但是这个初中生的文笔却是首屈一指,有口皆碑的。虽然经历了早年失学之痛和种种生活的磨难。父亲却从未放弃过学习,他自学了文学、财务等很多课程。
从那以后,父亲先后担任了农业局干事、副乡长、乡长、乡党委书记、市畜牧局副局长等职务。
父亲走上经商之路纯属偶然。当时小叔叔开了二个商店和一个小公司,经营家用电器和音像制品。因为经营和个人感情同时出现问题,一向在几个兄长的呵护下长大、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的小叔叔弃商而逃,远走它乡。债主差点挤破门坎。总得有人收拾烂摊子啊!按规定,干部不允许经商,父亲只能辞职,放弃这个经过多年奋斗,并读了三年电大才换来的干部身份。就在他的升任旗长(少数民族地区的职务设置,等于县长)的调令下来的那天,他递交了提前退休申请。
经商之路总是充满曲折,难以预测。有时就会“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在东拼西凑终于还清欠款,并努力经营积累了一定的家底后,在他经商的那条电器商业街,有一家店面失火,导致火烧连营,价值几十万元的货物化为乌有。亲戚、朋友都以为父亲这次肯定再也爬起不来了,一个个远离而去。那段时间,父亲既盼着电器厂的送货车能早点来,因为有货才能卖出钱。可是又怕它来,因为货款根本没有着落,亲友早已借无可借。每当送货车要来的前二天,他就早早地在大街上站着,看看能不能遇到熟人,还能不能借到点钱。当时我早已离开家乡。每当想起妹妹向我描述的这些,我都忍不住心酸落泪。
在经营了多种项目之后,父亲成立了物业管理公司,是我们那里附近几个城市的首家私营物业公司,在以后的几年里,也是唯一的一家。业务覆盖了几个县级市。父亲以前单位有个同事老赵,听说父亲现在经商发了,就特地前来投靠。可是,老赵下了火车之后却怎么也找不对地方,原来别人给他的是旧的地址。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走着走着踩到一张旧报纸,捡起来随意瞄了一眼,这一看不打紧,他立刻睁圆了眼睛。也真是巧得很,报纸上正好有一篇报道父亲的专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见到父亲后第一句话就说:“不得了!不得了!现在随便看一张报纸,上面就有你的事迹,想不到你这么有名!”
现在父亲的公司已经发展到六、七个,经营种类也多种多样。他从社会的最底层,到成为人人羡慕的成功人士。没有任何社会背景,靠的是自已的吃苦耐劳、努力奋斗和从不放弃。他坎坷的经历足以写一本厚厚的小说。我为拥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
我有一位和蔼可亲的爸爸他个子不高,中等身材,头上长满了浓密的头发,一双有神的大眼睛,好像永远都不知疲倦。也许是年纪大了,所以脸上刻满了不深不浅的皱纹。他是我尊敬的人!
爸爸是一位木匠,他对工作十分认真,经常为了工作,做工到深夜。
夜深了,时钟刚响了12声,我刚从甜梦里醒过来,屋外传来的阵阵“叭叭叭”的声音。啊!我的爸爸还在工作呢?我想爸爸长期这样下去。身体会垮下来,想到这里,我便下了床来到爸跟前,只见爸爸满头大汗,正聚精会神地工作着,他用划刀将木板割开,然后把一断长条形的方木锯成几断,最后用锤子迅速地把铁钉将木板和方木使劲地钉在一起,不一会儿就做成一张木椅子,爸爸的手艺是多么高超!”您怎么还不睡,爸爸?”。我问他,他只是随口答应我,“你去睡吧!”我真不想离开爸爸,可我又说不服他,只好呆呆地站在一旁看看,他那灵巧的手不停地工作,好像不知首疲倦,那手上的锤子好像是他的老交情了,一点儿也没锤他的手上,要是我去做,那锤子一定不会认我的。
爸爸整天这么干,但他的两眼睛依然是那么有神,这一次,爸爸又得到了一项任务,要在一个月内完成一个巨型组合柜,这一下,可把爸爸忙坏了。为了依时完成任务。爸爸没日没夜地干。放学回家,我第一眼就见爸爸蹲地上忙个不停,直到夜深了。这叭叭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响着,怎么才能使他休息一会呢?我苦苦思索。这时,爸爸看见了,问:“你怎么还不去睡?”我想到爸爸平时非常疼爱我,就故意说:”你不去睡,我也不去睡。“傻孩子,你就去睡吧。”“不,我们要一同睡。”爸爸说:“唉!真拿你没办法。”爸爸只好收拾工具,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我想了个办法,把他的工具藏了起来,爸爸很快地吃过晚饭,放下碗筷就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了,不一会儿,就听见他大声喊:叫我的工具呢?”我假装没听见。妈妈走过来,帮爸爸一齐寻找,后来,妈妈走到我的面前,问:“你看见过爸爸的工具吗?”我的脸虽然红了,但仍然沉着地说:“不知道,”爸爸露出了焦急的心情, 自言自语地说:“要是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呢?”我不忍心看到他这样子,偷偷地把他的工具藏在一个既
没找过,又明显的地方。爸爸很快地找到了。又开始了工作。
刀和锤子又在爸爸手中忙碌起来,仿佛也在不满地说:“哎,这样没完没了地干,你熬得住,我可受不了!”可爸爸却越干越起劲,啊,这是我的爸爸,他那勤劳苦干的美德,将是我永远的榜样。
爸爸,您是我最敬佩的人
爸爸一生勤劳,朴素,只知道吃苦,不懂得享受生活。爸爸是我这一生最敬佩的人!
爸爸年轻时就一直从事建筑行业工作,因为家庭原因,他只能靠自己努力。刚开始爸爸只是一个小瓦工,和泥,垒墙,给别人盖房子。在不断的工作中,他凭着自己的一股干劲,用只有初中文化的底子,学会了建筑专业的预结算及绘图等。他没上过一天建筑学校,全靠自学。那种毅力是难以想像的。没有什么基础,没有老师教,也没有任何人帮他。但他就是凭着自己对建筑的热爱,对那份工作的执着,楞是自学完了所有课程。
爸爸是我学习的榜样,当我向他请教问题时,他对每一个问题除了给我解答,还能很快在书上找到。好像他的脑子里印那些书的每一页。我真是太佩服我的爸爸了。就是上学时老师教过的课本也不一定能立刻找到,更何况是自己学习的课本呢!
爸爸,您是我最敬佩的人!我要向您学习!
最敬佩的人—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中国亿万民众中的普通一员,没有特别显赫的声望和地位。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他足以和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位开疆辟土的君主相媲美,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佩的人。
父亲出身于中国民众的最底层:农民家庭。虽然他非常喜欢读书,但初中毕业后,还是就不得不缀学务农。做为老大,他的下面还有八个弟妹要照顾。
当时的农村还在吃大锅饭。当地地少人多、土地贫瘠,生产队连年“涨肚”(当地土话,即亏损)。年终结算时,不但分不到半点钱、粮,还倒欠队里的钱。但是,人活着总要吃饭、穿衣啊。到了冬天,没农活的时候,父亲就去河里捕鱼。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轰轰烈烈,这种事情如果被抓住了,是要挨批斗的。只能偷偷地去。早晨,天不亮就出门,晚上,要等天黑透了才能回家。捕鱼的工具也很简单:用一根粗圆木,一头削尖,再包上一层铁皮,顶端钉上一根铁刺,就做成了简陋的冰穿子,再带上一张鱼网就行了。到了河中间,选择一个水深的地方,先用冰穿子破冰,在冰面上砸出一个大小合适的窟窿,然后开始下网。冬季冰下缺氧,冰面出现裂口后,如果附近有鱼,鱼就会游过来透气,这时就可以收网了。但破冰和收网的过程都很危险。万一将冰面砸出大的裂缝或砸开的面积过大,冰面就很容易塌陷。如果不小心掉进去,身上穿着的厚厚的棉祅、棉裤立刻被水浸湿,会猛然增加几十斤的重量,刺骨的冰水不用十分钟就能把人冻僵。在水下又很难找到冰口的位置。基本上,如果掉下去,就没有再上来的希望了。那时候,人穷,河也瘦。一天砸上十几个冰窟窿,也网不到几条鱼。就这样,父亲冒着危险,连续打了三年鱼,可是自己家就连过年都没舍得吃上一条,全都悄悄拿到镇上卖掉了,换回来米和盐。
父亲想买一件夏天穿的汗背心,计划了几年也没余钱买。到了夏季的三伏天,上工时,他还穿着那件秋天的大褂,热得汗流夹背。一进家门,脱了衣服,就只能光膀子,家里来客人时再穿上。
到了第四年,父亲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 ”,听说大兴安岭是个“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的富饶之地,父亲决定把全族人搬迁到那里。可是往那里跑了很多次,那边没有一个生产队愿意按纳他们。因为每个队的土地数量是固定的,人口一多,年终人均分配的口粮就会减少,所以人家都不愿意。只有一种办法叫做“以姑娘带户”,就是把自家女孩嫁给当地生产队的男孩子,这样可以让女孩子的娘家人落户。可是,这样,一般情况下,漂亮女孩只能嫁给那些有残疾的、讨不到老婆的光棍,造成不幸的婚姻。而且,也不能解决全族人的问题。
没办法,父亲决定在那里自己新组建一个生产队。他用几个月的时间,把选址、办理迁移的一切手续都办完。在1971年的春天,全族二十几户人家开始了浩浩荡荡的集体搬家。因为路途遥远,只带上了一些生产、生活必需品。包括粮食、衣物、农具、锅碗瓢盆、部分鸡鸭鹅狗。都说穷家值万贯呐!就是这样,也足够壮观的,一路上,孩儿哭,狗儿叫,从火车到汽车,人人侧目。
在到达他们的新建生产队之后,真正的创业才开始了。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坳、一块较为平坦的荒原。首先,他们要建起能住人的房子,然后要打井,修路,还要开辟出能种庄稼的农田。全体有劳动能力的一齐动手。先砍倒小树,扎了几个马架子,也就是窝棚。二十几户人家先住进去。然后再伐木、盖房。
吃饭只能在野地里。支起三块石头,架上大铁锅,折来树枝当柴烧,舀来河水,就开始煮大碴粥了。因为没有锅盖,锅底的粥已经糊了,上面的米还生着呢。风一吹过来,土沫、草叶都刮到粥里,成了不请自来的特殊调味品。当时我二周岁,已经记得很多事情。他们给了我一个断了柄的茶杯当做饭碗。虽然我饿得绕着饭锅咽口水,可是那种又夹生又糊的饭还是难以下咽。如果遇到下雨天,就吃不上饭了,只能等雨停了再做。
那时盖房子也没办法讲究。先做土坯,到大甸子(河边有草的湿地)上用平铲切割出长方形泥块,晒干了就可以切墙。河边都是河水冲刷出的淤泥,土质黏腻,中间又连着很多草茎,不易裂开,拿来砌墙较为耐用。再砍粗木做立柱和房梁,细木随便砍二斧,稍微砍直一些,就做了门窗。房顶盖苫草。房子盖好一座,就搬出一户。那时候哪有玻璃呀,所谓窗户也只是个大木头框子,小窗格都没来得及装。晚上睡觉时就挂起一幅幔帐(一种布做的帘子)当窗帘。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我忽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大人们都叫喊着冲了出去,说是狼来了,咬死了二只羊。我吓得躲在幔帐后面瑟瑟发抖,怕被狼叨了去。
运来的粮食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摞在一个马架子里。如果上面的是大碴子,就只能天天吃大碴子。吃上二、三个月,一直到大碴子吃完了,才能搬出下面的小米。唯一的好处是:全村男女老少都不必费心猜想今天吃什么饭,反正每天都是一个样。等房子盖得差不多时,父亲才发现,粮食已所剩无几。他连忙坐火车回老家去筹运粮食。父亲虽然走了没几天,可是这边的人多啊,一百多口人很快就断顿了。这时,母亲想起了一个路过这里的讨饭老人,老头把讨来的小半袋米放在这儿,让我们代为保管的。大家没办法,把这些米也吃了。那是真正的百家米啊!各个品种、各种成色的粮食混杂在一起。好在百家米吃完后,终于等来了父亲的粮食。老人再来时,我们还给他一袋新来,并对他千恩万谢,他救了我们一族人呐!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那位老人家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愿他老人家的灵魂在天国里得到安息!
新建的生产队有很多事情要办,父亲不停地往返于新建队和公社之间。二者相距60华里,交通工具只有二条腿。那时候,对他们来说,自行车比现在的高档轿车还稀奇,穷乡僻壤是难得一见的。买是没钱买,借也没处借啊!一次,为了办一件事,父亲在一天之内,在两地之间走了三个来回,到最后实在走不动了,只好折了根树枝当拐杖拄着走。妈妈给他做的千层底的布鞋,他只穿三天就磨破了底。
当时开荒种地也是异常艰辛的:伐倒树木、刨掉树根、割去杂草,再用镐头一镐一镐地翻整土地,打碎土块,整理出垄台和垄沟。然后,才能种上庄稼。这种开恳土地的方法,俗称“刨镐头荒”。因为没有铧犁和大牲口,全村大部分土地都是这样一镐一镐地刨出来的。头二年,土地还是很生,庄稼不会长得太好,只有在经过两年不停地翻整、施肥之后才会成为熟地,庄稼的长势才会好。
二爷爷从老家来看他们时,遍寻父亲不见,众人把一个瘦骨嶙峋、胡子拉碴、弯腰驼背的小老头指给他看。二爷爷当时就哭了,说:“好侄子,你受了多大罪呀!你才二十三岁呀!”
这一切的付出都没有白费,到了80年代初,那里已盖起了第二代砖瓦房,家家都有小四轮拖拉机,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普通人家年收入三、四万元。1987年,国家农业部搞了一次全国百名种粮大王抨比。结果评出的首名粮王,不在鱼米之乡的江南,而是在我们那个村附近,名叫赵宏玉。
因为附近出产铁矿石,那个村被命名为铁矿小队。直到现在,那里80%以上都是我的族人,他们都是同一个姓氏。父亲先后做过小队会计、大队会计。最后调到公社以工代干。
1981年,父亲调到公社农业经营管理站担任站长。当时各公社的农经站归条条管理,属于市农业局的派出机构。每到年头年尾,需要写计划、总结时,市农业局的小轿车就会开上四个多小时,到公社把父亲接到市局,执笔写报告,写完后再把他送回来。需要他汇总的不是一个公社的情况,而是全市二十三公社的总体农业情况。市农业局、再加上各农经站的员工有一百多人,比他学历高的人比比皆是。但是这个初中生的文笔却是首屈一指,有口皆碑的。虽然经历了早年失学之痛和种种生活的磨难。父亲却从未放弃过学习,他自学了文学、财务等很多课程。
从那以后,父亲先后担任了农业局干事、副乡长、乡长、乡党委书记、市畜牧局副局长等职务。
父亲走上经商之路纯属偶然。当时小叔叔开了二个商店和一个小公司,经营家用电器和音像制品。因为经营和个人感情同时出现问题,一向在几个兄长的呵护下长大、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的小叔叔弃商而逃,远走它乡。债主差点挤破门坎。总得有人收拾烂摊子啊!按规定,干部不允许经商,父亲只能辞职,放弃这个经过多年奋斗,并读了三年电大才换来的干部身份。就在他的升任旗长(少数民族地区的职务设置,等于县长)的调令下来的那天,他递交了提前退休申请。
经商之路总是充满曲折,难以预测。有时就会“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在东拼西凑终于还清欠款,并努力经营积累了一定的家底后,在他经商的那条电器商业街,有一家店面失火,导致火烧连营,价值几十万元的货物化为乌有。亲戚、朋友都以为父亲这次肯定再也爬起不来了,一个个远离而去。那段时间,父亲既盼着电器厂的送货车能早点来,因为有货才能卖出钱。可是又怕它来,因为货款根本没有着落,亲友早已借无可借。每当送货车要来的前二天,他就早早地在大街上站着,看看能不能遇到熟人,还能不能借到点钱。当时我早已离开家乡。每当想起妹妹向我描述的这些,我都忍不住心酸落泪。
在经营了多种项目之后,父亲成立了物业管理公司,是我们那里附近几个城市的首家私营物业公司,在以后的几年里,也是唯一的一家。业务覆盖了几个县级市。父亲以前单位有个同事老赵,听说父亲现在经商发了,就特地前来投靠。可是,老赵下了火车之后却怎么也找不对地方,原来别人给他的是旧的地址。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走着走着踩到一张旧报纸,捡起来随意瞄了一眼,这一看不打紧,他立刻睁圆了眼睛。也真是巧得很,报纸上正好有一篇报道父亲的专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见到父亲后第一句话就说:“不得了!不得了!现在随便看一张报纸,上面就有你的事迹,想不到你这么有名!”
现在父亲的公司已经发展到六、七个,经营种类也多种多样。他从社会的最底层,到成为人人羡慕的成功人士。没有任何社会背景,靠的是自已的吃苦耐劳、努力奋斗和从不放弃。他坎坷的经历足以写一本厚厚的小说。我为拥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0-01-02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