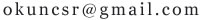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因而这些名称大都以及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因是卫国人又称“卫鞅”,因封为商君又称“商鞅”等。此外,在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生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与“名”互为表里,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 “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果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像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使用为了表示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因此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已不再需要这些字、号之类的东西。但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所知,就根本无从识别。所以,为了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思想、风格,还是需要对它们有所了解的。 摘自(时代学习报)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无其他回答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