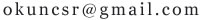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的能力是文学的基本能力。
由于永无止境的精神欲求和创造冲动,人类今天已经拥有一个极为庞大丰富、灿烂辉煌的第二世界——精神世界。
上帝创造第一世界,而人类创造第二世界。
这不是一个事实的世界,而是一个无限可能的空白世界,创造什么并不是必然的,而是自由的。
我们眼前的世界,既不是造物主所给予的高山河流、村庄田野,也不是喧嚣的人世,而只是一片白色的虚空,是“无”。
我们要让这白色的虚空生长出物象与故事,这些物象与故事实际上是生长在我们无边的心野上。
精神世界的惟一缺憾就是它与我们的物质世界无法交汇。我们的双足无法踏入,但我们的灵魂却可完全融入其间。它无法被验证,但我们却又坚信不疑。
无中生有就是编织和撒谎。
劳伦斯说:“艺术家是个说谎的该死的家伙,但是他的艺术会把他那个时代的真相告诉你。”
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跟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那才是文学。
在丛生的野草中的狼和夸张的故事中的狼之间有一个五光十色的过滤片,一副棱镜,这就是文学的艺术手段。
艺术的魔力在于孩子有意捏造出来的那只狼身上,也就是他对狼的幻觉;于是他的恶作剧就构成了一篇成功的故事。
顾弄玄虚
作家博尔赫斯的视角永远是出人预料的,他一生中从未选择过大众的视角。
当人们挤向一处去看同一景观时,他总是闪在一个冷僻的无人问津的角度,用那双视力单薄的眼睛去凝视另样的特别的景观。
这个后来双目失明的老者,他坐在那把椅子上所进行的是玄想,玄想的结果不再是我们这些俗人眼中的一切物象。
博尔赫斯的作品是写给成年人的童话。
另一个写成年童话的作家卡尔维诺,他每写一部作品都要处心积虑地搞些名堂,这些名堂完全出乎人的预料,并且意味深长。
他把我们带入一个似乎莫须有的世界。这个世界十分怪异,以至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他让我们总会有一种疑问:在我们通常所见的状态背后,究竟还有没有一个隐秘的世界?这个世界另有逻辑,另有一套运动方式,另有自己的语言?
文学家不是比力气,而是比潇洒、比智慧。
坐井观天
文学是一种用来书写个人经验的形式。
如果作家在创作时尊重了自己的个人经验、以个人的感受为原则,那么他在实质上就是坐井观天。
每个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会得到不同的经验。
我们应当将自己的作品建立在自己经验的基础上,文学必须回到个人的经验上来。
一个小说家自己的鲜活感觉永远是最重要的。
无所事事
无所事事可能是文学写作所需要的上佳状态。
由无所事事的心理状态而写成的、看似无所事事而实在有所事事的作品,在时间的淘汰下,最终反而突兀在文学的原野上。
中国文坛少有无所事事的作家,也少有无所事事的作品。
我们太紧张了,我们总是被沉重的念头压着。我们不恰当地看待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将文学与社会紧紧捆绑在一起,对当下的社会问题表现出了过分的热情。
普鲁斯特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之下发现了许多奇妙的东西,比如说姿势——姿势与人的思维、与人物的心理,等等。
当别人去注意一个人在大厅中所发表的观点与理论时,普鲁斯特关闭了听觉,只是去注意那个人的姿势。
人在无所事事的佳境,要么就爱琢磨非常细小的问题,比如枕头的问题、姿势的问题、家具的问题,要么就爱思考一些大如天地的、十分抽象的问题。这些问题自有人类的历史的那一天就开始被追问,是一些十分形而上的问题。
普鲁斯特将这些细小如尘埃的问题与宏大如天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在那些细小的物象背后,他看到了永世不衰、万古长青的问题。
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他有责任注视‘当下’。面对眼前的社会景观,他必须发言、评说与判断。
当一个知识分子对他所处的环境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竟然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时,他就已经放弃了对‘知识分子’这一角色的坚守。
当作家作为作家时,他应该换上另外一种思维方式。
作家所关心的‘当下’应含有‘过去’与‘将来’。他并不回避问题,但这些问题是跨越时空的:过去存在着,当下存在着,将来仍然会存在着。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消失。
那些琐碎的、有一定时间性和地域性的事物,在作家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他可以视而不见,他看到的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
无中生有的能力是文学的基本能力。
由于永无止境的精神欲求和创造冲动,人类今天已经拥有一个极为庞大丰富、灿烂辉煌的第二世界——精神世界。
上帝创造第一世界,而人类创造第二世界。
这不是一个事实的世界,而是一个无限可能的空白世界,创造什么并不是必然的,而是自由的。
我们眼前的世界,既不是造物主所给予的高山河流、村庄田野,也不是喧嚣的人世,而只是一片白色的虚空,是“无”。
我们要让这白色的虚空生长出物象与故事,这些物象与故事实际上是生长在我们无边的心野上。
精神世界的惟一缺憾就是它与我们的物质世界无法交汇。我们的双足无法踏入,但我们的灵魂却可完全融入其间。它无法被验证,但我们却又坚信不疑。
无中生有就是编织和撒谎。
劳伦斯说:“艺术家是个说谎的该死的家伙,但是他的艺术会把他那个时代的真相告诉你。”
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跟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那才是文学。
在丛生的野草中的狼和夸张的故事中的狼之间有一个五光十色的过滤片,一副棱镜,这就是文学的艺术手段。
艺术的魔力在于孩子有意捏造出来的那只狼身上,也就是他对狼的幻觉;于是他的恶作剧就构成了一篇成功的故事。
顾弄玄虚
作家博尔赫斯的视角永远是出人预料的,他一生中从未选择过大众的视角。
当人们挤向一处去看同一景观时,他总是闪在一个冷僻的无人问津的角度,用那双视力单薄的眼睛去凝视另样的特别的景观。
这个后来双目失明的老者,他坐在那把椅子上所进行的是玄想,玄想的结果不再是我们这些俗人眼中的一切物象。
博尔赫斯的作品是写给成年人的童话。
另一个写成年童话的作家卡尔维诺,他每写一部作品都要处心积虑地搞些名堂,这些名堂完全出乎人的预料,并且意味深长。
他把我们带入一个似乎莫须有的世界。这个世界十分怪异,以至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他让我们总会有一种疑问:在我们通常所见的状态背后,究竟还有没有一个隐秘的世界?这个世界另有逻辑,另有一套运动方式,另有自己的语言?
文学家不是比力气,而是比潇洒、比智慧。
坐井观天
文学是一种用来书写个人经验的形式。
如果作家在创作时尊重了自己的个人经验、以个人的感受为原则,那么他在实质上就是坐井观天。
每个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会得到不同的经验。
我们应当将自己的作品建立在自己经验的基础上,文学必须回到个人的经验上来。
一个小说家自己的鲜活感觉永远是最重要的。
无所事事
无所事事可能是文学写作所需要的上佳状态。
由无所事事的心理状态而写成的、看似无所事事而实在有所事事的作品,在时间的淘汰下,最终反而突兀在文学的原野上。
中国文坛少有无所事事的作家,也少有无所事事的作品。
我们太紧张了,我们总是被沉重的念头压着。我们不恰当地看待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将文学与社会紧紧捆绑在一起,对当下的社会问题表现出了过分的热情。
普鲁斯特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之下发现了许多奇妙的东西,比如说姿势——姿势与人的思维、与人物的心理,等等。
当别人去注意一个人在大厅中所发表的观点与理论时,普鲁斯特关闭了听觉,只是去注意那个人的姿势。
人在无所事事的佳境,要么就爱琢磨非常细小的问题,比如枕头的问题、姿势的问题、家具的问题,要么就爱思考一些大如天地的、十分抽象的问题。这些问题自有人类的历史的那一天就开始被追问,是一些十分形而上的问题。
普鲁斯特将这些细小如尘埃的问题与宏大如天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在那些细小的物象背后,他看到了永世不衰、万古长青的问题。
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他有责任注视‘当下’。面对眼前的社会景观,他必须发言、评说与判断。
当一个知识分子对他所处的环境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竟然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时,他就已经放弃了对‘知识分子’这一角色的坚守。
当作家作为作家时,他应该换上另外一种思维方式。
作家所关心的‘当下’应含有‘过去’与‘将来’。他并不回避问题,但这些问题是跨越时空的:过去存在着,当下存在着,将来仍然会存在着。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消失。
那些琐碎的、有一定时间性和地域性的事物,在作家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他可以视而不见,他看到的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