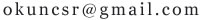日本古典文学(书面文学)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上起八世纪初,下至十九世纪中叶,大致可分为古代前期、古代后期,中世纪前期与中世纪后期四个阶段。(注:关于日本史的时代区分,日本国内及国外的史学界,有种种不同看法,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如日本封建社会究竟始于何时,竟有五种不同看法,上下悬殊达六、七个世纪。这里从日本国内多数史学家的看法,以 仓时期做为进入封建社会的分界。参见《岩波小辞典·日本史》“封建社会”项,岩波书店1964年版,第178页。)
一、古代前期文学
大约在公元前后,日本基本结束了原始共同体社会。最初出现的是一些地方上的群小酋长国。四、五世纪,在大和地方(今奈良县的一部分地区)兴起的强大豪族天皇氏,逐步统一了日本,建立了“大和政权”。日本古代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与接受中国文化、技术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文化、生产技术以及汉字,通过朝鲜半岛,或通过直接往来传入日本。特别是七世纪以后,日本的中央政权与中国隋、唐王朝直接往来更多,派遣了十数次大规模的遣唐使团及留学生、学问僧等到中国学习;这种措施先后持续二百余年之久,足以说明处于上升阶段的古代国家的进取精神。当然,日本古代贵族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创造其贵族文化。
日本最早的书面文学出现于八世纪初叶,即“奈良时期”(710-784)。这时期书面文学的代表作品有《古事记》与《万叶集》。当时日本还未创造出“假名文字”,这两部著作都是借助汉字写成的。前者汉字既用于表义,又用于表音;后者汉字主要用做表音符号。
《古事记》是一部记录古代神话与传说的作品,成书于公元712年。从这部书的序言可知,它是在天皇的命令下着手编纂的,目的是企图利用神话来证明天皇世系的权威性。由于这样的政治目的,所以《古事记》中有许多枯燥无味的关于神的世系的说明;虽然如此,并不能掩盖《古事记》这部书中一些生动的神话与传说的文学性。
神话是古代人通过美丽的幻想,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或表达人们对支配自然的渴望;《古事记》也不例外。它的许多章节或片断,如上卷中的“海幸与山幸的故事”写的是渔夫与樵夫两兄弟的争执,然后转入山幸与海神之女结婚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还以美丽的想象解释了旱涝潮汐的自然现象。“大国主命求婚的故事”是以几组爱情歌谣为主发展起来的。在中卷中插有多首古代集团战斗的歌谣,在下卷中记录了古代部族之间的战斗传说。所有这些,做为反映古代日本民族生活气息的最初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力量。
八世纪的下半期,出现了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全书共二十卷,收和歌(注:和歌是古代日本人将民族固有的诗歌与汉诗加以区分的称呼。一般称歌,即指前者;称诗,即指后者。和歌只有音数律这种固定的诗形,但无韵脚。)(长歌(注:长歌的音数律是5·7·5·7……7·7,其中5·7可反复多次,长短不限。)及短歌(注:短歌的音数律是5·7·5·7·7共三十一个音节。)等体裁)共四千五百余首。
《万叶集》的编次方法,各卷不同。有的卷按年代编次,有的卷按内容分为杂歌、挽歌、相闻歌(广义指赠答歌,狭义指恋歌)三大类,有的卷还设譬喻歌防人歌(戍边兵士歌)等目。
《万叶集》中有署名的作品,也有无名氏的作品。无名氏作品中有些属于民歌和民谣;具名的作品中有许多是所谓著名“歌人”的创作。集中署名的作者约四百五十人。
除少量传说的作者(其中有的可上溯三、四百年)外,著名“歌人”的活动,大多集中于七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这段时期。这百余年间又可细分为三个时期,前期的作者大多为天皇一族,如舒明天皇、中皇命、天智天皇、额田王等人。这个时期正是日本古代中央集权国家整备与壮大的时期,这些人的歌风,以格调醇朴率真见长。作歌的背景往往与当时历史的动乱有关。
中期的作者,活跃于七世纪中期以后与八世纪初,其中代表作者有柿本人麻吕、高市黑人、志贵皇子、山上忆良、大伴旅人、山部赤人、笠金村、高桥虫麻吕等人。这些人是当时的贵族或中、下级官吏。他们的歌风各具特色,对和歌形式的完成及使艺术手法臻于完美方面,各自做出了贡献。柿本人麻吕自古以来被称为“歌圣”,他善于驱使长歌这一形式,写出了许多怀古歌及挽歌,如《高市皇子城上殡宫歌》、《过近江荒都歌》以及别妻歌、悼念亡妻歌等等。他写的以宫廷为题材的怀古歌,表现了对古代国家上升时期的景慕与追怀,声调功雄浑、沉郁悲壮。抒发个人感情的别妻歌、悼亡歌写得语重意真、哀婉 切。他善于运用对句及枕词(注:“枕词”是和歌中特有的修饰语,亦称“冠辞”。每一枕词,与特定的被修饰语发生联系,起着丰富联想及调整音调的作用。),词藻赡富,音韵流利,于浑厚中见性情的真挚。高市黑人与山部赤人擅长写叙景歌,他们所写的自然风光,寓情于景,格调清新有致。高桥虫麻吕擅长写传说歌,卷九中收录了他写的《咏江水浦岛子歌》、《胜鹿真间娘子歌》、《见菟原处女歌》等以民间爱情故事为题材的长歌,刻画事件与人物细腻生动,别具特色。
在这些“万叶歌人”当中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山上忆良。他年轻时曾做过遣唐大使的随员来过我国。他的长歌,大多附有用骈体汉文写的长序,可以看出他汉文修养之深。他写的著名长歌《贫穷问答歌》是唯一直接反映古代律令制国家统治下人民遭受横征暴敛之苦的一首绝唱。现将这首歌的全文译介如下:
风雨交加夜,冷雨夹雪天。瑟瑟冬日晚,难御此夜寒。粗盐权下酒,糟醅聊取暖。鼻塞频作响,背曲嗽连连。捻髭空自许,难御彻骨寒。盖我麻布衾,披我破衣衫。虽尽我所有,难御此夜寒。贫尤甚我者,听我问数言:妻儿吞声泣,父母号饥寒。凄苦此时景,何以度岁年?
天地虽云广,独容我身难。日月虽云明,岂照我身边?世人皆如此,抑或我独然?老天偶生我,耕作从不闲。身着无棉衣,条条垂在肩。褴褛如海藻,何以御此寒?矮屋四倾颓,稻铺湿地眠。妻儿伏脚下,父母偎枕边。举家无大小,鸣咽复长叹。灶头无烟火,锅上蛛网悬。忍饥已多日,不复忆三餐。声微细如线,力竭软如棉。灾祸不单行,沸油浇烈焰。里长气汹汹,吆喝在房前,手执笞杖来,催逼田税钱。世道竟如此,此生怎排遣?
〔反歌〕(注:反歌——受我国“返辞”的影响,附在长歌之后,以短歌形式,集中地再次讽咏长歌的主要内容。)忧患兮人世!耻辱兮人世!恨非凌空鸟,欲飞缺双翅。
这首歌,有种种解释,一般倾向于将前半首理解为一个古代读书人对贫困处境的自诉,并推己及人,连想到较己尤甚的农民的痛苦,下半首是代农民作答,道出了在古代班田制下农民抢地呼天、欲告无门的悲惨处境。
《万叶集》的后期作者,以大伴家持及大伴坂上郎女为代表。这时,时代已进入律令制国家的后期,古代社会暴露出种种矛盾,开始走上解体的过程。大伴家持的歌风正反映了这个下降时期的特点。他的短歌,具有凄清纤丽、情致缠绵的特点。坂上郎女写了一些纤 绮丽的恋爱歌。
《万叶集》中无名氏的歌,约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这些歌中最具有特色的是收录在卷十四中的二百多首“东歌”(本州东部地区的民歌)。这些民歌大多以爱情为主题,不但语言纯朴自然,而且利用各种劳动场景做为比、兴等艺术手段,使这些民歌表现得情趣盎然,富于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有些歌还表达了不畏父母横暴干涉,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感情。卷二十里收录了九十二首“防人歌”(戍边兵士之歌)。这些歌反映了在古代天皇制下被迫别父母、抛妻子,兵士远戍边疆的凄苦哀怨之情。除去上边提到的一些歌之外,《万叶集》还收有不少反映古代社会各方面生活的作品。
总之,《万叶集》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古老,而在于它反映古代生活的深度及广度,在于它格调的深厚真挚。在《万叶集》以后,和歌逐渐堕落为贵族们吟风咏月的消闲品,贵族们利用它做为社交赠答及男女求爱的工具,或利用它进行宫廷“歌合”(比赛和歌的游戏)。到了平安、镰仓时期,和歌也专为贵族及僧侣们所占有,成了他们抒发个人纤弱感情的手段。
本时期除上述《古事记》与《万叶集》之外,在散文方面应提出的还有《风土记》。《风土记》原本是由当时各地方官吏,在天皇政权指令下编纂起来的地方志性质的书,但其中含有许多片断的地方传说与古老的故事。这些古老传说虽然经采集的地方官吏之手写得比较简略,但却往往洋溢着古代民众的生活情趣。有些传说,后来为民间故事所继承,不断加以发展。
本时期在韵文方面,除了《万叶集》及在《古事记》等书中保存下来的歌谣外,还有宗教性质的歌谣《祝词》,这是古代祷神用的歌词,其中有的歌词反映了古歌谣中那种韵律的美及形象生动的比喻手法。
二、古代后期文学
古代后期起自九世纪初,迄十二世纪末。日本通常将这时期称为平安时期。在这期间古代国家发生了质的变化,班田制的土地所有制逐渐为大土地私有的庄园制所代替。天皇逐渐失去了权柄,藤原氏一族掌握了中央的政治实权。古代贵族的进取精神逐渐消失,天皇家、藤原氏一族以及所有居住在平安京的贵族阶级,蜷伏在京城,倚靠从全国各地庄园收刮来的财富,过着纸醉金迷、尽情享乐的生活。
平安时期初期,和歌创作转入衰微。贵族之间,出现了模仿汉诗汉文的极盛时期,编纂了许多敕撰的汉诗集或诗文合集,如《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他们致力的是如何模仿汉诗汉文的华丽辞藻及技巧,至于内容则完全脱离不开空具形骸的宫廷游 生活。因此,这些汉诗汉文除了可以看出当时贵族模仿能力外,对日本民族文学的发展,关系不大。
另一方面,自平安初期以来,创造出由汉字草书演变而来的“平假名”,及由汉字偏旁演变而来的“片假名”。随后创造出假名与汉字交混在一起的书写方式。至此日本的民族文学,才获得了自由自在地表现的手段。这对平安时期的散文作品“物语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早出现用“假名”创作的物语文学是《竹取物语》,成书的具体年代及作者均不明,大体推测写于九世纪后半期至十世纪上半期。这是一个带有民间故事性质的作品,内容叙述月宫天女下凡,住在一个以伐竹为业的老翁家里,几个大贵族向天女求婚,均遭天女拒绝与嘲弄,最后天女返回月宫的故事。从这个故事的构思来说,情节单纯,类似民间故事或童话。但从细节来看,由于作者以幽默、讽刺的态度,刻画了五个向天女求婚的贵族的种种丑态,使得这部最早的物语文学,从它情节描写的细腻,人物性格的突出以及对贵族保持的批判精神来说,都给日本文学带来了崭新的东西。日本文学已脱离了那种片断式的古代传说,发展成具有完整结构的短篇小说的形式。
到了十一世纪初,由贵族妇女之手创作了许多散文文学的新的体裁:基于作者个人生活体验写成的“随笔文学”及“日记文学”,以及由作者通过虚构创造出来的“物语文学”等等。
十一世纪是属于整个平安时期的中期,是藤原氏“摄关”(注:“摄关”是“摄政”与“关白”的简称。藤原氏自九世纪中叶起,利用外戚地位,取得政治实权;在天皇未成人时,由藤原氏摄政,天皇成人后,则藤原氏改称关白。这种政权形态,一直延续到十一世纪中叶。)政治,达到顶峰并开始走上没落的转折期。贵族阶级本身的腐败堕落,地方豪族势力的伸张、新兴武士阶级的抬头,使得中央贵族内部孕育着日益深重的危机。而藤原氏一族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仍在热中于制造宫廷阴谋,在同族之间不断争夺外戚的地位,以达到操纵天皇这个傀儡的目的。他们除了卖官鬻爵,穷极奢欲之外,对全国政治完全丧失了处理的能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由中、下层贵族妇女之手创造了为这一时期整个贵族阶级奏挽歌的作品。这些贵族妇女,她们大多出身于中层贵族家庭,她们的父兄,或者不甘心雌伏于藤原氏一族之下,宁愿到地方去做“国守”成为熟悉地方民情的官吏;或者留在京师,以他们的才能学识,攀附藤原氏一族来维持他们不安定的地位。这些中层贵族出身的妇女,受这样家庭气氛及文化教养的熏陶,加上当时藤原氏一族习惯于招纳有才华的中层贵族妇女给他们做后妃的女儿充陪侍的女官,这样,这些中下层贵族妇女,既具有超出京城贵族狭隘眼界的教养,又身临目睹了藤原氏一族及宫廷等大贵族的生活实际情况,从而使这些贵族妇女产生了省察整个贵族生活的创作动机。
这个时期出现的、最有才华的贵族妇女作者,要首推紫式部(详见本章第二节),长达八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就是她的杰作。这部作品是平安贵族的一部百科全书,它揭示了整个宫廷贵族生活,描写了贵族妇女的群像,并对她们所处的悲惨地位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与《源氏物语》略约同时出现的还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这是一部随笔或札记性质的散文集,记录了她在宫廷做女官时的一些生活片断及见闻。作者完全是以肯定与赞美的态度来描绘当时的宫廷生活的。作品中还用“杂纂集类”的形式,正面表露了作者对自然美的纤细感受及贵族生活趣味的评价。她的观察及感受虽然十分敏锐与细腻,但她评价自然与人事的标准,一步也未离开贵族阶级的立场。
除了上述两个女作者外,还有其他一些贵族妇女的作品,如道纲母写的《蜻蛉日记》(成书大约在十世纪末,较早于《源氏物语》),写的是作者半生的生活体验,真实地记录了在贵族阶级一夫多妻制下自身的苦痛,这部作品无疑给《源氏物语》以多方面的影响。此外,还有《落 物语》(作者不明,大约在《源氏物语》前,作者为男贵族),描写贵族家庭继母虐待前妻女儿的故事,以及《狭衣物语》、《堤中纳言物语》等。前者也是描写贵族恋爱的故事,但思想境界远逊于《源氏物语》,后者是十个短篇集,追求故事内容的新奇,说明物语文学正在走上形式的多样化。
十二世纪末叶,文学中出现了两种新的体裁。一种是被称为“历史物语”的《荣华物语》及《大镜》。前者叙述了宇多天皇(887)至堀河天皇约二百年间的“摄关”政治的大致情况,而以藤原道长的专权时期为重点,描写了他权势赫赫的半生及围绕他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后者仿效我国《史记》的列传体,记叙了简单的帝纪,然后着力写了登上权臣宝座的藤原氏一族势要人物的列传。《大镜》对于“摄关政治”时期贵族内部的权势之争有所批判。
大致与《大镜》、《荣华物语》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部《今昔物语集》。这是一种其内容及文体与上述反映贵族生活完全异趣的崭新作品。全书共三十一卷(现存本已残缺不全),收有一千余篇短小的故事。日本文学史上将这种文学形式称之为“说话文学”,以区别于那些反映贵族生活的“物语文学”。《今昔物语集》收集的“说话”,一多半属于“佛教说话”,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卷二十二以下的“世俗说话”。从这类“说话”中可以看到平安末期新兴的武士阶级的面貌及一般民众的生活情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包罗了农民、渔民、贵族、僧侣、武士、商人、艺人、妓女、盗贼等当时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反映了这些人物的不同行径与新的历史时期各阶层的思想状态。这部作品,在语言上也有所创新,它使用的是明快、简素的“和汉混淆体”,完全脱离了“物语文学”那种纤弱的、情绪缠绵的“王朝文体”。因此,无论就内容或就表现形式来说,都给即将到来的镰仓时期反映武士阶级的文学开辟出新的蹊径。这部作品的出现,说明贵族文学已趋于没落,而崭新的文学正处于破晓的状态之中。
三、中世纪前期文学
这里所说的中世纪前期,是指从十二世纪末至十六世纪末这段时期。
从十一世纪后半期,藤原氏专权的“摄关政治”出现了破绽,天皇氏一族从藤原氏夺回了政治实权,历史进入了“院政时期”(由退位了的天皇掌握政治实权),但这并不能挽救已经腐朽、注定灭亡的贵族统治。经过1157年的“保元之乱”以及接踵而来的“平治之乱”,从庄园制产生出来的地方武士阶级(武装了的地主阶级),挤入了中央政治舞台,并以源氏与平氏两家武士之争的形式,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乱,终于在十二世纪末出现了由新兴的武士阶级掌握全国政权的局面。这就是源氏所建立起来的“镰仓幕府”。十四世纪初一度出现了由京都贵族策划的旧天皇政治的复辟。至1338年才又由武士足利尊氏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室町幕府”。接着于十五世纪中叶,武士阶级内部又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居于中央政权的武士——足利氏逐渐失去了统治全国的力量,出现了诸侯连年征战不已的“战国时期”。在这种分裂与统一的过程中,终于消灭了古代贵族政治上的残余势力,使日本社会逐渐完成了封建体制。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非常急剧,也由于统治者之间的不断纷争,使得统治力量日趋削弱,民众的力量日益兴起与壮大。特别是进入十五世纪以后,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同时出现了都市要求自治的动向。在思想方面,由于统治者权威的失坠,出现了“下克上”的时代思潮,使得这时期文学具有鲜明地反映民众力量兴起的特色。
这时期文学中最早出现、同时又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是“军记物语”。十三世纪三十年代,首先出现了《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然后继之又出现了《平家物语》。由于这时的政治动乱离不开战争这一形态,所以这些作品都着力描写了新兴的武士驰骋战场,叱咤风云的形象。虽然一般把这类文学,统称为“军记物语”或“战记物语”,但实际上它所反映的决不单纯是战争场面,而是多方面地反映了进入巨大历史转折期的阶级的、政治的种种面貌。
《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两书的作者不明,据推两书可能出于一人之手。《保元物语》描写的是历史上的“保元之乱”,《平治物语》描写的是继“保元之乱”三年后又一次出现的“平治之乱”。这两部作品有个共同主题,那就是通过文学形象,如实地生动地再现新兴的武士阶级的种种的刚毅、勇猛的性格以及他们的积极、果断的行动。前一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无位无官”的武士源为朝,为他在宫廷权力之争中的智勇以及失败后被流放,最后终于兵败自杀的过程;后一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是恶源太义平,书中专写了他的勇猛的作战行动及他那虎虎有生气的武士性格。这两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由担当新的历史使命的武士阶级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刻画了已处于垂死阶段的公卿贵族的怯懦与愚蠢。这两部作品与前一时期经贵族妇女之手创造出来的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呈现出本质上的不同。这两部作品在着力描写新兴阶级的英雄人物行动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了做为新的剥削阶级——武士本质的另一侧面:这些武士们在卷入贵族内部的阴谋纷争当中,进行了子杀父,兄杀弟等等极其无情的骨肉相残。作品对这方面的忠实描写,有力地传出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两部作品,继承并发展了《今昔物语》在语言上的创新,说明一种新的文学的产生必然要求作品的语言突破以往的窠臼,要求创造出崭新的艺术形式。
《平家物语》是较前两部作品稍晚一些时候出现的军记物语的白眉。这部作品内容也是描写平安末期新兴武士阶级与中央贵族势力进行殊死斗争、终于将政治实权掌握到本阶级手中的巨大历史事件的。就文学成就来说,它所反映的时代本质,较前两部作品更为深刻,塑造的英雄人物,也更富于生命力。
《平家物语》这部作品,正如书名所示,是以源平之争的一方,平氏一族的命运为主线进行描绘的。这部作品,带有浓厚的佛教净土思想,对平氏一门灭亡的命运,做了种种文学上的渲染,使用了悲哀的语调,极尽叹婉之能事。这说明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平氏这一边的。但是,作者对这次巨大的历史动乱,又表现出矛盾的态度。固然作者从贵族出身的立场出发,对贵族化了的平氏子孙的所谓风流蕴藉的生活态度,处处流露了赞美与同情;但从客观上却揭示了失去了原有武士阶级属性的平氏一族,早已变得纤弱萎靡,他们的灭亡,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作者虽然认为兴起于东国的源氏一族,都是一些不解风流为何物的、蛮勇粗犷的武士,甚至加以讪笑;但在描写他们作战的场面时,却又不能不投以惊异、畏服与赞叹的目光。作者生动地刻画了他们那种刚毅、勇敢的性格,描绘了他们疾风怒涛的战斗行动,尤其是对源氏大将们的英雄形象,对源义仲、源义经等人的刻画,写得有声有色。这部作品,除了对史实上的人物,予以文学加工,塑造了许多鲜明的典型外,还插入了若干“王朝物语式”的故事,如“祗王祗女的故事”、“小督的故事”等。这些哀婉有致的、关于妇女命运的描写,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浓厚的抒情色调。
这部作品,在艺术语言上,也为古典文学开辟了崭新的境地。它继承了《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开创出来的刚劲有力的汉文调的文体,又将《源氏物语》以来王朝物语中那种缠绵悱恻、委婉多姿的和文调文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和汉混淆”、韵散结合的文体,对以后文学语言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镰仓初期出现的这几部作品,是在武士阶级已取得政权的政治背景下出现的。它有力地反映了处于上升阶级武士阶级的思想感情。这几部作品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它们带有说唱文学的性质。这些作品,原始版本与现今普遍流传的版本之间,存在着不断增添、润色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可能有演唱这些作品的盲艺人——“琵琶法师”参与其间,说明了这类文学创作的民众性。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长期地广泛地为以后的戏曲、小说所大量继承,在为后世戏曲及民间文学素材的丰富来源,直到今天,日本古典文学中广为流传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大多出自这几部作品。
从十四世纪开始,在当时的京城周围的农村里,通过演剧酬神逐渐兴起了民间戏剧和艺能。后者逐步沿着音乐、舞蹈及表演等综合艺术的方向发展,后来成为一种以音乐、歌唱、舞蹈为主的戏剧——“能”。前者则发展成为以对白为主的独幕喜剧——狂言。最初,狂言都是演员们的即兴创作,讽刺当时的某些社会现象。到了十五世纪前后,它逐渐成熟,产生了许多定了型的传统剧目,它的脚本也由各个流派之手固定并保存下来。现在的狂言脚本,约有三百出左右。
狂言的高度文学价值,在于它反映了当时民众力量的兴起。狂言采取集中一个突出的矛盾,用喜剧或闹剧的手法,讽刺、嘲笑了欺压民众的一切邪恶势力。狂言中的许多所谓“大名”类的剧目,大多写的是“大名”(中世纪京都周边的地主武士阶级)与仆人的矛盾。在剧中“大名”被刻画为贪婪、蛮横而又愚蠢的形象,而仆人则被刻画为聪明、伶俐,富于机智的人物。在戏剧冲突中,一般都以“大名”的失败与仆人的胜利告终。狂言还对僧侣使用欺骗手段进行敛财以及酗酒渔色等等丑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嘲笑。对统治者乐于宣扬的、束缚人民意识觉醒的神鬼观念,进行了大胆的嘲弄。狂言中的妇女形象也是性格泼辣,非常富于进取的。正是由于狂言充分反映了中世纪“下克上”的时代精神,因而它深受下层民众的喜爱,在民众的支持下日益得到发展。当然,由于狂言在逐步走上定型化之后,它的讽刺精神已不象它初期即兴演出时那样泼辣尖锐;到了室町时期,它成了演出“能”时的附随物——幕间狂言,做为狂言生命的讽刺精神,也就停滞了。
这时期的另一种文艺是连歌。这是利用一首和歌分为上下两句,由不同的作者进行互相连句的艺术形式。它原是出于平安贵族比赛和歌时,做为会后余兴发展起来的,最初在贵族及僧侣之间流行,后来浸透到下级武士及商人之间,形成一种带有娱乐、社交性质的文艺活动。参加连歌的一些人,叫做“连众”,他们一边进行连歌创作,一边进行互相品评与欣赏。但后来出现了种种连歌的繁琐规则,形成了教授及品定连歌优劣的“宗师”制度。到了室町末期,连歌的首句独立出来,发展成为俳句,而连歌本身则逐渐丧失了它的生命力。总之,连歌做为一种特殊创作活动的文艺,就其发生与发展来说,也是这时期文学逐渐走上民众化的一种反映。
这时期另一种文学创作是随笔文学。其代表作品有十三世纪初期问世的《徒然草》,作者为鸭长明(1153-1216),十四世纪初期出现的《方丈记》,作者田兼好(1283-1350)。这两个作者均出身于没落的贵族阶级,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后来出家为僧。他们对本阶级注定的死亡命运都有一定程度的觉察,但又不能对新兴的武士阶级做无条件的肯定,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旁观的态度,过着一种隐逸的生活。在《方丈记》中记录了平安末期的天灾与人事异变,对异族争夺权势持否定的看法,也流露了隐逸者的、消极的生活态度。《徒然草》是一种杂感性质的小品集,全书分为长短不等的二百四十三段,作者的人生观基本上也是消极的,但也有一些短小精辟的寓意性小故事,富有教训意义,说明了作者重视理性的一面。这两部作品,由于采用的都是和汉混淆体,文字精确简练,长期被视为古文的典范。书中一些消极的、旁观者思想及生活态度,对后世文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这时期,还有两部值得提出的作品,一部是《曾我物语》,成书于十四世纪初,一部是《义经记》,成书于十五世纪初期至中期之间。前者是写两个武士曾我兄弟为父报仇的故事,后者是写源氏的大将源义经的传奇式的、悲剧性的一生。这两部长篇作品,虽然也列入军记物语之中,但它们描写的已不是象《平家物语》那样大规模的武士阶级的集团搏斗,而是专门刻画武士个人历尽艰辛、波澜起伏的一生。这两部作品实际是摭拾当时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关这些人物的传说,经过加工润饰而成的。由于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
一、古代前期文学
大约在公元前后,日本基本结束了原始共同体社会。最初出现的是一些地方上的群小酋长国。四、五世纪,在大和地方(今奈良县的一部分地区)兴起的强大豪族天皇氏,逐步统一了日本,建立了“大和政权”。日本古代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与接受中国文化、技术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文化、生产技术以及汉字,通过朝鲜半岛,或通过直接往来传入日本。特别是七世纪以后,日本的中央政权与中国隋、唐王朝直接往来更多,派遣了十数次大规模的遣唐使团及留学生、学问僧等到中国学习;这种措施先后持续二百余年之久,足以说明处于上升阶段的古代国家的进取精神。当然,日本古代贵族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创造其贵族文化。
日本最早的书面文学出现于八世纪初叶,即“奈良时期”(710-784)。这时期书面文学的代表作品有《古事记》与《万叶集》。当时日本还未创造出“假名文字”,这两部著作都是借助汉字写成的。前者汉字既用于表义,又用于表音;后者汉字主要用做表音符号。
《古事记》是一部记录古代神话与传说的作品,成书于公元712年。从这部书的序言可知,它是在天皇的命令下着手编纂的,目的是企图利用神话来证明天皇世系的权威性。由于这样的政治目的,所以《古事记》中有许多枯燥无味的关于神的世系的说明;虽然如此,并不能掩盖《古事记》这部书中一些生动的神话与传说的文学性。
神话是古代人通过美丽的幻想,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或表达人们对支配自然的渴望;《古事记》也不例外。它的许多章节或片断,如上卷中的“海幸与山幸的故事”写的是渔夫与樵夫两兄弟的争执,然后转入山幸与海神之女结婚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还以美丽的想象解释了旱涝潮汐的自然现象。“大国主命求婚的故事”是以几组爱情歌谣为主发展起来的。在中卷中插有多首古代集团战斗的歌谣,在下卷中记录了古代部族之间的战斗传说。所有这些,做为反映古代日本民族生活气息的最初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力量。
八世纪的下半期,出现了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全书共二十卷,收和歌(注:和歌是古代日本人将民族固有的诗歌与汉诗加以区分的称呼。一般称歌,即指前者;称诗,即指后者。和歌只有音数律这种固定的诗形,但无韵脚。)(长歌(注:长歌的音数律是5·7·5·7……7·7,其中5·7可反复多次,长短不限。)及短歌(注:短歌的音数律是5·7·5·7·7共三十一个音节。)等体裁)共四千五百余首。
《万叶集》的编次方法,各卷不同。有的卷按年代编次,有的卷按内容分为杂歌、挽歌、相闻歌(广义指赠答歌,狭义指恋歌)三大类,有的卷还设譬喻歌防人歌(戍边兵士歌)等目。
《万叶集》中有署名的作品,也有无名氏的作品。无名氏作品中有些属于民歌和民谣;具名的作品中有许多是所谓著名“歌人”的创作。集中署名的作者约四百五十人。
除少量传说的作者(其中有的可上溯三、四百年)外,著名“歌人”的活动,大多集中于七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这段时期。这百余年间又可细分为三个时期,前期的作者大多为天皇一族,如舒明天皇、中皇命、天智天皇、额田王等人。这个时期正是日本古代中央集权国家整备与壮大的时期,这些人的歌风,以格调醇朴率真见长。作歌的背景往往与当时历史的动乱有关。
中期的作者,活跃于七世纪中期以后与八世纪初,其中代表作者有柿本人麻吕、高市黑人、志贵皇子、山上忆良、大伴旅人、山部赤人、笠金村、高桥虫麻吕等人。这些人是当时的贵族或中、下级官吏。他们的歌风各具特色,对和歌形式的完成及使艺术手法臻于完美方面,各自做出了贡献。柿本人麻吕自古以来被称为“歌圣”,他善于驱使长歌这一形式,写出了许多怀古歌及挽歌,如《高市皇子城上殡宫歌》、《过近江荒都歌》以及别妻歌、悼念亡妻歌等等。他写的以宫廷为题材的怀古歌,表现了对古代国家上升时期的景慕与追怀,声调功雄浑、沉郁悲壮。抒发个人感情的别妻歌、悼亡歌写得语重意真、哀婉 切。他善于运用对句及枕词(注:“枕词”是和歌中特有的修饰语,亦称“冠辞”。每一枕词,与特定的被修饰语发生联系,起着丰富联想及调整音调的作用。),词藻赡富,音韵流利,于浑厚中见性情的真挚。高市黑人与山部赤人擅长写叙景歌,他们所写的自然风光,寓情于景,格调清新有致。高桥虫麻吕擅长写传说歌,卷九中收录了他写的《咏江水浦岛子歌》、《胜鹿真间娘子歌》、《见菟原处女歌》等以民间爱情故事为题材的长歌,刻画事件与人物细腻生动,别具特色。
在这些“万叶歌人”当中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山上忆良。他年轻时曾做过遣唐大使的随员来过我国。他的长歌,大多附有用骈体汉文写的长序,可以看出他汉文修养之深。他写的著名长歌《贫穷问答歌》是唯一直接反映古代律令制国家统治下人民遭受横征暴敛之苦的一首绝唱。现将这首歌的全文译介如下:
风雨交加夜,冷雨夹雪天。瑟瑟冬日晚,难御此夜寒。粗盐权下酒,糟醅聊取暖。鼻塞频作响,背曲嗽连连。捻髭空自许,难御彻骨寒。盖我麻布衾,披我破衣衫。虽尽我所有,难御此夜寒。贫尤甚我者,听我问数言:妻儿吞声泣,父母号饥寒。凄苦此时景,何以度岁年?
天地虽云广,独容我身难。日月虽云明,岂照我身边?世人皆如此,抑或我独然?老天偶生我,耕作从不闲。身着无棉衣,条条垂在肩。褴褛如海藻,何以御此寒?矮屋四倾颓,稻铺湿地眠。妻儿伏脚下,父母偎枕边。举家无大小,鸣咽复长叹。灶头无烟火,锅上蛛网悬。忍饥已多日,不复忆三餐。声微细如线,力竭软如棉。灾祸不单行,沸油浇烈焰。里长气汹汹,吆喝在房前,手执笞杖来,催逼田税钱。世道竟如此,此生怎排遣?
〔反歌〕(注:反歌——受我国“返辞”的影响,附在长歌之后,以短歌形式,集中地再次讽咏长歌的主要内容。)忧患兮人世!耻辱兮人世!恨非凌空鸟,欲飞缺双翅。
这首歌,有种种解释,一般倾向于将前半首理解为一个古代读书人对贫困处境的自诉,并推己及人,连想到较己尤甚的农民的痛苦,下半首是代农民作答,道出了在古代班田制下农民抢地呼天、欲告无门的悲惨处境。
《万叶集》的后期作者,以大伴家持及大伴坂上郎女为代表。这时,时代已进入律令制国家的后期,古代社会暴露出种种矛盾,开始走上解体的过程。大伴家持的歌风正反映了这个下降时期的特点。他的短歌,具有凄清纤丽、情致缠绵的特点。坂上郎女写了一些纤 绮丽的恋爱歌。
《万叶集》中无名氏的歌,约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这些歌中最具有特色的是收录在卷十四中的二百多首“东歌”(本州东部地区的民歌)。这些民歌大多以爱情为主题,不但语言纯朴自然,而且利用各种劳动场景做为比、兴等艺术手段,使这些民歌表现得情趣盎然,富于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有些歌还表达了不畏父母横暴干涉,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感情。卷二十里收录了九十二首“防人歌”(戍边兵士之歌)。这些歌反映了在古代天皇制下被迫别父母、抛妻子,兵士远戍边疆的凄苦哀怨之情。除去上边提到的一些歌之外,《万叶集》还收有不少反映古代社会各方面生活的作品。
总之,《万叶集》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古老,而在于它反映古代生活的深度及广度,在于它格调的深厚真挚。在《万叶集》以后,和歌逐渐堕落为贵族们吟风咏月的消闲品,贵族们利用它做为社交赠答及男女求爱的工具,或利用它进行宫廷“歌合”(比赛和歌的游戏)。到了平安、镰仓时期,和歌也专为贵族及僧侣们所占有,成了他们抒发个人纤弱感情的手段。
本时期除上述《古事记》与《万叶集》之外,在散文方面应提出的还有《风土记》。《风土记》原本是由当时各地方官吏,在天皇政权指令下编纂起来的地方志性质的书,但其中含有许多片断的地方传说与古老的故事。这些古老传说虽然经采集的地方官吏之手写得比较简略,但却往往洋溢着古代民众的生活情趣。有些传说,后来为民间故事所继承,不断加以发展。
本时期在韵文方面,除了《万叶集》及在《古事记》等书中保存下来的歌谣外,还有宗教性质的歌谣《祝词》,这是古代祷神用的歌词,其中有的歌词反映了古歌谣中那种韵律的美及形象生动的比喻手法。
二、古代后期文学
古代后期起自九世纪初,迄十二世纪末。日本通常将这时期称为平安时期。在这期间古代国家发生了质的变化,班田制的土地所有制逐渐为大土地私有的庄园制所代替。天皇逐渐失去了权柄,藤原氏一族掌握了中央的政治实权。古代贵族的进取精神逐渐消失,天皇家、藤原氏一族以及所有居住在平安京的贵族阶级,蜷伏在京城,倚靠从全国各地庄园收刮来的财富,过着纸醉金迷、尽情享乐的生活。
平安时期初期,和歌创作转入衰微。贵族之间,出现了模仿汉诗汉文的极盛时期,编纂了许多敕撰的汉诗集或诗文合集,如《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他们致力的是如何模仿汉诗汉文的华丽辞藻及技巧,至于内容则完全脱离不开空具形骸的宫廷游 生活。因此,这些汉诗汉文除了可以看出当时贵族模仿能力外,对日本民族文学的发展,关系不大。
另一方面,自平安初期以来,创造出由汉字草书演变而来的“平假名”,及由汉字偏旁演变而来的“片假名”。随后创造出假名与汉字交混在一起的书写方式。至此日本的民族文学,才获得了自由自在地表现的手段。这对平安时期的散文作品“物语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早出现用“假名”创作的物语文学是《竹取物语》,成书的具体年代及作者均不明,大体推测写于九世纪后半期至十世纪上半期。这是一个带有民间故事性质的作品,内容叙述月宫天女下凡,住在一个以伐竹为业的老翁家里,几个大贵族向天女求婚,均遭天女拒绝与嘲弄,最后天女返回月宫的故事。从这个故事的构思来说,情节单纯,类似民间故事或童话。但从细节来看,由于作者以幽默、讽刺的态度,刻画了五个向天女求婚的贵族的种种丑态,使得这部最早的物语文学,从它情节描写的细腻,人物性格的突出以及对贵族保持的批判精神来说,都给日本文学带来了崭新的东西。日本文学已脱离了那种片断式的古代传说,发展成具有完整结构的短篇小说的形式。
到了十一世纪初,由贵族妇女之手创作了许多散文文学的新的体裁:基于作者个人生活体验写成的“随笔文学”及“日记文学”,以及由作者通过虚构创造出来的“物语文学”等等。
十一世纪是属于整个平安时期的中期,是藤原氏“摄关”(注:“摄关”是“摄政”与“关白”的简称。藤原氏自九世纪中叶起,利用外戚地位,取得政治实权;在天皇未成人时,由藤原氏摄政,天皇成人后,则藤原氏改称关白。这种政权形态,一直延续到十一世纪中叶。)政治,达到顶峰并开始走上没落的转折期。贵族阶级本身的腐败堕落,地方豪族势力的伸张、新兴武士阶级的抬头,使得中央贵族内部孕育着日益深重的危机。而藤原氏一族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仍在热中于制造宫廷阴谋,在同族之间不断争夺外戚的地位,以达到操纵天皇这个傀儡的目的。他们除了卖官鬻爵,穷极奢欲之外,对全国政治完全丧失了处理的能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由中、下层贵族妇女之手创造了为这一时期整个贵族阶级奏挽歌的作品。这些贵族妇女,她们大多出身于中层贵族家庭,她们的父兄,或者不甘心雌伏于藤原氏一族之下,宁愿到地方去做“国守”成为熟悉地方民情的官吏;或者留在京师,以他们的才能学识,攀附藤原氏一族来维持他们不安定的地位。这些中层贵族出身的妇女,受这样家庭气氛及文化教养的熏陶,加上当时藤原氏一族习惯于招纳有才华的中层贵族妇女给他们做后妃的女儿充陪侍的女官,这样,这些中下层贵族妇女,既具有超出京城贵族狭隘眼界的教养,又身临目睹了藤原氏一族及宫廷等大贵族的生活实际情况,从而使这些贵族妇女产生了省察整个贵族生活的创作动机。
这个时期出现的、最有才华的贵族妇女作者,要首推紫式部(详见本章第二节),长达八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就是她的杰作。这部作品是平安贵族的一部百科全书,它揭示了整个宫廷贵族生活,描写了贵族妇女的群像,并对她们所处的悲惨地位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与《源氏物语》略约同时出现的还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这是一部随笔或札记性质的散文集,记录了她在宫廷做女官时的一些生活片断及见闻。作者完全是以肯定与赞美的态度来描绘当时的宫廷生活的。作品中还用“杂纂集类”的形式,正面表露了作者对自然美的纤细感受及贵族生活趣味的评价。她的观察及感受虽然十分敏锐与细腻,但她评价自然与人事的标准,一步也未离开贵族阶级的立场。
除了上述两个女作者外,还有其他一些贵族妇女的作品,如道纲母写的《蜻蛉日记》(成书大约在十世纪末,较早于《源氏物语》),写的是作者半生的生活体验,真实地记录了在贵族阶级一夫多妻制下自身的苦痛,这部作品无疑给《源氏物语》以多方面的影响。此外,还有《落 物语》(作者不明,大约在《源氏物语》前,作者为男贵族),描写贵族家庭继母虐待前妻女儿的故事,以及《狭衣物语》、《堤中纳言物语》等。前者也是描写贵族恋爱的故事,但思想境界远逊于《源氏物语》,后者是十个短篇集,追求故事内容的新奇,说明物语文学正在走上形式的多样化。
十二世纪末叶,文学中出现了两种新的体裁。一种是被称为“历史物语”的《荣华物语》及《大镜》。前者叙述了宇多天皇(887)至堀河天皇约二百年间的“摄关”政治的大致情况,而以藤原道长的专权时期为重点,描写了他权势赫赫的半生及围绕他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后者仿效我国《史记》的列传体,记叙了简单的帝纪,然后着力写了登上权臣宝座的藤原氏一族势要人物的列传。《大镜》对于“摄关政治”时期贵族内部的权势之争有所批判。
大致与《大镜》、《荣华物语》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部《今昔物语集》。这是一种其内容及文体与上述反映贵族生活完全异趣的崭新作品。全书共三十一卷(现存本已残缺不全),收有一千余篇短小的故事。日本文学史上将这种文学形式称之为“说话文学”,以区别于那些反映贵族生活的“物语文学”。《今昔物语集》收集的“说话”,一多半属于“佛教说话”,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卷二十二以下的“世俗说话”。从这类“说话”中可以看到平安末期新兴的武士阶级的面貌及一般民众的生活情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包罗了农民、渔民、贵族、僧侣、武士、商人、艺人、妓女、盗贼等当时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反映了这些人物的不同行径与新的历史时期各阶层的思想状态。这部作品,在语言上也有所创新,它使用的是明快、简素的“和汉混淆体”,完全脱离了“物语文学”那种纤弱的、情绪缠绵的“王朝文体”。因此,无论就内容或就表现形式来说,都给即将到来的镰仓时期反映武士阶级的文学开辟出新的蹊径。这部作品的出现,说明贵族文学已趋于没落,而崭新的文学正处于破晓的状态之中。
三、中世纪前期文学
这里所说的中世纪前期,是指从十二世纪末至十六世纪末这段时期。
从十一世纪后半期,藤原氏专权的“摄关政治”出现了破绽,天皇氏一族从藤原氏夺回了政治实权,历史进入了“院政时期”(由退位了的天皇掌握政治实权),但这并不能挽救已经腐朽、注定灭亡的贵族统治。经过1157年的“保元之乱”以及接踵而来的“平治之乱”,从庄园制产生出来的地方武士阶级(武装了的地主阶级),挤入了中央政治舞台,并以源氏与平氏两家武士之争的形式,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乱,终于在十二世纪末出现了由新兴的武士阶级掌握全国政权的局面。这就是源氏所建立起来的“镰仓幕府”。十四世纪初一度出现了由京都贵族策划的旧天皇政治的复辟。至1338年才又由武士足利尊氏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室町幕府”。接着于十五世纪中叶,武士阶级内部又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居于中央政权的武士——足利氏逐渐失去了统治全国的力量,出现了诸侯连年征战不已的“战国时期”。在这种分裂与统一的过程中,终于消灭了古代贵族政治上的残余势力,使日本社会逐渐完成了封建体制。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非常急剧,也由于统治者之间的不断纷争,使得统治力量日趋削弱,民众的力量日益兴起与壮大。特别是进入十五世纪以后,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同时出现了都市要求自治的动向。在思想方面,由于统治者权威的失坠,出现了“下克上”的时代思潮,使得这时期文学具有鲜明地反映民众力量兴起的特色。
这时期文学中最早出现、同时又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是“军记物语”。十三世纪三十年代,首先出现了《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然后继之又出现了《平家物语》。由于这时的政治动乱离不开战争这一形态,所以这些作品都着力描写了新兴的武士驰骋战场,叱咤风云的形象。虽然一般把这类文学,统称为“军记物语”或“战记物语”,但实际上它所反映的决不单纯是战争场面,而是多方面地反映了进入巨大历史转折期的阶级的、政治的种种面貌。
《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两书的作者不明,据推两书可能出于一人之手。《保元物语》描写的是历史上的“保元之乱”,《平治物语》描写的是继“保元之乱”三年后又一次出现的“平治之乱”。这两部作品有个共同主题,那就是通过文学形象,如实地生动地再现新兴的武士阶级的种种的刚毅、勇猛的性格以及他们的积极、果断的行动。前一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无位无官”的武士源为朝,为他在宫廷权力之争中的智勇以及失败后被流放,最后终于兵败自杀的过程;后一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是恶源太义平,书中专写了他的勇猛的作战行动及他那虎虎有生气的武士性格。这两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由担当新的历史使命的武士阶级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刻画了已处于垂死阶段的公卿贵族的怯懦与愚蠢。这两部作品与前一时期经贵族妇女之手创造出来的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呈现出本质上的不同。这两部作品在着力描写新兴阶级的英雄人物行动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了做为新的剥削阶级——武士本质的另一侧面:这些武士们在卷入贵族内部的阴谋纷争当中,进行了子杀父,兄杀弟等等极其无情的骨肉相残。作品对这方面的忠实描写,有力地传出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两部作品,继承并发展了《今昔物语》在语言上的创新,说明一种新的文学的产生必然要求作品的语言突破以往的窠臼,要求创造出崭新的艺术形式。
《平家物语》是较前两部作品稍晚一些时候出现的军记物语的白眉。这部作品内容也是描写平安末期新兴武士阶级与中央贵族势力进行殊死斗争、终于将政治实权掌握到本阶级手中的巨大历史事件的。就文学成就来说,它所反映的时代本质,较前两部作品更为深刻,塑造的英雄人物,也更富于生命力。
《平家物语》这部作品,正如书名所示,是以源平之争的一方,平氏一族的命运为主线进行描绘的。这部作品,带有浓厚的佛教净土思想,对平氏一门灭亡的命运,做了种种文学上的渲染,使用了悲哀的语调,极尽叹婉之能事。这说明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平氏这一边的。但是,作者对这次巨大的历史动乱,又表现出矛盾的态度。固然作者从贵族出身的立场出发,对贵族化了的平氏子孙的所谓风流蕴藉的生活态度,处处流露了赞美与同情;但从客观上却揭示了失去了原有武士阶级属性的平氏一族,早已变得纤弱萎靡,他们的灭亡,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作者虽然认为兴起于东国的源氏一族,都是一些不解风流为何物的、蛮勇粗犷的武士,甚至加以讪笑;但在描写他们作战的场面时,却又不能不投以惊异、畏服与赞叹的目光。作者生动地刻画了他们那种刚毅、勇敢的性格,描绘了他们疾风怒涛的战斗行动,尤其是对源氏大将们的英雄形象,对源义仲、源义经等人的刻画,写得有声有色。这部作品,除了对史实上的人物,予以文学加工,塑造了许多鲜明的典型外,还插入了若干“王朝物语式”的故事,如“祗王祗女的故事”、“小督的故事”等。这些哀婉有致的、关于妇女命运的描写,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浓厚的抒情色调。
这部作品,在艺术语言上,也为古典文学开辟了崭新的境地。它继承了《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开创出来的刚劲有力的汉文调的文体,又将《源氏物语》以来王朝物语中那种缠绵悱恻、委婉多姿的和文调文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和汉混淆”、韵散结合的文体,对以后文学语言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镰仓初期出现的这几部作品,是在武士阶级已取得政权的政治背景下出现的。它有力地反映了处于上升阶级武士阶级的思想感情。这几部作品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它们带有说唱文学的性质。这些作品,原始版本与现今普遍流传的版本之间,存在着不断增添、润色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可能有演唱这些作品的盲艺人——“琵琶法师”参与其间,说明了这类文学创作的民众性。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长期地广泛地为以后的戏曲、小说所大量继承,在为后世戏曲及民间文学素材的丰富来源,直到今天,日本古典文学中广为流传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大多出自这几部作品。
从十四世纪开始,在当时的京城周围的农村里,通过演剧酬神逐渐兴起了民间戏剧和艺能。后者逐步沿着音乐、舞蹈及表演等综合艺术的方向发展,后来成为一种以音乐、歌唱、舞蹈为主的戏剧——“能”。前者则发展成为以对白为主的独幕喜剧——狂言。最初,狂言都是演员们的即兴创作,讽刺当时的某些社会现象。到了十五世纪前后,它逐渐成熟,产生了许多定了型的传统剧目,它的脚本也由各个流派之手固定并保存下来。现在的狂言脚本,约有三百出左右。
狂言的高度文学价值,在于它反映了当时民众力量的兴起。狂言采取集中一个突出的矛盾,用喜剧或闹剧的手法,讽刺、嘲笑了欺压民众的一切邪恶势力。狂言中的许多所谓“大名”类的剧目,大多写的是“大名”(中世纪京都周边的地主武士阶级)与仆人的矛盾。在剧中“大名”被刻画为贪婪、蛮横而又愚蠢的形象,而仆人则被刻画为聪明、伶俐,富于机智的人物。在戏剧冲突中,一般都以“大名”的失败与仆人的胜利告终。狂言还对僧侣使用欺骗手段进行敛财以及酗酒渔色等等丑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嘲笑。对统治者乐于宣扬的、束缚人民意识觉醒的神鬼观念,进行了大胆的嘲弄。狂言中的妇女形象也是性格泼辣,非常富于进取的。正是由于狂言充分反映了中世纪“下克上”的时代精神,因而它深受下层民众的喜爱,在民众的支持下日益得到发展。当然,由于狂言在逐步走上定型化之后,它的讽刺精神已不象它初期即兴演出时那样泼辣尖锐;到了室町时期,它成了演出“能”时的附随物——幕间狂言,做为狂言生命的讽刺精神,也就停滞了。
这时期的另一种文艺是连歌。这是利用一首和歌分为上下两句,由不同的作者进行互相连句的艺术形式。它原是出于平安贵族比赛和歌时,做为会后余兴发展起来的,最初在贵族及僧侣之间流行,后来浸透到下级武士及商人之间,形成一种带有娱乐、社交性质的文艺活动。参加连歌的一些人,叫做“连众”,他们一边进行连歌创作,一边进行互相品评与欣赏。但后来出现了种种连歌的繁琐规则,形成了教授及品定连歌优劣的“宗师”制度。到了室町末期,连歌的首句独立出来,发展成为俳句,而连歌本身则逐渐丧失了它的生命力。总之,连歌做为一种特殊创作活动的文艺,就其发生与发展来说,也是这时期文学逐渐走上民众化的一种反映。
这时期另一种文学创作是随笔文学。其代表作品有十三世纪初期问世的《徒然草》,作者为鸭长明(1153-1216),十四世纪初期出现的《方丈记》,作者田兼好(1283-1350)。这两个作者均出身于没落的贵族阶级,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后来出家为僧。他们对本阶级注定的死亡命运都有一定程度的觉察,但又不能对新兴的武士阶级做无条件的肯定,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旁观的态度,过着一种隐逸的生活。在《方丈记》中记录了平安末期的天灾与人事异变,对异族争夺权势持否定的看法,也流露了隐逸者的、消极的生活态度。《徒然草》是一种杂感性质的小品集,全书分为长短不等的二百四十三段,作者的人生观基本上也是消极的,但也有一些短小精辟的寓意性小故事,富有教训意义,说明了作者重视理性的一面。这两部作品,由于采用的都是和汉混淆体,文字精确简练,长期被视为古文的典范。书中一些消极的、旁观者思想及生活态度,对后世文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这时期,还有两部值得提出的作品,一部是《曾我物语》,成书于十四世纪初,一部是《义经记》,成书于十五世纪初期至中期之间。前者是写两个武士曾我兄弟为父报仇的故事,后者是写源氏的大将源义经的传奇式的、悲剧性的一生。这两部长篇作品,虽然也列入军记物语之中,但它们描写的已不是象《平家物语》那样大规模的武士阶级的集团搏斗,而是专门刻画武士个人历尽艰辛、波澜起伏的一生。这两部作品实际是摭拾当时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关这些人物的传说,经过加工润饰而成的。由于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无其他回答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