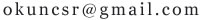《蚁生》节选之一
三十七年前——那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几乎是上一辈子的事了——十八岁的女知青郭秋云正同她的颜哲哥哥在知青农场的堰塘边幽会时,突然得知一个噩耗:场长赖安胜要暗杀颜哲!初听这个消息俩人都不信。赖安胜是个暴君加色鬼,他们相信他会干很多坏事,但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策划搞暗杀,这似乎太离谱,不符合逻辑。何况消息是刘学孝送来的,这更减弱了消息的可信度。刘学孝与他俩从小是街坊,又与颜哲是高中同班同学(秋云比他们低两届),关系一度不错。但文化革命开始后,很多人都展现出了人性的另一面,这一面也许连他本人都不自知。颜哲的父亲颜夫之和母亲袁晨露在学校被迫害,双双自杀,刘学孝可以说是掷出第一块石头的人,而且直到下乡后,他对自己的行为从无半句忏悔。由于这些历史恩怨,颜、刘之间一直横亘着很深的敌意。这会儿他突然要扮成颜哲的救命菩萨,谁信?
但那是一个疯狂错乱的年代,许多不合逻辑的事反倒成了正常。后来的事态证明,刘学孝送来的这个消息竟然是真的!并由此引发出一桩死亡七八人的血案,死者包括领头策划暗杀的赖安胜、送信的刘学孝、两个凶手、公社干部老魏叔和他的相好谷阿姨,等等。颜哲倒没有死于赖安胜之手,但也因此失踪,至今生死不明。
那段经历在秋云心中割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她原以为这道伤口永远不会平复了。但时间真是最强大的巫师,它慢慢抚平了伤口,让秋云最终接受了颜哲的死亡——他如果没死,在风平浪静后绝不会一直躲着自己!后来秋云回城,在麻绳社当工人,结婚,生儿育女,赶着末班车上大学,当语文教师,照顾孙子外孙。她的心被世俗生活填满了,无暇回顾往事。旧日的记忆被仔细打叠好,封存到记忆深处,蒙上了厚厚的尘土。
也许是上帝的安排,恰好在退休后,秋云听说农场旧址发生了一件“灵异之事”——颜哲的衣冠冢前出现“蚁群朝圣”。为了验证它,秋云拉上丈夫高自远到故地重游。农场已经不复存在,当年的知青不用说早就走光了,驻场的十八个老农也早已星散,说不定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了。知青们当年的住房是土坯房,全部毁于那年的洪水,只余下砖砌的粮库和场长室,也已破败不堪,门窗都被偷走了。秋云祭奠了七个死者的坟墓和颜哲的衣冠冢。八个坟头坐落在农场最高的那片荒岗上,长满及膝深的野草。多半是这些野草的保护,它们才没有被三十七年前的雨水冲平。她听到的那个传说并非虚言,这儿的蚂蚁极多,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密密麻麻,来来往往,忙忙碌碌,其活动显然以颜哲的衣冠冢为中心。附近的乡人们说,这样的“蚂蚁朝圣”是从三四天前开始的。“真是怪事啦,莫不是坟里的死人显灵?”
秋云当然知道这件“灵异之事”的原因,不是什么死人显灵,而是科学,是技术。她目睹过颜哲用一种叫“蚁素”或“利他素”的玩意儿,在瞬间招来千千万万只蚂蚁,就如眼前的景象一般。而这种蚁素是颜哲父亲,一位著名的昆虫学家,一生研究的结晶。这么说,那个握着蚁素秘密的人——颜哲——也许并没死去?是他回到故地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他是用这种方法向别人(主要是秋云)显示他的存在?秋云暗暗揣着一份希望,仔细寻找有关迹象。
在农场留连的时间里,秋云一直情绪黯然,默默无语。她老伴儿高自远虽然没在这个农场呆过,但也下过乡的,而且知道妻子在农场的初恋,很能体会妻子的心情。在他体贴的陪伴下,秋云到处捡拾着记忆的残片。原来那些被打过封的、蒙上尘土的记忆并没有褪色啊,它们仍然清晰鲜亮、栩栩如生。郭秋云就像经历了一趟时间旅行,她的灵魂离开五十五岁的身体,以第三者的视角,观察着一个十八岁女知青的人生之路,体会着她的悲乐苦辛,爱恨情仇。不过这不是单纯的场景重现,当她以历尽沧桑的视角重历自己的人生之路时,自然有很多不同于过去的感悟。
在不断强化记忆的过程中,三十七年前那个女孩儿的印象逐渐饱满和清晰,直到她从第三者变成了“我”,变成这个五十五岁的郭秋云的意识主体。
《蚁生》节选之二
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中,蚂蚁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种群。这种社会性昆虫的社会比人类社会先进得多,那是完全利他主义的社会,每一个个体都是无私、牺牲、纪律、勤劳的典范。最可贵的是:蚂蚁的利他主义完全来自于基因,来自于生物学结构(腺体及信息素等)的作用,生而有之并保持终生,不需要教育、感化、强制、惩罚,不需要宗教、法律、监狱和政府。所以,蚂蚁社会的每一滴社会能量都被有效利用,没有任何内耗。由于蚂蚁个体的利他主义是内禀稳定的,因而其社会也是稳定和连续的典范,8000万年来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任何断裂。
和它们相比,万物之灵们真该感到羞愧。人类的一万年文明史绝大部分浸泡在丑恶、血腥、无序、私欲膨胀和道德沦丧中。上帝和圣人们的“向善”教诲抵不过众生的“趋恶”本性,好容易建立起来的“治世”只是流沙上的城堡,转眼间就分崩离析。
如果我们能以蚂蚁社会为楷模,人类文明该发展到何等的高度!
——摘自昆虫学家颜夫之的著作《论利他主义的蚂蚁社会》
――1948年发表于英国《理论生物学杂志》
《蚁生》节选之三
恋人幽会时的时间是最快的,我们坐在堰塘堤上,扯着两家的闲话,不知不觉天已晚了。颜哲说:怕是有十点了吧,该回去了,要不又有人说闲话了。我说,好吧,回去吧。颜哲站起来,笑着对我张开双臂。这是我们的老程序,告别前颜哲一定要再和我亲热一次。我投身入怀,享受着他的热吻和拥抱。正在情浓时,忽然听到很近处有一声冷笑!俩人一机灵,立即分开身子,我忙整理好衣服,仔细搜索四周——不,不是幻觉,隔着一株蓖麻,仅一米之外有一个清晰的男人身影。他是何时走近的,我们一点没察觉,我们信赖的蓖麻丛屏障反倒成了对方的掩护。我声音战栗地问:
“谁?”
那边冷冷地回答:“是我,刘学孝。我找颜哲有急事。”
我一下子面庞发烧。我想他一定听到了我们的情话,也看到了我俩刚才的亲热。让刘学孝看到这些,比让其他人看到更令我难堪。我们从小是街坊,而且在年岁渐长时,学孝哥分明是对我有意的,但我那时已经选定了颜哲。以后,我能从学孝哥身上看出他对颜哲的敌意。文革开始时,他第一个对颜伯伯掷出那块致命的石头,对此我不会为他辩解,那是他内心深处兽性的公开显露。自从他显露了兽性的一面后,我和他的关系也非常冷淡了。不过,私下里我也曾猜想,当他决定向颜哲的父亲落井下石时,也许,“情敌”的嫉恨也是因素之一?
不管怎样,既然让他撞见了,我也得去面对。我绕过那株蓖麻,硬着头皮向他走过去,问:
“学孝哥,你找颜哲有事?”仓促中,我说了一句不算得体的话,“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他又是一声冷笑,“你问问全农场的人,哪个不知道这儿是你们幽会的老地方。”
我更加脸红了,原来我们自以为保护得很好的秘密,已经成了农场的公开话题!身后的颜哲用力拉了拉我,虽然没有言语交流,我也能揣摸出他的意思:不用在他面前难为情,恋人有点亲热举动算不上丢人事!然后颜哲平静地问:
“找我啥事?”
刘学孝狠狠地撂了一句:“啥事?对你生死攸关的大事!”
我俩有一点吃惊,但也仅是“有一点”而已。颜哲只是一个普通知青,没杀人放火没写反动标语,怕是不会有什么性命攸关的大事吧。颜哲又拽了拽我,分明是说:别听他放屁!
刘学孝知道我们不会信,冷冷地说:“颜哲,你是不是打算到省里去告赖安胜?”
我们这次真的吃惊了!因为直到目前,这还是只有我们俩才知道的私房话。看来刘学孝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
这事是因孙小小而起。农场共有北阴市和旧城县的六十八名知青,孙小小是年龄最小的,下乡时不足十四岁。按说,这个年纪是不够下乡条件的,但孙小小家门不幸,母亲和姐姐都是县里有名的“破鞋”,据说她上高中的姐在教室里靠墙站着就把那种事办了。他父亲嫌丢人,愤而离家出走,不知所终。后来,旧城县兴起“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热潮。孙小小的母亲和姐姐既然是有名的“破鞋”,自然头一批被撵下乡。孙小小不能一个人留在家里,只好“照顾”到知青农场来。知青们都知道这些根由,因而对孙小小有潜意识的歧视。再加上小小有点缺心眼,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让她成了男知青们经常逗弄的对象。
那天在稻田里拔稗子,知青林镜逗小小:你看你,拔错了,拔的都是秧苗!小小看看手里的稗子,不服气地说:不是,是稗子,秧苗我没拔!
林镜马上接过话头:“你没‘爸’?你‘爸’可多了!”
周围的男知青们哄然大笑,小小还是听不懂,气恼地一遍遍重复:我没拔,就是没拔!她越说,大伙儿越笑。我看不过,托故把孙小小赶走,对林镜说:
“我知道你们看不起小小的家世。但那不是她的错。你们要是这么着一直耍弄她,只会有一个结果:让她走她妈和她姐的老路。你们愿意这样吗?”
林镜刷地红了脸。他其实是个好男孩,平素与我和颜哲很友善。听了我的责备,非常难为情,以后再也不戏弄小小了,反倒经常护着她。小小也凭本能认准了我,就像小狗小猫能认准家里哪个人最亲它一样。她有什么心里话,一点也不瞒我。
前天晚上,我已经睡着了,忽然有人扯我的胳臂,我睁开眼,原来是孙小小。她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不让我说话,然后悄悄拉我出门。我们到了离知青宿舍较远的地方,在这儿说话不会有人听到了。我小声问:
“啥事?把你紧张成这个样子!”
她确实非常紧张,浑身止不住发颤,两眼像高烧病人那样怪异地明亮。我原以为她是让吓的,后来才(非常痛心地)知道,她不光是害怕,更主要是亢奋,而这一幕最终极大地影响了她,让她一生都走歪了。
她说:“赖场长刚从我们屋出来,我就来你这儿了!”
衬着她失常的表情,这句话让我有了误解,莫非那个色鬼场长把小小怎么了?原来不是,事情是这样的:孙小小与岑明霞和宗大兰住一间房,这些天宗大兰回北阴探亲去了,只留下小小和岑明霞两人。一个小时前,小小刚睡下,赖场长进来(天热,知青们睡觉都不关门的),熟门熟路地走向里边岑明霞的那张床,撩开蚊帐坐到床边,两人小声谈话,谈了很久。小小在这边竖起耳朵听,能听出个大概。赖场长说,农场已经来了第一批招工指标,可惜不大满意,县纺纱厂的集体工指标,不是全民工。他说,让不让你走这批指标,我很犯难。走吧,也许以后有更好的地方;不走吧,万一以后的指标还不如这次呢。你说该咋办?岑明霞小声说:我听你的,听哥的安排。那边沉默一会儿,赖场长小声冒出一句:
“⋯⋯也舍不得你。”
后来那边就不说话了,只听见床吱呀吱呀地响着⋯⋯
听着小小绘声绘色的描述,我止不住手足发冷,那是缘于极度的愤怒。说句没道理的话,如果赖安胜把那个贱女人唤到场长室里去办那事,我肯定不会这样愤怒。但他竟公然当着另一个女知青的面!当着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他竟然一点也不害怕别人告发他!
早在知青下乡之前,上边就深知女知青们面临的危险:女知青和他们的男上级,一边是比农村姑娘嫩生风情的城里女学生;一边是握有生杀大权的、又常常处于性饥渴状态的农村男干部。这种双重的不对称会造成什么后果,那是不难想象的。所以,上边制订了保护女知青的强力措施,甚至比保护军婚更严厉。在旧城县就曾发生过轰动全县的一件事:一位女知青到公社邮局去寄信,一个同她相熟的男职员一时发贱,开了一个过头的玩笑,拿手中的剪刀把她的辫梢剪掉一段。这位姑奶奶大怒,立即喊来男知青把那人痛殴一顿,又告到县里。最后那人被判两年徒刑,开除公职,罪名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犯”。
可是在我们农场,那个色鬼竟嚣张到这样程度!我强使自己冷静下来,考虑片刻,劝小小说:
“可不敢告诉别人!这是大事,如果你说出去,又没有真凭实据,赖安胜一定饶不了你。”
小小一个劲儿点头,说:我只对云姐你一个人说,绝不会告诉别人。我于是劝小小回去睡,免得岑明霞发现那件事之后她偷偷溜出来会起疑心。
第二天晚上和颜哲幽会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颜哲顿时勃然大怒,发怒的原因和我一样:不光是因为赖安胜诱奸女知青,更因为他做事之嚣张。颜哲甚至骂了粗话,还愤愤地说:“太不把知青当人了!我明天就去县里去告他,县里告不倒我去省里!”
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已经经过一天的沉淀,所以比他冷静一些。我说:
“我不反对你告,但是得慎重。这种事岑明霞绝不会承认的,孙小小这种见证人也十分靠不住。弄不好赖安胜会反咬一口,说你陷害革命领导干部。”
我的话让他冷静下来。最后我们商定,先不去告,暗地里收集证据,等有把握了再说。这会儿听刘学孝拎出我们的密语,我十分吃惊。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些话我从没告诉过第三者,想来颜哲也不会说。我忽然想到:既然刘学孝今天能悄悄来到我们身边而不被觉察,也许那天他也来了,偷听了我们的谈话,又向赖安胜告发?也许他一直在跟踪我,用阴森的目光,看他心仪的姑娘咋和别的男人亲热?我在心中再次仔细地捋一遍,确信这个推理有八成是对的。这让我止不住心中发颤——不光是因为对这件事的恐惧(原来我和颜哲在这儿亲热时一直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们!),而且是对人性的恐惧。如果刘学孝真的干了这些事(跟梢、偷窥和告密),那这人就太可怕了!
但为什么他又会跑来为我们通风报信?我没来得及继续想下去,因为刘学孝紧接着抛出一个惊人的消息:
“赖安胜已经知道颜哲要告他!他打算做掉颜哲以除去后患。凶手都找好了,是咱场的陈得财和陈秀宽。”
我俩大吃一惊。不过虽然震惊,我们打心眼里不信。赖安胜确实是个坏种,说他干啥坏事我们都信,但这么公然策划杀人未免太离谱。也许这是刘学孝的阴谋,他想挑起颜哲和赖安胜拼命,好从中渔利⋯⋯
刘学孝显然深知我们的思路,断喝一声:“你们以为他不敢!别迂了!你们只用想想,如果奸污知青的事捅出来,他会啥下场,就知道他敢不敢干了!”
我俩一惊,立时悟到刘学孝的话是对的。据传赖安胜已经在场里奸污了三四个女知青,这些如果都坐实,那至少是十年徒刑,如果撞上“严打”,挨枪子也是可能的。“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他为了保住场长的宝座,为了避免坐牢甚至挨枪子的下场,当然会毫无顾忌地铤而走险。我们确实是书呆子,即使在运用智谋策划政治战争时,也不由自主地按“羊”的思路,而不会体悟到“狼”的想法。
而刘学孝显然是深谙“狼”道的。
他看看我俩的表情,知道他的话已经击中十环,便不欲多停,说:“反正我已经尽心了,信不信由你们。颜哲你好自为之吧。”
他就要离开,颜哲问了一句:“刘学孝,我能问问你这样做的动机吗?”
刘学孝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冷冷地说:“赖安胜是个不知死活的驴种,杀人这种事也敢干?早晚会露馅,我才不会陪着他跳火坑。再说,咱们毕竟是老街坊老同学,我不想让你不明不白地送命。”
我和颜哲对视一眼,心照不宣。我根本不信他说的后一个原因。理由很简单:如果他透露的消息是确实的,那他很可能先做了告密者,否则赖安胜不会这么信任他,甚至让他参与(至少是风闻)了杀人预谋。
刘学孝又对颜哲说:“不过,赖安胜的事拿不到真凭实据之前,我不会出头为你做证人的。我把话说前头,到时候你别烦我。”
颜哲说:“对,你不会为我火中取栗的。等我把赖安胜告倒,你就可以安安稳稳做场长了。”
刘学孝没有说话,匆匆离开。
我俩开始认真思索面临的危险,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已经真真切切地悬在头顶了。也许,两个凶手这会儿已经潜伏在四周?我不敢在这儿多停,拉着颜哲,在蓖麻丛的掩护下,悄悄转移到一个新地方。确认周围没人潜伏后,我急迫地说:
“先不管刘学孝是什么动机,我相信他说的消息是真的。咱们不能坐以待毙。颜哲,你继续呆在农场太危险,谁知道姓赖的啥时候下手?防不胜防。我想咱们干脆破釜沉舟,到县里去告他。只要把这件事公开,他就不敢再对你下手了。”
颜哲摇摇头:“你昨天说的话是对的。这泡脓还没熟透,不能硬挤。咱一定得拿到真凭实据。否则,如果刘学孝不认账,孙小小又被吓住哄住,那咱们就输了,反倒落个陷害革命领导干部的罪名。”
“我也考虑到这种可能,那就实行第二个办法:你告病假,回家或到我亲戚家躲几个月。我想赖安胜再厉害,也不过能在农场一手遮天,总不至于把手伸到别的县市吧。等这泡脓熟透、有人出来作证时,你再回来,那时就安全了。”
颜哲摇头,“这样未免太怯弱了。”
“那你说,该咋办?”
颜哲认真思考着,我在月光下紧紧地盯着他的面庞。他的表情忽然有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似乎某个困扰多时的问题忽然得到解决,脸上也绽出轻松的笑容。他说:
“秋云我有办法了,也许这是天赐的机会,让我完成早就想干的一件大事。我有办法了,绝对可靠的办法。至于详情我暂时不能向你透露,你只管放心吧。”
他这番话让我充满狐疑,不禁想起他早先曾说过的:他要用父母留下的一大笔钱办一件“大事”。我原以为,他所说的“大事”是不确指的,只是对今后的一种预期。但从这会儿的意思来看,这件大事是具体的,是早有腹案的。我生气地说:
“你不告我详情,我咋能放心?这是生死大事,你别这么吊儿郎当的!”
颜哲笑了,“秋云你别问,该说的时候,我肯定会第一个告诉你。”
“不行!你至少得告诉我个大概。”
颜哲犹豫片刻,“那我只能告诉你,我要启用我爸留下的一个宝贝,专门对付赖安胜这类坏人的,绝对有效。可惜他没来得及用。”说起父亲,他的情绪有一刹那的黯然。“你放心吧,真的尽管放心,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何况——”他一把搂住我,在我耳边轻笑道,“你还没有为我生儿育女呢,我咋舍得扔下你,一个人先走?”
他的笑声中有发自内心的轻松,让我也变轻松了。我骂他:“不要鼻子座(脸)的东西。这个紧要当口,还惦记着说疯话。”
然后我们回去。他的轻松有效地安抚了我的焦灼——不,他不光是轻松,这个词尚不足以形容他的变化。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只彩色的蝴蝶从原来的蛹壳中破壳而出。他显然下定了决心,今后要为新的目的而活了。
不过我并不知道这个变化的真正原因。
三十七年前——那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几乎是上一辈子的事了——十八岁的女知青郭秋云正同她的颜哲哥哥在知青农场的堰塘边幽会时,突然得知一个噩耗:场长赖安胜要暗杀颜哲!初听这个消息俩人都不信。赖安胜是个暴君加色鬼,他们相信他会干很多坏事,但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策划搞暗杀,这似乎太离谱,不符合逻辑。何况消息是刘学孝送来的,这更减弱了消息的可信度。刘学孝与他俩从小是街坊,又与颜哲是高中同班同学(秋云比他们低两届),关系一度不错。但文化革命开始后,很多人都展现出了人性的另一面,这一面也许连他本人都不自知。颜哲的父亲颜夫之和母亲袁晨露在学校被迫害,双双自杀,刘学孝可以说是掷出第一块石头的人,而且直到下乡后,他对自己的行为从无半句忏悔。由于这些历史恩怨,颜、刘之间一直横亘着很深的敌意。这会儿他突然要扮成颜哲的救命菩萨,谁信?
但那是一个疯狂错乱的年代,许多不合逻辑的事反倒成了正常。后来的事态证明,刘学孝送来的这个消息竟然是真的!并由此引发出一桩死亡七八人的血案,死者包括领头策划暗杀的赖安胜、送信的刘学孝、两个凶手、公社干部老魏叔和他的相好谷阿姨,等等。颜哲倒没有死于赖安胜之手,但也因此失踪,至今生死不明。
那段经历在秋云心中割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她原以为这道伤口永远不会平复了。但时间真是最强大的巫师,它慢慢抚平了伤口,让秋云最终接受了颜哲的死亡——他如果没死,在风平浪静后绝不会一直躲着自己!后来秋云回城,在麻绳社当工人,结婚,生儿育女,赶着末班车上大学,当语文教师,照顾孙子外孙。她的心被世俗生活填满了,无暇回顾往事。旧日的记忆被仔细打叠好,封存到记忆深处,蒙上了厚厚的尘土。
也许是上帝的安排,恰好在退休后,秋云听说农场旧址发生了一件“灵异之事”——颜哲的衣冠冢前出现“蚁群朝圣”。为了验证它,秋云拉上丈夫高自远到故地重游。农场已经不复存在,当年的知青不用说早就走光了,驻场的十八个老农也早已星散,说不定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了。知青们当年的住房是土坯房,全部毁于那年的洪水,只余下砖砌的粮库和场长室,也已破败不堪,门窗都被偷走了。秋云祭奠了七个死者的坟墓和颜哲的衣冠冢。八个坟头坐落在农场最高的那片荒岗上,长满及膝深的野草。多半是这些野草的保护,它们才没有被三十七年前的雨水冲平。她听到的那个传说并非虚言,这儿的蚂蚁极多,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密密麻麻,来来往往,忙忙碌碌,其活动显然以颜哲的衣冠冢为中心。附近的乡人们说,这样的“蚂蚁朝圣”是从三四天前开始的。“真是怪事啦,莫不是坟里的死人显灵?”
秋云当然知道这件“灵异之事”的原因,不是什么死人显灵,而是科学,是技术。她目睹过颜哲用一种叫“蚁素”或“利他素”的玩意儿,在瞬间招来千千万万只蚂蚁,就如眼前的景象一般。而这种蚁素是颜哲父亲,一位著名的昆虫学家,一生研究的结晶。这么说,那个握着蚁素秘密的人——颜哲——也许并没死去?是他回到故地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他是用这种方法向别人(主要是秋云)显示他的存在?秋云暗暗揣着一份希望,仔细寻找有关迹象。
在农场留连的时间里,秋云一直情绪黯然,默默无语。她老伴儿高自远虽然没在这个农场呆过,但也下过乡的,而且知道妻子在农场的初恋,很能体会妻子的心情。在他体贴的陪伴下,秋云到处捡拾着记忆的残片。原来那些被打过封的、蒙上尘土的记忆并没有褪色啊,它们仍然清晰鲜亮、栩栩如生。郭秋云就像经历了一趟时间旅行,她的灵魂离开五十五岁的身体,以第三者的视角,观察着一个十八岁女知青的人生之路,体会着她的悲乐苦辛,爱恨情仇。不过这不是单纯的场景重现,当她以历尽沧桑的视角重历自己的人生之路时,自然有很多不同于过去的感悟。
在不断强化记忆的过程中,三十七年前那个女孩儿的印象逐渐饱满和清晰,直到她从第三者变成了“我”,变成这个五十五岁的郭秋云的意识主体。
《蚁生》节选之二
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中,蚂蚁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种群。这种社会性昆虫的社会比人类社会先进得多,那是完全利他主义的社会,每一个个体都是无私、牺牲、纪律、勤劳的典范。最可贵的是:蚂蚁的利他主义完全来自于基因,来自于生物学结构(腺体及信息素等)的作用,生而有之并保持终生,不需要教育、感化、强制、惩罚,不需要宗教、法律、监狱和政府。所以,蚂蚁社会的每一滴社会能量都被有效利用,没有任何内耗。由于蚂蚁个体的利他主义是内禀稳定的,因而其社会也是稳定和连续的典范,8000万年来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任何断裂。
和它们相比,万物之灵们真该感到羞愧。人类的一万年文明史绝大部分浸泡在丑恶、血腥、无序、私欲膨胀和道德沦丧中。上帝和圣人们的“向善”教诲抵不过众生的“趋恶”本性,好容易建立起来的“治世”只是流沙上的城堡,转眼间就分崩离析。
如果我们能以蚂蚁社会为楷模,人类文明该发展到何等的高度!
——摘自昆虫学家颜夫之的著作《论利他主义的蚂蚁社会》
――1948年发表于英国《理论生物学杂志》
《蚁生》节选之三
恋人幽会时的时间是最快的,我们坐在堰塘堤上,扯着两家的闲话,不知不觉天已晚了。颜哲说:怕是有十点了吧,该回去了,要不又有人说闲话了。我说,好吧,回去吧。颜哲站起来,笑着对我张开双臂。这是我们的老程序,告别前颜哲一定要再和我亲热一次。我投身入怀,享受着他的热吻和拥抱。正在情浓时,忽然听到很近处有一声冷笑!俩人一机灵,立即分开身子,我忙整理好衣服,仔细搜索四周——不,不是幻觉,隔着一株蓖麻,仅一米之外有一个清晰的男人身影。他是何时走近的,我们一点没察觉,我们信赖的蓖麻丛屏障反倒成了对方的掩护。我声音战栗地问:
“谁?”
那边冷冷地回答:“是我,刘学孝。我找颜哲有急事。”
我一下子面庞发烧。我想他一定听到了我们的情话,也看到了我俩刚才的亲热。让刘学孝看到这些,比让其他人看到更令我难堪。我们从小是街坊,而且在年岁渐长时,学孝哥分明是对我有意的,但我那时已经选定了颜哲。以后,我能从学孝哥身上看出他对颜哲的敌意。文革开始时,他第一个对颜伯伯掷出那块致命的石头,对此我不会为他辩解,那是他内心深处兽性的公开显露。自从他显露了兽性的一面后,我和他的关系也非常冷淡了。不过,私下里我也曾猜想,当他决定向颜哲的父亲落井下石时,也许,“情敌”的嫉恨也是因素之一?
不管怎样,既然让他撞见了,我也得去面对。我绕过那株蓖麻,硬着头皮向他走过去,问:
“学孝哥,你找颜哲有事?”仓促中,我说了一句不算得体的话,“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他又是一声冷笑,“你问问全农场的人,哪个不知道这儿是你们幽会的老地方。”
我更加脸红了,原来我们自以为保护得很好的秘密,已经成了农场的公开话题!身后的颜哲用力拉了拉我,虽然没有言语交流,我也能揣摸出他的意思:不用在他面前难为情,恋人有点亲热举动算不上丢人事!然后颜哲平静地问:
“找我啥事?”
刘学孝狠狠地撂了一句:“啥事?对你生死攸关的大事!”
我俩有一点吃惊,但也仅是“有一点”而已。颜哲只是一个普通知青,没杀人放火没写反动标语,怕是不会有什么性命攸关的大事吧。颜哲又拽了拽我,分明是说:别听他放屁!
刘学孝知道我们不会信,冷冷地说:“颜哲,你是不是打算到省里去告赖安胜?”
我们这次真的吃惊了!因为直到目前,这还是只有我们俩才知道的私房话。看来刘学孝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
这事是因孙小小而起。农场共有北阴市和旧城县的六十八名知青,孙小小是年龄最小的,下乡时不足十四岁。按说,这个年纪是不够下乡条件的,但孙小小家门不幸,母亲和姐姐都是县里有名的“破鞋”,据说她上高中的姐在教室里靠墙站着就把那种事办了。他父亲嫌丢人,愤而离家出走,不知所终。后来,旧城县兴起“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热潮。孙小小的母亲和姐姐既然是有名的“破鞋”,自然头一批被撵下乡。孙小小不能一个人留在家里,只好“照顾”到知青农场来。知青们都知道这些根由,因而对孙小小有潜意识的歧视。再加上小小有点缺心眼,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让她成了男知青们经常逗弄的对象。
那天在稻田里拔稗子,知青林镜逗小小:你看你,拔错了,拔的都是秧苗!小小看看手里的稗子,不服气地说:不是,是稗子,秧苗我没拔!
林镜马上接过话头:“你没‘爸’?你‘爸’可多了!”
周围的男知青们哄然大笑,小小还是听不懂,气恼地一遍遍重复:我没拔,就是没拔!她越说,大伙儿越笑。我看不过,托故把孙小小赶走,对林镜说:
“我知道你们看不起小小的家世。但那不是她的错。你们要是这么着一直耍弄她,只会有一个结果:让她走她妈和她姐的老路。你们愿意这样吗?”
林镜刷地红了脸。他其实是个好男孩,平素与我和颜哲很友善。听了我的责备,非常难为情,以后再也不戏弄小小了,反倒经常护着她。小小也凭本能认准了我,就像小狗小猫能认准家里哪个人最亲它一样。她有什么心里话,一点也不瞒我。
前天晚上,我已经睡着了,忽然有人扯我的胳臂,我睁开眼,原来是孙小小。她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不让我说话,然后悄悄拉我出门。我们到了离知青宿舍较远的地方,在这儿说话不会有人听到了。我小声问:
“啥事?把你紧张成这个样子!”
她确实非常紧张,浑身止不住发颤,两眼像高烧病人那样怪异地明亮。我原以为她是让吓的,后来才(非常痛心地)知道,她不光是害怕,更主要是亢奋,而这一幕最终极大地影响了她,让她一生都走歪了。
她说:“赖场长刚从我们屋出来,我就来你这儿了!”
衬着她失常的表情,这句话让我有了误解,莫非那个色鬼场长把小小怎么了?原来不是,事情是这样的:孙小小与岑明霞和宗大兰住一间房,这些天宗大兰回北阴探亲去了,只留下小小和岑明霞两人。一个小时前,小小刚睡下,赖场长进来(天热,知青们睡觉都不关门的),熟门熟路地走向里边岑明霞的那张床,撩开蚊帐坐到床边,两人小声谈话,谈了很久。小小在这边竖起耳朵听,能听出个大概。赖场长说,农场已经来了第一批招工指标,可惜不大满意,县纺纱厂的集体工指标,不是全民工。他说,让不让你走这批指标,我很犯难。走吧,也许以后有更好的地方;不走吧,万一以后的指标还不如这次呢。你说该咋办?岑明霞小声说:我听你的,听哥的安排。那边沉默一会儿,赖场长小声冒出一句:
“⋯⋯也舍不得你。”
后来那边就不说话了,只听见床吱呀吱呀地响着⋯⋯
听着小小绘声绘色的描述,我止不住手足发冷,那是缘于极度的愤怒。说句没道理的话,如果赖安胜把那个贱女人唤到场长室里去办那事,我肯定不会这样愤怒。但他竟公然当着另一个女知青的面!当着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他竟然一点也不害怕别人告发他!
早在知青下乡之前,上边就深知女知青们面临的危险:女知青和他们的男上级,一边是比农村姑娘嫩生风情的城里女学生;一边是握有生杀大权的、又常常处于性饥渴状态的农村男干部。这种双重的不对称会造成什么后果,那是不难想象的。所以,上边制订了保护女知青的强力措施,甚至比保护军婚更严厉。在旧城县就曾发生过轰动全县的一件事:一位女知青到公社邮局去寄信,一个同她相熟的男职员一时发贱,开了一个过头的玩笑,拿手中的剪刀把她的辫梢剪掉一段。这位姑奶奶大怒,立即喊来男知青把那人痛殴一顿,又告到县里。最后那人被判两年徒刑,开除公职,罪名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犯”。
可是在我们农场,那个色鬼竟嚣张到这样程度!我强使自己冷静下来,考虑片刻,劝小小说:
“可不敢告诉别人!这是大事,如果你说出去,又没有真凭实据,赖安胜一定饶不了你。”
小小一个劲儿点头,说:我只对云姐你一个人说,绝不会告诉别人。我于是劝小小回去睡,免得岑明霞发现那件事之后她偷偷溜出来会起疑心。
第二天晚上和颜哲幽会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颜哲顿时勃然大怒,发怒的原因和我一样:不光是因为赖安胜诱奸女知青,更因为他做事之嚣张。颜哲甚至骂了粗话,还愤愤地说:“太不把知青当人了!我明天就去县里去告他,县里告不倒我去省里!”
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已经经过一天的沉淀,所以比他冷静一些。我说:
“我不反对你告,但是得慎重。这种事岑明霞绝不会承认的,孙小小这种见证人也十分靠不住。弄不好赖安胜会反咬一口,说你陷害革命领导干部。”
我的话让他冷静下来。最后我们商定,先不去告,暗地里收集证据,等有把握了再说。这会儿听刘学孝拎出我们的密语,我十分吃惊。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些话我从没告诉过第三者,想来颜哲也不会说。我忽然想到:既然刘学孝今天能悄悄来到我们身边而不被觉察,也许那天他也来了,偷听了我们的谈话,又向赖安胜告发?也许他一直在跟踪我,用阴森的目光,看他心仪的姑娘咋和别的男人亲热?我在心中再次仔细地捋一遍,确信这个推理有八成是对的。这让我止不住心中发颤——不光是因为对这件事的恐惧(原来我和颜哲在这儿亲热时一直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们!),而且是对人性的恐惧。如果刘学孝真的干了这些事(跟梢、偷窥和告密),那这人就太可怕了!
但为什么他又会跑来为我们通风报信?我没来得及继续想下去,因为刘学孝紧接着抛出一个惊人的消息:
“赖安胜已经知道颜哲要告他!他打算做掉颜哲以除去后患。凶手都找好了,是咱场的陈得财和陈秀宽。”
我俩大吃一惊。不过虽然震惊,我们打心眼里不信。赖安胜确实是个坏种,说他干啥坏事我们都信,但这么公然策划杀人未免太离谱。也许这是刘学孝的阴谋,他想挑起颜哲和赖安胜拼命,好从中渔利⋯⋯
刘学孝显然深知我们的思路,断喝一声:“你们以为他不敢!别迂了!你们只用想想,如果奸污知青的事捅出来,他会啥下场,就知道他敢不敢干了!”
我俩一惊,立时悟到刘学孝的话是对的。据传赖安胜已经在场里奸污了三四个女知青,这些如果都坐实,那至少是十年徒刑,如果撞上“严打”,挨枪子也是可能的。“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他为了保住场长的宝座,为了避免坐牢甚至挨枪子的下场,当然会毫无顾忌地铤而走险。我们确实是书呆子,即使在运用智谋策划政治战争时,也不由自主地按“羊”的思路,而不会体悟到“狼”的想法。
而刘学孝显然是深谙“狼”道的。
他看看我俩的表情,知道他的话已经击中十环,便不欲多停,说:“反正我已经尽心了,信不信由你们。颜哲你好自为之吧。”
他就要离开,颜哲问了一句:“刘学孝,我能问问你这样做的动机吗?”
刘学孝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冷冷地说:“赖安胜是个不知死活的驴种,杀人这种事也敢干?早晚会露馅,我才不会陪着他跳火坑。再说,咱们毕竟是老街坊老同学,我不想让你不明不白地送命。”
我和颜哲对视一眼,心照不宣。我根本不信他说的后一个原因。理由很简单:如果他透露的消息是确实的,那他很可能先做了告密者,否则赖安胜不会这么信任他,甚至让他参与(至少是风闻)了杀人预谋。
刘学孝又对颜哲说:“不过,赖安胜的事拿不到真凭实据之前,我不会出头为你做证人的。我把话说前头,到时候你别烦我。”
颜哲说:“对,你不会为我火中取栗的。等我把赖安胜告倒,你就可以安安稳稳做场长了。”
刘学孝没有说话,匆匆离开。
我俩开始认真思索面临的危险,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已经真真切切地悬在头顶了。也许,两个凶手这会儿已经潜伏在四周?我不敢在这儿多停,拉着颜哲,在蓖麻丛的掩护下,悄悄转移到一个新地方。确认周围没人潜伏后,我急迫地说:
“先不管刘学孝是什么动机,我相信他说的消息是真的。咱们不能坐以待毙。颜哲,你继续呆在农场太危险,谁知道姓赖的啥时候下手?防不胜防。我想咱们干脆破釜沉舟,到县里去告他。只要把这件事公开,他就不敢再对你下手了。”
颜哲摇摇头:“你昨天说的话是对的。这泡脓还没熟透,不能硬挤。咱一定得拿到真凭实据。否则,如果刘学孝不认账,孙小小又被吓住哄住,那咱们就输了,反倒落个陷害革命领导干部的罪名。”
“我也考虑到这种可能,那就实行第二个办法:你告病假,回家或到我亲戚家躲几个月。我想赖安胜再厉害,也不过能在农场一手遮天,总不至于把手伸到别的县市吧。等这泡脓熟透、有人出来作证时,你再回来,那时就安全了。”
颜哲摇头,“这样未免太怯弱了。”
“那你说,该咋办?”
颜哲认真思考着,我在月光下紧紧地盯着他的面庞。他的表情忽然有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似乎某个困扰多时的问题忽然得到解决,脸上也绽出轻松的笑容。他说:
“秋云我有办法了,也许这是天赐的机会,让我完成早就想干的一件大事。我有办法了,绝对可靠的办法。至于详情我暂时不能向你透露,你只管放心吧。”
他这番话让我充满狐疑,不禁想起他早先曾说过的:他要用父母留下的一大笔钱办一件“大事”。我原以为,他所说的“大事”是不确指的,只是对今后的一种预期。但从这会儿的意思来看,这件大事是具体的,是早有腹案的。我生气地说:
“你不告我详情,我咋能放心?这是生死大事,你别这么吊儿郎当的!”
颜哲笑了,“秋云你别问,该说的时候,我肯定会第一个告诉你。”
“不行!你至少得告诉我个大概。”
颜哲犹豫片刻,“那我只能告诉你,我要启用我爸留下的一个宝贝,专门对付赖安胜这类坏人的,绝对有效。可惜他没来得及用。”说起父亲,他的情绪有一刹那的黯然。“你放心吧,真的尽管放心,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何况——”他一把搂住我,在我耳边轻笑道,“你还没有为我生儿育女呢,我咋舍得扔下你,一个人先走?”
他的笑声中有发自内心的轻松,让我也变轻松了。我骂他:“不要鼻子座(脸)的东西。这个紧要当口,还惦记着说疯话。”
然后我们回去。他的轻松有效地安抚了我的焦灼——不,他不光是轻松,这个词尚不足以形容他的变化。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只彩色的蝴蝶从原来的蛹壳中破壳而出。他显然下定了决心,今后要为新的目的而活了。
不过我并不知道这个变化的真正原因。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无其他回答
相似回答
大家正在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