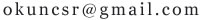《干草车》是英国著名画家约翰·康斯太勃尔田园风景画的代表作。该油画描绘了英国萨福克郡阿尔河畔一个小村庄的优美风景。
《六君子图》写江南秋色, 坡陀上有松、柏、樟、楠、槐、榆六种树木, 疏密掩映, 姿势挺拔。图的上部有远山地抹。全图气象萧疏, 近乎荒凉, 用笔简洁疏放。此图后有黄公望题诗云:"远望云山隔秋水, 近有古木拥披陀, 居然相对六君子, 正直特立无偏颇。"倪瓒生活于元代后期,其时文人绘画的创作理念和纸本山水画的"干笔皴擦"笔墨技法已经完善,而《六君子图》可谓经典之作。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西方绘画中最本原的美学差异:写意与写实。中国绘画偏于精神性的写意,表达了画者对物象的理解及感受,表现物象最本质特征,并进行了理想性塑造加工。其精神性常常高于画本身的表达与技法,物象作为抒情的媒介表达着作者的精神境界与人格追求。而西方绘画则偏于写实性地再现对象,往往表达重于构思,技法展示遮蔽了画家的精神表达,要透过层层物象才能体味画家深藏的内心世界。而且西画常以故事性或场景性代替精神性,在立意上存在缺失。如18世纪评论家狄德罗所说:“在我们的画作中都有着构思上的弱点,思想性的贫乏。”下面将从造型、色彩及构图三个方面进一步阐释中西方绘画在写意与写实上的美学差异。
1 在造型上,中国绘画美学偏于平面性,而西方绘画美学偏于立体性。中国的绘画由工艺装饰(青铜器、陶器纹样)发展而来,本身就具有先天的平面特征。陶器上的纹样多是图案化、美化后的物象,因此中国绘画常具有较强的装饰性意味,也历来不竭力追求再现对象,而是满足于表现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具有意象性造型理念。中国画家不写生,而是通过观察记忆将形象积累于脑海,作画时便全凭记忆,这样既保留了物象的本质特征如种类、规律、结构等等,又主观过滤掉了其非本质的元素如光影、明暗及色彩变化。譬如中国绘画中的树,大致只有几类明显的品种,其枝干变化也常常遵循“树分四枝”的原则,而不像西方绘画中如实描绘树的真实枝干姿态,叶片轮廓。中国绘画中也绝少表现光影,因此给人以强烈的平面感和装饰性,这也养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习惯。这种既非写实又非抽象的画法使中国绘画带有浓郁的写意美,所谓“画意不画形”,画者在似与不似之间创造出了意象与真实物象的距离,表达了作者对于物象的理解与理想。这一点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美学是相同的,意象源于自然又超乎自然,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这也体现了中国绘画的文学性审美特质,古时绘画为“文章余事”, 诗与散文的写意性自然也延续到了绘画中,因此绘画的语言常常是文学性的,精神性的,“画在补文字之缺”。而“印、字、画”一体的模式则成为中国绘画的文学性特质的鲜明外在体现。相比而言,西方绘画有明显的立体性特征,画家们忠于表现物象的素描关系:明暗、透视、体积感、质感、空间感等表面性因素,追求逼真的明暗及色彩变化以及细节的表达。这一方面是出于西方文明中对人和事都要探究清楚的理性及科学精神,一方面继承了古希腊雕塑的审美特征——准确性和完美性的高度统一,因此西方绘画常常注重形体塑造的雕塑感,追求光影下形体的黑白虚实关系产生的美学韵律。
2 在用色上,中西方的差异性则更加明显。西方绘画重用色,色彩与素描一起成为在纸面上创造深度幻觉的两个有力工具。画家以物象的固有色为依据,根据色彩在光影下和环境中色相、纯度、明度的变化精准用色,表现自然化的效果,使人感觉“很像”自然。这种效果明显是具有写实主义色彩的,并且容易将观者引导向对技巧的关注而忽略了物象本身的美。中国绘画则不在个体上作太多颜色变化,更注重整体颜色的协调配合。这与其溯源——装饰艺术中对统一性的要求是分不开的,装饰艺术中讲究重复与统一的韵律,个体若变化太多则会干扰整体的统一性。因此中国绘画中着色常常依循“随类赋色”的原则,即按照物象的种类赋予颜色,不考虑它在光影和环境中的变化。譬如描绘花朵,栀子花皆赋白色,石榴花皆赋朱砂兼胭脂色等等。这种用色方法是写意的,它表达了花卉在画者印象中的颜色,并通过一定的布置使其达到理想的关系,只表现了花最本质的生命特质,没有对其他表象作精确分析。这种用色方法使得大多数中国绘画都给人以淡雅宁静的色彩印象,它超越技巧直达本质,表现了中国文化对自然美的认识与品位。
3 在构图上,西方使用焦点透视,并遵循一定的几何美学规律组织画面。西方绘画画风景时则选定视角后便就视野内的景物作画。这就导致了西方绘画中对透视准确性的追求,无论是平行透视、成角透视、还是倾斜透视曲线透视都要求画家对透视学的绝对把握。文艺复兴时期透视学的发展使得西方绘画写实几乎达到极致。相比之下,中国绘画则呈散点状,移动状,没有一个明确的焦点。这与画家的观察方式是很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