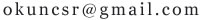有些人真的很奇怪,和你说他的朋友如何哪般不好,待你跟他站在同一阵线,和这个他所谓不好的朋友翻脸后,
有些人真的很奇怪,和你说他的朋友如何哪般不好,待你跟他站在同一阵线,和这个他所谓不好的朋友翻脸后,他倒和他成死党了[捂脸][捂脸][捂脸]
《逾期不候》
《青年文摘》—年第6期
文/野象小姐 逾期不候
A
你是我抢来的。
对,你是我从大眼睛学姐手里抢来的。她比我高一届,也比我高大半个头。头发好长,皮肤白皙到晶莹剔透,无辜的大眼睛最造势,我见犹怜,一推就倒。细胳膊细腿跟你挺合衬。大家都说她很漂亮,那她就漂亮好了。
“她哭了又怎样。”
“关我屁事。”
“就是要跟你在一起呀。”
B
遇见你时我大一快结束,你即将大三。我正沉溺于一个永远不会回头看我一眼的人,敏感又多疑,情绪极易失控。对爱情没有概念,明明一知半解,却自以为是懂得了所有。
那时大家精力充沛,总有一大堆莫须有的理由让认识的不认识的人聚在一块。比如“庆祝XX活动成功”“XX和XX谈恋爱啦!”甚至“植树节快乐”“明天考试”。学校附近的俱乐部、休闲餐厅整天人满为患。那天,我和社团几个人玩杀人游戏,你在隔壁桌喝酒。双方阵营里有人熟识,于是凑成一桌变成一个阵营。本来也没什么特别熟的人,于是我只低头喝自己的小酒。后来大家各玩各的,有人打桌球,有人玩电动,有人看球赛。见没人唱,就借着酒兴抓着话筒唱了范晓萱的《消失》
唱着唱着我就哭了,整屋的人面面相觑。我哭得愈加投入,咳嗽不止,手撑在跟我差不多高的吧台上,站也站不稳。有人来扶我,我挂着眼泪笑出来,“没事没事,我这就回去了。你们好好玩……”没说完,“扑通”一个踉跄直接摔倒在门口。
“跟你说了今晚社团联合会有活动才……我是负责人当然要来了。求你别生气了,好好我回来。”包厢门口传来懊恼的男声,挂线后,转过来一张明显喝高了、但神志清醒的脸。
“陆睿,要回去了?”扶我的人正左右为难,声音惊喜万分。
“唔。”对方大步朝这里走过来。
“正好嘛!只有你和千昭一个校区,你把她送回去吧。”
“千昭?”
“啊,方千昭,你们认识一下。”那人指了指我,“那边在叫我,我先过去啦。”赶紧笑嘻嘻地溜了。我抬头看你,不要脸地朝你傻笑。你茫然地看着正闹的人,又转头看看可怜兮兮的我,礼貌地问:“同学能走吗?”
外“一瓶倒”的我,酒量差,酒品更差。路上一个劲儿地扯着你的袖子神侃。说到动情处破口大骂,偶尔的桥段还一本正经朝你撒娇。你一开始很为难地默不作声,后来不知是被我感染、想着反正路上也没什么人看见,还是你酒劲儿也上来了,总之陪我一起铆着劲儿骂人。
“去!”
“对。去他妈的!”
“我说去!”我一拳结实地擂到你肚子上,“谁准你骂他了!”
通过这次痛快的酒后真言,我知道你和你女朋友问题很大。她时时刻刻都想掌控你,想了解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在做什么。但如果真的把她带去饭局,她又会从头到尾拉着脸坐在那儿,如一尊菩萨般搞坏整场气氛。不喜欢你的朋友圈子,不愿意认识他们,更别提主动融合。
“这是哪门子女朋友,”我痛心疾首地跺足,替你瞎激动着,“狗屎一般!”
“屎!”
“分手!”耿直不阿、气势如虹的女侠胸襟,不如说是瞎起哄的邪恶本质更贴切。
“分手!”
你显然喝得比我多得多,因为快到宿舍楼区时我酒醒得差不多了,你却越来越不像话。指着某栋女生宿舍楼下的垃圾桶说:“信不信我可以跳过去?!”还没等我回答,你就以百米短跑的标准速度冲过去,敏捷地一跃而起,顺利地卡在上面。
我一个激灵完全吓醒,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你费了好大劲儿从上边蹭下来,也不管有多少人围观,傻笑着冲我径直走过来。闭着眼睛拖着你走了两步,你突然蹲在路边不起来。我多想死啊,一边斜着眼瞟着来来往往的路人,一边扯扯你的衣领小声说:“喂,我可把你扔这儿了。反正我不认识你。”
“看,”你欣喜地抬头,“这种虫你认不认识?爬行姿势好怪异!”
想来你也是有头有脸的人,这一闹果然闹出了事。
后来知道,你“斑羚飞渡垃圾桶”的宿舍楼,正是你女朋友那栋。
C
我成了众矢之的的第三者,被推上的风口浪尖。莫名其妙,但又似乎顺理成章的样子。隔了几天,你打来跟我道歉。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原来你很有名。你拿的奖学金是国家级的,申请的课题是学校愿意砸几万块给你建工作室的。你不是哪个哪个社团的蝇头社长,而是海纳百川的社团联合会的会长。在台上讲演或者主持会议时,条理清晰,言简意赅,神态亲切却不容置疑。人际关系经营得非常棒,各种各样的人提到你都赞不绝口。就连我这种挑剔的人精,也闻不出你身上有哪怕一丁点儿学生会干部的装腔作势和侩气息,反而觉得你还挺有品位。可见你把“出世”和“入世”平衡得像个神话。
当然,你出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听老婆的话。女生们都夸你是绝种好男人。
越来越熟以后,除了众所周知的那些台面信息,我还知道你鼻子高,但状况不太好,有轻微的鼻炎。皮肤白皙,从来都目不斜视。所有的鞋清一色的匡威。不敢看恐怖片。喜欢喝玻璃瓶装的芬达,可惜现在都没得。与人交谈时会毫不掩饰地爽朗大笑。认真做事时全神贯注的样子,最迷人。
转眼暑假。
“你在干吗?”“帮妈妈浇花。”
“你在干吗?”“睡完午觉,刚起床。”
“你在干吗?”“喂,你是不是老想我呀。”
没好气的打趣,你却沉默了。
不住频繁地发信息来确认我的生活状态;知道我不开心不会多事地过问,却懂得讲笑话;半夜打知道我马上要停机,催我快点挂,我说停就停呗,你说那我明天怎么你;隔着十万八千里动不动拉我一起守着电视看同一档节目,球赛、陈奕迅专访、专题新闻、综艺节目。
我忽然有种奇怪的情绪。
开学后第一天晚上,你迫不及待地找我出来聊天。
学校教职工区是很规整的旧式居民区。楼全由红砖砌成,黑漆雕花栏杆爬满爬山虎。居民区围起一个废弃的篮球场。篮板被球砸到会晃荡很久,估计螺丝全松动了。水泥的地面极不平整,坑坑洼洼。早就废弃的模样。
坐在球场边的阶梯上,看大妈们排着不整齐的阵型挥舞红色的大扇子,艳丽动人,脸上也是喜气洋洋的笑脸。收音机里播放着《好日子》这样老旧的热闹曲。你坐在我右边,穿着红T恤,篮球在脚边。我们聊着刚过去的暑假。
过了一会儿,大妈们的舞蹈结束,收拾着扇子和收音机,说说笑笑着回家了。几分钟后篮球场的灯熄灭,路灯寂寞地散发着橘色暖光。偌大的篮球场只剩我们两个人。
“我背诗给你听吧。”我抠着你篮球上的凸点。
“噢?”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消失了一般。
你在远方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
“你的沉默就是星星的沉默,遥远而明亮。
“而我会觉得幸福,因为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聂鲁达是不是?”
“嗯。”
“待繁华落尽,年华凋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
“而我们的爱情,则会像北方冬天的枝干……
“勇敢,清晰,坚强。”
“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理科生谁准你知道这么多的,这让我们文科生拿什么体现人生价值?真是的。”
“没,恰好而已。是我喜欢的诗句。”
各自沉默。
“她根本不了解我。”良久,你抬起头说道,“生活也……”
拖沓吗?艰辛吗?彼时我扭头看着你,你的侧脸浸在阴影和暖光调和的景象里,又美好又寂寞。不再是平日光芒万丈的模样,而是温顺得像只小鹿。
“分手咯。”我皱皱眉头。
“她离开我,要崩溃的。”你补充着,“我舍不得。”
我掏出一个橘子,专心地剥了起来。你捞起球,冲去不远处的篮球筐。我依然坐在台阶上,抬起头看你。身着黛青色格纹衬衣,一个人在黑暗的球场上跳跃,影子寂寥。
投篮。带球。断球。三分。上篮。你一反常态的谦和,变得凶猛又激烈。
忽然觉得你很可笑。是应该夸你责任感强呢,还是骂你迂腐不化?当下的两个人,在一起不开心。拖延太久,对彼此都是消耗。必须各自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才能明白此时的优柔寡断是多么残。而所谓的“离开你就会崩溃”,完全是瞎扯淡。任何人都比自己想象的强大,有什么是完全不能承受的呢?
我猛地站起来,把手里没剥完的橘子朝你狠狠砸过去。你肩膀吃痛,气喘吁吁地转过来看我。
“分手吧。跟我过。”我平静地朝篮球中心的你说道。
不由自主地被你吸引,于是蠢蠢欲动。我本是贪玩的人,唯恐天下不乱。除去这些,便是一整套破破烂烂的爱情理论。
是段烂感情,就该扔。
哪里来所谓的道德标准和底线?我想要,我便会伸手。
谁管伤害不伤害。就算我不出现,也会出现其他的人。究其根本是你们自己出了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心里一股暗流,把我推向你,牵引我游向深处。
D
大眼睛学姐哭了。我惹得。
初秋的空气干爽,晴朗清浅。你生病,躺在医务室的床上打点滴。你没有叫你的女朋友而是叫了我。我在很远的
沙发上看电视,慢慢地蹭到你身边蹲下来。你半睁着眼睛,看到我凑过来的大脸吓了一跳。我很懂事地不跟你讲话,
知道你没力气,所以只是看着你。你朝我笑笑,闲出一只手摸摸我的头,又闭起眼睛睡了。
我帮你把输液管调到适中位置,把已经掖好的被子轻轻拍了拍实,把鞋子归顺到床边靠着。搬来小凳子,自己也
打起了盹儿。阳光暖融融的,空气里都是闪耀的金色光斑。时间像只肥猫一样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很慢很慢。
回去之后,听说又被人看见了。我的“小三”形象毫无置疑地屹立于大众心中岿然不倒,除此之外,还有传言说
我已经成功上位了。
又听说,你女朋友终于按捺不住,对你大哭大闹,并且以死相逼。
我听着插着兜,摇头晃脑地路过这些流言。
某天,收到一串陌生码的,“好自为之。”一目了然,我当然知道是谁。
“客气。”面无表情地回复。
“破坏别人感情有意思吗?被人唾骂有意思吗?请你离他远点儿。”
“动不动就用眼泪挽留男人有意思吗?以死相逼的下三滥伎俩有意思吗?不好好活就赶紧死。”
夜里收到你的信息。
“她哭了。”
“哭了又怎样?”
“关我屁事。
”
“就是要跟你在一起呀。”
当时的我多么不懂事,甩狠话都一溜一溜的。自私又霸道。无从体会她的痛苦和绝望,竟然还暗自嫌弃她的不可
理喻——如果生命的全部内容都是关注自己男朋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全部时间用来干涉他的生活,自己的生活怎
么办?完全没有精力去经营啊。为了一个男人,变成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笑柄。有那么多精力瞎折腾,不如多长点本事
守好自己的男人。
怎么没人来扇我两巴掌?
学姐的疯狂,明明都是因为爱。
因为太在乎所以害怕失去,所以干出傻事说出傻话,丧失理智。
F
你何时焦躁和不安,我早就察觉。
你走神,发呆。你一直一直盯着我,却并不是在看我。我知道你的世界除了我,还有无限宽广的领域。你的科研课题、你庞大的人脉、你的社团工作、你的未来。而我根本无法参与,更无从分享,触角伸得再长也触及不了。
我穿着你的黑衬衣跟你睡在一起。袖子很长,必须卷好几道。用脚趾戳你肚子,你大力地扯我入怀。耳朵紧贴你的胸口,是潮汐般规律有力的心跳。你的鼻子蹭着我的头发。
“怎么这么香?”
“啊?”
“柚子味,很清冽呢。”
“没那么梦幻吧。”
“少女体香?”
“超猥琐啊!”
黑暗中感觉到你无声无息地笑,爽朗又干净。
“遇见你像是捡到块宝。”你突然认真地说。说完你就哭了,手揽得更紧。我心中有疑问但我不敢问,只好默不作声。是被老师骂了吗?是课题进展得不顺利吗?是单纯的悲从中来呢还是其他?你不告诉我,你不愿同我分担,因为你觉得讲给我听我也听不懂。
后来,你睡着了,如父兄般轻抚我的背。呼吸沉醉如迷,安稳妥帖。
遇见你像是捡到块宝。这样总结性的陈述句,不是应该出现在故事完结的段落才对吗,陆睿?
世界太阔,你的哭笑不只为我。
G
故事讲到这里,也该完结了。
你前女友回来找你,她曾经是你事业的得力骨干,现在依然可以。撇开那些为了挽留你做的傻事,她是一名能干光鲜的贤内助。她回家修炼一番,改掉了强势控制的恶习,于是你思付再三后放弃了我。
啊。你们守得云开见月明,你们柳暗花明又一村,你们风雨之后见彩虹了。那么我算什么呢?你们漫漫爱情长路上遇见的一个小挫折小考验?我出现的价值就是为了巩固你们的坚贞爱情?
这是一个多狗血的故事,连提及的兴趣都索然。
我需要一个盖。
我要喝很多很多的喜力啤酒,然后用这个盖把我和啤酒盖起来。让心和啤酒泡沫一起,安静地发酵。
分开后不知道第几天,我一个人去街上闲逛。
早上带相机出门,走了很久的路。路上风很大。目睹了两辆摩托车相撞。在某个街角吃到非常美味的灌汤包。了珊瑚石的项链想送给妈妈。拍了一个剪头发只要两块钱的、墙上用油漆写着“传统理发”的店。路边的阿公乐呵呵地坐在长板凳上看我拍照片。在麦当劳看到一个侧脸极像你的人,穿着黑色立领外套。我坐在角落里一直盯着他看,直到他吃好离开。我也离开。
我知道那不可能是你。
“生活到底要怎样,才能取悦自己?”我摁着。走了一会儿,在站台等公车。我重新掏出,把“生活”后面的全删掉。改成:“生活,不就是玩吗?”
发送成功。上车。
竟然不舍得,让你承受我的低落。
是不舒服还是饿了,是热了还是依赖;是缺陷还是理解,是懒惰还是勤劳;是期望还是随便提提?
是生气了还是做姿态,是正轨还是徒劳;是受挫了还是根本不想理会,是多想了还是不过如此。
是爱还是索取,是不敢正名还是无阻挂齿;是真不懂还是虚掩,是不想了还是想不起?
是深到不还是浅就算了,是虚荣还是自尊;是幼稚还是了解人情,是掏心还是一概微笑;是不值还是不愿?
是不是一定要经得起谎言,受得起敷衍,得住欺骗,忘得了诺言,放得下一切,才算成长?
我换了脑子,被你成一个拥有一套正常思维的人。我用它判断世事,处理问题。不再嚣张跋扈,不再横冲直撞,不再不要脸地放狠话。
我多想变得再年轻一点儿,这样我就可以不顾一切地置你于死地。
H
没有啕大哭过,所有人看到风轻云淡的我都以为我没事。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缓慢释放的痛楚无法言说,却又哽住咽喉,无从吞咽。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风天气不敢出门,因为只要刘海儿一吹乱就想你;慢情全不敢听,因为只要心一静下来就会想你;你送的万圣节小恶魔羽毛面具、民族特色的斜挎包、剩半瓶的木糖醇我统统扔进垃圾桶了,因为只要视线落在上面就不住疯狂地想你。
现在我知道,整个经过不是“爱不爱我”的是非判断题,而是ABCD的单选题。
你爱我,但你不要我。你选择跟你生活步调协调的别人。
就这么简单。
爱情这回事,哪里来的缘分使然。你遇见A,便是A;遇见B,便是B了。不要做“等待”这样的傻事,到头来你发现所有人都铆着劲儿往前冲了老远,只有你一个人傻兮兮地被抛在原地。
心动之后便会倦怠,甜蜜之后一定是疲乏。反正爱情,不都那样?
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逾期不候。
隔了许久后梦见你。醒来对着漆黑的天花板发了许久的呆,终于流出眼泪。
夏日午后黏稠的空气,温热暧昧。你间外的小阳台挂着你的黑衬衣,没有风,所以纹丝不动。地板上没了四处散落的电影光碟、、饼干,而是干净又空旷。我与你盘腿对坐,中间是呼呼作响的摇头小电风扇。
你伸手摸我的脸,起身作势吻我。我躲过。沉默横亘在我们之间,巨大而无从跨越。目光疏离,轻轻掠过你的眼、你的眉宇、你的嘴,最后停在海岸线般寂寥的下巴,心里静得出奇。
我说:“有时候我们渴望爱,不是寂寞不是空虚,也不必羞于启齿。
“不是路途遥远没人陪,不是缺少温暖所以渴望拥抱。
“没有那么多冠冕堂皇的漂亮理由,不用粉饰地世间不可多得。”
定定地看着诧异又局促的你。
“需要爱情,只是人的本能而已。没有为什么。”我长叹一口气,轻松许多。风扇嘎吱嘎吱也搅不动黏稠的空气。
你沉了肩膀,坐定后挺了挺脊背。皱着眉头似笑非笑,眼里溢满宠溺的意味。
“我家千昭,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清醒?”
I
清醒是我,糊涂是我,要的不是我。
青年文摘爱好者为你回答。
《青年文摘》—年第6期
文/野象小姐 逾期不候
A
你是我抢来的。
对,你是我从大眼睛学姐手里抢来的。她比我高一届,也比我高大半个头。头发好长,皮肤白皙到晶莹剔透,无辜的大眼睛最造势,我见犹怜,一推就倒。细胳膊细腿跟你挺合衬。大家都说她很漂亮,那她就漂亮好了。
“她哭了又怎样。”
“关我屁事。”
“就是要跟你在一起呀。”
B
遇见你时我大一快结束,你即将大三。我正沉溺于一个永远不会回头看我一眼的人,敏感又多疑,情绪极易失控。对爱情没有概念,明明一知半解,却自以为是懂得了所有。
那时大家精力充沛,总有一大堆莫须有的理由让认识的不认识的人聚在一块。比如“庆祝XX活动成功”“XX和XX谈恋爱啦!”甚至“植树节快乐”“明天考试”。学校附近的俱乐部、休闲餐厅整天人满为患。那天,我和社团几个人玩杀人游戏,你在隔壁桌喝酒。双方阵营里有人熟识,于是凑成一桌变成一个阵营。本来也没什么特别熟的人,于是我只低头喝自己的小酒。后来大家各玩各的,有人打桌球,有人玩电动,有人看球赛。见没人唱,就借着酒兴抓着话筒唱了范晓萱的《消失》
唱着唱着我就哭了,整屋的人面面相觑。我哭得愈加投入,咳嗽不止,手撑在跟我差不多高的吧台上,站也站不稳。有人来扶我,我挂着眼泪笑出来,“没事没事,我这就回去了。你们好好玩……”没说完,“扑通”一个踉跄直接摔倒在门口。
“跟你说了今晚社团联合会有活动才……我是负责人当然要来了。求你别生气了,好好我回来。”包厢门口传来懊恼的男声,挂线后,转过来一张明显喝高了、但神志清醒的脸。
“陆睿,要回去了?”扶我的人正左右为难,声音惊喜万分。
“唔。”对方大步朝这里走过来。
“正好嘛!只有你和千昭一个校区,你把她送回去吧。”
“千昭?”
“啊,方千昭,你们认识一下。”那人指了指我,“那边在叫我,我先过去啦。”赶紧笑嘻嘻地溜了。我抬头看你,不要脸地朝你傻笑。你茫然地看着正闹的人,又转头看看可怜兮兮的我,礼貌地问:“同学能走吗?”
外“一瓶倒”的我,酒量差,酒品更差。路上一个劲儿地扯着你的袖子神侃。说到动情处破口大骂,偶尔的桥段还一本正经朝你撒娇。你一开始很为难地默不作声,后来不知是被我感染、想着反正路上也没什么人看见,还是你酒劲儿也上来了,总之陪我一起铆着劲儿骂人。
“去!”
“对。去他妈的!”
“我说去!”我一拳结实地擂到你肚子上,“谁准你骂他了!”
通过这次痛快的酒后真言,我知道你和你女朋友问题很大。她时时刻刻都想掌控你,想了解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在做什么。但如果真的把她带去饭局,她又会从头到尾拉着脸坐在那儿,如一尊菩萨般搞坏整场气氛。不喜欢你的朋友圈子,不愿意认识他们,更别提主动融合。
“这是哪门子女朋友,”我痛心疾首地跺足,替你瞎激动着,“狗屎一般!”
“屎!”
“分手!”耿直不阿、气势如虹的女侠胸襟,不如说是瞎起哄的邪恶本质更贴切。
“分手!”
你显然喝得比我多得多,因为快到宿舍楼区时我酒醒得差不多了,你却越来越不像话。指着某栋女生宿舍楼下的垃圾桶说:“信不信我可以跳过去?!”还没等我回答,你就以百米短跑的标准速度冲过去,敏捷地一跃而起,顺利地卡在上面。
我一个激灵完全吓醒,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你费了好大劲儿从上边蹭下来,也不管有多少人围观,傻笑着冲我径直走过来。闭着眼睛拖着你走了两步,你突然蹲在路边不起来。我多想死啊,一边斜着眼瞟着来来往往的路人,一边扯扯你的衣领小声说:“喂,我可把你扔这儿了。反正我不认识你。”
“看,”你欣喜地抬头,“这种虫你认不认识?爬行姿势好怪异!”
想来你也是有头有脸的人,这一闹果然闹出了事。
后来知道,你“斑羚飞渡垃圾桶”的宿舍楼,正是你女朋友那栋。
C
我成了众矢之的的第三者,被推上的风口浪尖。莫名其妙,但又似乎顺理成章的样子。隔了几天,你打来跟我道歉。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原来你很有名。你拿的奖学金是国家级的,申请的课题是学校愿意砸几万块给你建工作室的。你不是哪个哪个社团的蝇头社长,而是海纳百川的社团联合会的会长。在台上讲演或者主持会议时,条理清晰,言简意赅,神态亲切却不容置疑。人际关系经营得非常棒,各种各样的人提到你都赞不绝口。就连我这种挑剔的人精,也闻不出你身上有哪怕一丁点儿学生会干部的装腔作势和侩气息,反而觉得你还挺有品位。可见你把“出世”和“入世”平衡得像个神话。
当然,你出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听老婆的话。女生们都夸你是绝种好男人。
越来越熟以后,除了众所周知的那些台面信息,我还知道你鼻子高,但状况不太好,有轻微的鼻炎。皮肤白皙,从来都目不斜视。所有的鞋清一色的匡威。不敢看恐怖片。喜欢喝玻璃瓶装的芬达,可惜现在都没得。与人交谈时会毫不掩饰地爽朗大笑。认真做事时全神贯注的样子,最迷人。
转眼暑假。
“你在干吗?”“帮妈妈浇花。”
“你在干吗?”“睡完午觉,刚起床。”
“你在干吗?”“喂,你是不是老想我呀。”
没好气的打趣,你却沉默了。
不住频繁地发信息来确认我的生活状态;知道我不开心不会多事地过问,却懂得讲笑话;半夜打知道我马上要停机,催我快点挂,我说停就停呗,你说那我明天怎么你;隔着十万八千里动不动拉我一起守着电视看同一档节目,球赛、陈奕迅专访、专题新闻、综艺节目。
我忽然有种奇怪的情绪。
开学后第一天晚上,你迫不及待地找我出来聊天。
学校教职工区是很规整的旧式居民区。楼全由红砖砌成,黑漆雕花栏杆爬满爬山虎。居民区围起一个废弃的篮球场。篮板被球砸到会晃荡很久,估计螺丝全松动了。水泥的地面极不平整,坑坑洼洼。早就废弃的模样。
坐在球场边的阶梯上,看大妈们排着不整齐的阵型挥舞红色的大扇子,艳丽动人,脸上也是喜气洋洋的笑脸。收音机里播放着《好日子》这样老旧的热闹曲。你坐在我右边,穿着红T恤,篮球在脚边。我们聊着刚过去的暑假。
过了一会儿,大妈们的舞蹈结束,收拾着扇子和收音机,说说笑笑着回家了。几分钟后篮球场的灯熄灭,路灯寂寞地散发着橘色暖光。偌大的篮球场只剩我们两个人。
“我背诗给你听吧。”我抠着你篮球上的凸点。
“噢?”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消失了一般。
你在远方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
“你的沉默就是星星的沉默,遥远而明亮。
“而我会觉得幸福,因为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聂鲁达是不是?”
“嗯。”
“待繁华落尽,年华凋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
“而我们的爱情,则会像北方冬天的枝干……
“勇敢,清晰,坚强。”
“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理科生谁准你知道这么多的,这让我们文科生拿什么体现人生价值?真是的。”
“没,恰好而已。是我喜欢的诗句。”
各自沉默。
“她根本不了解我。”良久,你抬起头说道,“生活也……”
拖沓吗?艰辛吗?彼时我扭头看着你,你的侧脸浸在阴影和暖光调和的景象里,又美好又寂寞。不再是平日光芒万丈的模样,而是温顺得像只小鹿。
“分手咯。”我皱皱眉头。
“她离开我,要崩溃的。”你补充着,“我舍不得。”
我掏出一个橘子,专心地剥了起来。你捞起球,冲去不远处的篮球筐。我依然坐在台阶上,抬起头看你。身着黛青色格纹衬衣,一个人在黑暗的球场上跳跃,影子寂寥。
投篮。带球。断球。三分。上篮。你一反常态的谦和,变得凶猛又激烈。
忽然觉得你很可笑。是应该夸你责任感强呢,还是骂你迂腐不化?当下的两个人,在一起不开心。拖延太久,对彼此都是消耗。必须各自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才能明白此时的优柔寡断是多么残。而所谓的“离开你就会崩溃”,完全是瞎扯淡。任何人都比自己想象的强大,有什么是完全不能承受的呢?
我猛地站起来,把手里没剥完的橘子朝你狠狠砸过去。你肩膀吃痛,气喘吁吁地转过来看我。
“分手吧。跟我过。”我平静地朝篮球中心的你说道。
不由自主地被你吸引,于是蠢蠢欲动。我本是贪玩的人,唯恐天下不乱。除去这些,便是一整套破破烂烂的爱情理论。
是段烂感情,就该扔。
哪里来所谓的道德标准和底线?我想要,我便会伸手。
谁管伤害不伤害。就算我不出现,也会出现其他的人。究其根本是你们自己出了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心里一股暗流,把我推向你,牵引我游向深处。
D
大眼睛学姐哭了。我惹得。
初秋的空气干爽,晴朗清浅。你生病,躺在医务室的床上打点滴。你没有叫你的女朋友而是叫了我。我在很远的
沙发上看电视,慢慢地蹭到你身边蹲下来。你半睁着眼睛,看到我凑过来的大脸吓了一跳。我很懂事地不跟你讲话,
知道你没力气,所以只是看着你。你朝我笑笑,闲出一只手摸摸我的头,又闭起眼睛睡了。
我帮你把输液管调到适中位置,把已经掖好的被子轻轻拍了拍实,把鞋子归顺到床边靠着。搬来小凳子,自己也
打起了盹儿。阳光暖融融的,空气里都是闪耀的金色光斑。时间像只肥猫一样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很慢很慢。
回去之后,听说又被人看见了。我的“小三”形象毫无置疑地屹立于大众心中岿然不倒,除此之外,还有传言说
我已经成功上位了。
又听说,你女朋友终于按捺不住,对你大哭大闹,并且以死相逼。
我听着插着兜,摇头晃脑地路过这些流言。
某天,收到一串陌生码的,“好自为之。”一目了然,我当然知道是谁。
“客气。”面无表情地回复。
“破坏别人感情有意思吗?被人唾骂有意思吗?请你离他远点儿。”
“动不动就用眼泪挽留男人有意思吗?以死相逼的下三滥伎俩有意思吗?不好好活就赶紧死。”
夜里收到你的信息。
“她哭了。”
“哭了又怎样?”
“关我屁事。
”
“就是要跟你在一起呀。”
当时的我多么不懂事,甩狠话都一溜一溜的。自私又霸道。无从体会她的痛苦和绝望,竟然还暗自嫌弃她的不可
理喻——如果生命的全部内容都是关注自己男朋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全部时间用来干涉他的生活,自己的生活怎
么办?完全没有精力去经营啊。为了一个男人,变成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笑柄。有那么多精力瞎折腾,不如多长点本事
守好自己的男人。
怎么没人来扇我两巴掌?
学姐的疯狂,明明都是因为爱。
因为太在乎所以害怕失去,所以干出傻事说出傻话,丧失理智。
F
你何时焦躁和不安,我早就察觉。
你走神,发呆。你一直一直盯着我,却并不是在看我。我知道你的世界除了我,还有无限宽广的领域。你的科研课题、你庞大的人脉、你的社团工作、你的未来。而我根本无法参与,更无从分享,触角伸得再长也触及不了。
我穿着你的黑衬衣跟你睡在一起。袖子很长,必须卷好几道。用脚趾戳你肚子,你大力地扯我入怀。耳朵紧贴你的胸口,是潮汐般规律有力的心跳。你的鼻子蹭着我的头发。
“怎么这么香?”
“啊?”
“柚子味,很清冽呢。”
“没那么梦幻吧。”
“少女体香?”
“超猥琐啊!”
黑暗中感觉到你无声无息地笑,爽朗又干净。
“遇见你像是捡到块宝。”你突然认真地说。说完你就哭了,手揽得更紧。我心中有疑问但我不敢问,只好默不作声。是被老师骂了吗?是课题进展得不顺利吗?是单纯的悲从中来呢还是其他?你不告诉我,你不愿同我分担,因为你觉得讲给我听我也听不懂。
后来,你睡着了,如父兄般轻抚我的背。呼吸沉醉如迷,安稳妥帖。
遇见你像是捡到块宝。这样总结性的陈述句,不是应该出现在故事完结的段落才对吗,陆睿?
世界太阔,你的哭笑不只为我。
G
故事讲到这里,也该完结了。
你前女友回来找你,她曾经是你事业的得力骨干,现在依然可以。撇开那些为了挽留你做的傻事,她是一名能干光鲜的贤内助。她回家修炼一番,改掉了强势控制的恶习,于是你思付再三后放弃了我。
啊。你们守得云开见月明,你们柳暗花明又一村,你们风雨之后见彩虹了。那么我算什么呢?你们漫漫爱情长路上遇见的一个小挫折小考验?我出现的价值就是为了巩固你们的坚贞爱情?
这是一个多狗血的故事,连提及的兴趣都索然。
我需要一个盖。
我要喝很多很多的喜力啤酒,然后用这个盖把我和啤酒盖起来。让心和啤酒泡沫一起,安静地发酵。
分开后不知道第几天,我一个人去街上闲逛。
早上带相机出门,走了很久的路。路上风很大。目睹了两辆摩托车相撞。在某个街角吃到非常美味的灌汤包。了珊瑚石的项链想送给妈妈。拍了一个剪头发只要两块钱的、墙上用油漆写着“传统理发”的店。路边的阿公乐呵呵地坐在长板凳上看我拍照片。在麦当劳看到一个侧脸极像你的人,穿着黑色立领外套。我坐在角落里一直盯着他看,直到他吃好离开。我也离开。
我知道那不可能是你。
“生活到底要怎样,才能取悦自己?”我摁着。走了一会儿,在站台等公车。我重新掏出,把“生活”后面的全删掉。改成:“生活,不就是玩吗?”
发送成功。上车。
竟然不舍得,让你承受我的低落。
是不舒服还是饿了,是热了还是依赖;是缺陷还是理解,是懒惰还是勤劳;是期望还是随便提提?
是生气了还是做姿态,是正轨还是徒劳;是受挫了还是根本不想理会,是多想了还是不过如此。
是爱还是索取,是不敢正名还是无阻挂齿;是真不懂还是虚掩,是不想了还是想不起?
是深到不还是浅就算了,是虚荣还是自尊;是幼稚还是了解人情,是掏心还是一概微笑;是不值还是不愿?
是不是一定要经得起谎言,受得起敷衍,得住欺骗,忘得了诺言,放得下一切,才算成长?
我换了脑子,被你成一个拥有一套正常思维的人。我用它判断世事,处理问题。不再嚣张跋扈,不再横冲直撞,不再不要脸地放狠话。
我多想变得再年轻一点儿,这样我就可以不顾一切地置你于死地。
H
没有啕大哭过,所有人看到风轻云淡的我都以为我没事。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缓慢释放的痛楚无法言说,却又哽住咽喉,无从吞咽。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风天气不敢出门,因为只要刘海儿一吹乱就想你;慢情全不敢听,因为只要心一静下来就会想你;你送的万圣节小恶魔羽毛面具、民族特色的斜挎包、剩半瓶的木糖醇我统统扔进垃圾桶了,因为只要视线落在上面就不住疯狂地想你。
现在我知道,整个经过不是“爱不爱我”的是非判断题,而是ABCD的单选题。
你爱我,但你不要我。你选择跟你生活步调协调的别人。
就这么简单。
爱情这回事,哪里来的缘分使然。你遇见A,便是A;遇见B,便是B了。不要做“等待”这样的傻事,到头来你发现所有人都铆着劲儿往前冲了老远,只有你一个人傻兮兮地被抛在原地。
心动之后便会倦怠,甜蜜之后一定是疲乏。反正爱情,不都那样?
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逾期不候。
隔了许久后梦见你。醒来对着漆黑的天花板发了许久的呆,终于流出眼泪。
夏日午后黏稠的空气,温热暧昧。你间外的小阳台挂着你的黑衬衣,没有风,所以纹丝不动。地板上没了四处散落的电影光碟、、饼干,而是干净又空旷。我与你盘腿对坐,中间是呼呼作响的摇头小电风扇。
你伸手摸我的脸,起身作势吻我。我躲过。沉默横亘在我们之间,巨大而无从跨越。目光疏离,轻轻掠过你的眼、你的眉宇、你的嘴,最后停在海岸线般寂寥的下巴,心里静得出奇。
我说:“有时候我们渴望爱,不是寂寞不是空虚,也不必羞于启齿。
“不是路途遥远没人陪,不是缺少温暖所以渴望拥抱。
“没有那么多冠冕堂皇的漂亮理由,不用粉饰地世间不可多得。”
定定地看着诧异又局促的你。
“需要爱情,只是人的本能而已。没有为什么。”我长叹一口气,轻松许多。风扇嘎吱嘎吱也搅不动黏稠的空气。
你沉了肩膀,坐定后挺了挺脊背。皱着眉头似笑非笑,眼里溢满宠溺的意味。
“我家千昭,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清醒?”
I
清醒是我,糊涂是我,要的不是我。
青年文摘爱好者为你回答。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无其他回答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