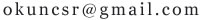童年的梦,七彩的梦;童年的歌,欢乐的歌;童年的脚印一串串;童年的故事一摞摞。”这首歌是否能让你回想起美好的童年生活?在那五彩缤纷的岁月中,发生过许多事情,不像星星一样的明亮。我的童年是美好的,有许多事值得回忆……
从我记事起,大姨的班上就养了两只小鸡,一有时间我就去大姨班上看小鸡,不知过了多久,两只小鸡渐渐长大了,又过了许久,母鸡下蛋了,蛋中要孵出小鸡了,21天后,闻声可听一阵小鸡的叫声,看到这情况,听到这声音。我觉得小鸡太可怜了,在母鸡和公鸡都不在家时,帮一下小鸡。机会,终于来了……
那天,母鸡给小小鸡找食去了,淘气的公鸡也不在家,跑出去玩了。趁大姨不注意顺手拿起一个鸡蛋,捧在手心里轻轻抚摸着,一本正经地说:“小鸡不要害怕,一会你就会来到世界上了。”说完,我不再犹豫了,剥开了一个鸡蛋,一只带有余热,未睁开眼睛的小鸡“诞生”了,它看了看我,叫了两声好像在说:“谢谢你,让我早日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可高兴了,又剥开了第二个,当我剥到第四个的时候母鸡回来了,看见我正在“欺负”蛇的小宝宝就猛琢了我一口,顿时鲜血流了出来,我哭哭啼啼地去找大姨,大姨并没说我,反而哭笑不得地说:“小傻瓜,鸡要到一定时候才会出生呢!你这样给它们接生,会死的。”我听完,赶忙跑看小鸡,果然刚刚被我“接生”的小鸡都快死了,而没被我“接生”的都活了下来。我后悔极了,但一切都晚了……
虽然这件事过去很久了,虽然那里我还年幼无知,但这件事一直鞭策着我,让我勇往直前,永不后退。
童年,是欢乐的海洋。在回忆的海边,有无数的贝壳,有灰暗的,勾起一段伤心的往事;有灿烂的,使人想起童年趣事。我在那回忆的海岸,寻觅着最美丽的贝壳,啊,找到了……
那时,我才六岁,是对过生日情有独钟的年龄。我喜欢过生日,因为我会吃到大蛋糕,而那次,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忙碌了一上午的我,终于可以吃到盼望以久的蛋糕啦!瞧,那蛋糕又大又圆,被纯白的奶油覆盖着,上面堆满了各种奶油花儿,好像在对我笑着,可爱极了!蛋糕上还用红果酱写的“生日快乐”。再烛光的映衬下,蛋糕真令我垂涎三尺啊!我迫不及待的想吃掉它。
终于到手啦!一大块蛋糕被我拿在手中。我咬了一大口,啊,真是美味啊!姐姐突然笑了,这笑让我莫名其妙,一照镜子,呵,我把一块奶油蹭在了鼻子上,活像一个小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姐姐不爱吃奶油,正想着怎么办,忽然看见我鼻子上的奶油,眼睛猛一亮,笑眯眯地说“妹妹,过来!”我想都没想,大步跨了过去。姐姐让我坐下,只见她端来一个盘子,里面有我爱吃的奶油,我以为她要给我吃,赶快张大了嘴。“啪”,一块凉凉的东西贴在了我的脑门上,接着是脸,下巴,我知道是奶油,便伸长了舌头去舔,却听见了一阵大笑。去镜子前一看,哈!镜子里出现了一只小花猫!满脸的奶油,东一块,西一块。我的脸被这种“高级”化妆品涂的好似京剧脸谱一般。不,京剧脸谱的颜色没这么单一,纯白的奶油在镜子里好像小花猫的毛,我舔奶油,何不像一只馋猫!我也笑了,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摇身一变,竟变成了一只馋嘴的小花猫!
童年趣事,件件都像一枚五彩的贝壳,这些五彩的贝壳,托起了我五彩的童年!
小时侯的我特别的调皮捣蛋,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我童年的一件趣事。
记得有一次回家,我看到爸爸正躺在床上睡觉,于是我的小脑袋里便突然冒出了一个“坏”念头,就是画“脸谱”,当然不是在纸上画,而是-----在爸爸的脸上画,我先找出颜料、笔和水,随后我在爸爸的额上小心翼翼的画上了一个大大的“王”字,再用土黄色在爸爸脸的四周画上一堆金灿灿的斑纹,这样就是一只威风十足的老虎了,画完之后我一边为自己的“杰作”感到高兴也一边为爸爸的脸被我画成这样感到惋惜,因为爸爸那张漂亮的脸被我画成这样真是可惜。正在我高兴的看着自己的“杰作”的时候,突然爸爸醒了过来,看着他一脸茫然的样子,我哈哈大笑起来,爸爸莫名其妙的看看我,当他看到满地的水彩颜料和水,看着我那不怀好意的笑,爸爸连忙跑到卫生间去照镜子,当他发现自己的脸上已经被我画成一道一道的时候,他也顾不得脸上有水彩颜料,就飞快的跑进屋,抓起我就是一顿乱打,打的我是咕呱乱叫,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我仍记忆犹心。
你看!我小时侯多调皮呀!直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趣呢!
每个人的童年中都有许许多多有趣的事,我当然也不例外,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在我童年中一件有趣的事情吧。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在姥姥家玩,姥姥家住农村,她养了很多鸡。 有一天,姥姥、舅舅、姥爷出去玩把我一个人扔在家,我很生气,心想,他们怎么这样,出去也不带我。在屋里闲着没事干,便想去鸡舍中,看看那些鸡在干什么。 我刚进去,只听“砰”的一声,一只母鸡生了一个蛋。真好玩,我好奇的摸了摸蛋,咦,热热的,湿湿的。这是,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心想,鸡会生蛋,那鸡舍中所有的鸡一定都会生了,要不掏鸡蛋吧,姥姥回来看到这么多的蛋,还不夸奖我,没准还奖励我呢,对掏鸡蛋!想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一只鸡就掏,那只鸡好像知道自己命运似的,使劲拍着翅膀,想要逃,我呢,死抓着鸡爪不放,看是它厉害还是我厉害,掏了半天没掏出来,怎么回事,怎么掏不出来,难到我的奖励没了吗?我偏不信,这只掏不出来在掏另一只吧,我随手把鸡一扔,又去抓别的鸡,那些鸡看见我走来,一个个上窜下跳,好像老鼠见到猫一样,拔腿就跑,我呢,就不放手,一个劲去抓鸡,这不,还没半个小时我就快变成鸡毛人了。好不容易才抓到一只鸡,我上手就掏,掏的那只鸡“嗷嗷”直叫,又没掏出来,再抓一只……掏的这只鸡直吐白沫,我又……姥姥她们回来了,看见我的狼狈样,不禁哈哈大笑,问清原因,姥姥不仅没夸奖我,还训了我一顿,后来,我才知道除了鸡舍中的那只母鸡外,剩下的全都是公鸡。
这就是我童年中一件有趣的事,它不仅好玩,还时时告戒我:偷鸡不成拾把米,千万不要好心办坏事。
童年是七色的,是热情的,可爱的。童年是这么的美好,那童年趣事又是这样的呢?
我是一个北方的女孩,小时侯的我喜欢在冰天雪地里玩,打雪仗、堆雪人。每当冬天到来时,鹅毛般地大雪从空中飘落下来,一朵朵、一簇簇,像银花,似白蝶。展望天地之间,唯见雪花飘扬,像吹落地花瓣,纷纷扬扬;像七仙女散花,漫天飞舞。人站立在雪中,就像蹲在轧花机上,只看见无数的棉絮花拂向你,给你罩了一身洁白的素花。
早上起来,风定了,雪停了。打开门,一道白色的寒光刺得人眼花缭乱。于是,我和弟弟、表哥拿起铲子就在院子里堆起了雪人,洁白的身子,圆圆的头,煤球做黑眼睛,棉花捏成的鼻子,还向上翘着呢!表哥又用红墨水给雪人涂了嘴巴,一咧一咧,正朝着我们哈哈大笑呢!弟弟用一张红色的纸给雪人做了一顶漂亮的帽子。雪人一下变得神气多了!雪人堆成了,又迎来一场大仗,表哥掷好一个雪球趁我不注意向我发起进攻,还好没大中。当我反击表哥时,他已经被弟弟的雪球打中了,雪球在表哥的头顶上开了画,这时院子里充满了欢笑声。表哥不服气,拿起雪球向弟弟攻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攻击院子里的笑声就更大了。
童年是多么的有趣呀!童年趣事给我带来了欢乐,童年真好。
童年趣事
童年是五彩缤纷的,就像海边漂亮的贝壳;童年是无忧无虑的,就像整天嘻闹的浪娃娃;童年是纯真甜美的,就像山溪中清亮的泉水。说起童年,倒不禁使我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
记得那是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奶奶给我和菊菊每人一粒使人一见就流口水的高级奶糖,这可把我们两只“小馋猫”给乐坏了,真是心花怒放。
我们俩谁也舍不得吃。我说:“咱们吃了好吗?”“好,一起吃!”菊菊答应了。我手脚快,一下两下就拆开了,我拿出糖,伸长脖子去看菊菊的。我一看她的糖,急了:
“你的比我的大!”
“哪里?我的这里缺一点!”
“哼,我的溶掉了!”
“你的颜色浓,牛奶多!”
“……”
我们争来争去没有结果,都觉得自己吃亏。可一说要调换,就连忙转过身,谁也不愿意。我们开始吃糖了,“1、2、3!”我们一起吃了下去。哇!真甜,真鲜,真香!吃了一会儿,我说:“拿出来看看,你大还是我大!”“好!”菊菊说着像只哈巴狗一样把糖顶在舌尖上伸出来。我一看也同她那样伸出舌头,可她说看不清楚,我只好把糖放在舌尖上,半粒在外面,并竭力把舌头向外伸。这时,正好一只小狗钻到我脚下,我躲闪不及,舌尖上的糖一不小心掉在了地上,真是无巧不成书,我整个人向前一冲,右脚正好对着那粒糖,唉呀,怎么办?说时迟,那时快,我还没来得及回过神来,脚已经踩在“宝贝”上了。我真是又急又气:“你这只臭狗、烂狗、死狗!”我对准狗肚子就是一脚,狗吓得连忙逃走了。我抬起脚,用手掰掉粘在鞋底上的糖,左瞧右瞧,舍不得扔掉。“扔掉呀,难道你还想吃吗?”菊菊讽刺我说。我两只粘满糖的手不由自主地搓着,两只眼睛盯着菊菊的嘴巴,就是让我看一看奶糖也好。我不断地咽着口水,恨不得她把糖吐出来,咬半粒给我吃。我再也看不下去了,只觉得鼻子一酸,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下来:“妈妈,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现在,时光老人已经来临,把童年匆匆带走了。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为了一粒糖而斤斤计较,更不会大哭一场。感谢时光老人,因为他把童年编成一本最纯最真最美的书印在我们的心坎里。■
回答者:w553604923 - 初学弟子 一级 11-25 17:30
这是我从网上找的‘童年趣事’你参考下
童年是快乐的,童年是美好的。我的童年就非常快乐。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阳光明媚,正好下楼去玩。我把我的那几个好朋友一朱昱、胡晓、蔡李宁洁聚集在一起。我做了个打枪的姿势,他们点了点头,一致同意玩“反恐”。我们分别扮成两个“小偷”,两个“警察”,枪就用小木棍代替。
第—盘,我先当严“小偷”。要先跑,我和我的同伴胡晓跑到一个门栋里躲着,等待着“敌人”的到来;可是等了半天,也没有人影;我悄悄对胡晓说:“这样等没完没了,我出去侦察一下,你在这里不要离开”。说完,我贼溜溜地沿着墙壁走,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仔细察看一番,生怕露出一点“狐狸尾巴”。当我来到一栋楼的拐角处,突然一个轻轻的步子向我走来,我急了,怕“警察”跳出来把我“击毙”。我四处张望,想找到一线生机溜走,可是已来不及了。“警察”朱昱箭步冲到我面前对我“咚、咚—….”猛“开枪”。等我再回到那个门栋找到胡晓时,他垂头丧气地对我说;“你刚一走,,蔡李宁洁就冲进来把我干掉了”。原来“警察”一直盯者我们的动向,等我走了,就采用偷袭战术。
第二盘,我们互换角色。,我和胡晓紧握双手,发誓一定要把“小偷”抓获归案。我们看见他们躲好了,开始了战斗。正当我们胜利在望时,“洛洛,快回家吃饭!”,听到妈妈在大声呼唤。大家都停住了战斗的脚步,我无奈地跑回家。不知他们此时心情怎样,我心里可是仍然想着,这次战斗我们必胜。
怎样?我的童年快乐吧
(女孩子也可以玩的!绝对真实!!!!!)
“童年的梦,七彩的梦;童年的歌,欢乐的歌;童年的脚印一串串;童年的故事一摞摞。”这首歌是否能让你回想起美好的童年生活?在那五彩缤纷的岁月中,发生过许多事情,不像星星一样的明亮。我的童年是美好的,有许多事值得回忆……
从我记事起,大姨的班上就养了两只小鸡,一有时间我就去大姨班上看小鸡,不知过了多久,两只小鸡渐渐长大了,又过了许久,母鸡下蛋了,蛋中要孵出小鸡了,21天后,闻声可听一阵小鸡的叫声,看到这情况,听到这声音。我觉得小鸡太可怜了,在母鸡和公鸡都不在家时,帮一下小鸡。机会,终于来了……
那天,母鸡给小小鸡找食去了,淘气的公鸡也不在家,跑出去玩了。趁大姨不注意顺手拿起一个鸡蛋,捧在手心里轻轻抚摸着,一本正经地说:“小鸡不要害怕,一会你就会来到世界上了。”说完,我不再犹豫了,剥开了一个鸡蛋,一只带有余热,未睁开眼睛的小鸡“诞生”了,它看了看我,叫了两声好像在说:“谢谢你,让我早日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可高兴了,又剥开了第二个,当我剥到第四个的时候母鸡回来了,看见我正在“欺负”蛇的小宝宝就猛琢了我一口,顿时鲜血流了出来,我哭哭啼啼地去找大姨,大姨并没说我,反而哭笑不得地说:“小傻瓜,鸡要到一定时候才会出生呢!你这样给它们接生,会死的。”我听完,赶忙跑看小鸡,果然刚刚被我“接生”的小鸡都快死了,而没被我“接生”的都活了下来。我后悔极了,但一切都晚了……
虽然这件事过去很久了,虽然那里我还年幼无知,但这件事一直鞭策着我,让我勇往直前,永不后退。
童年,是欢乐的海洋。在回忆的海边,有无数的贝壳,有灰暗的,勾起一段伤心的往事;有灿烂的,使人想起童年趣事。我在那回忆的海岸,寻觅着最美丽的贝壳,啊,找到了……
那时,我才六岁,是对过生日情有独钟的年龄。我喜欢过生日,因为我会吃到大蛋糕,而那次,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忙碌了一上午的我,终于可以吃到盼望以久的蛋糕啦!瞧,那蛋糕又大又圆,被纯白的奶油覆盖着,上面堆满了各种奶油花儿,好像在对我笑着,可爱极了!蛋糕上还用红果酱写的“生日快乐”。再烛光的映衬下,蛋糕真令我垂涎三尺啊!我迫不及待的想吃掉它。
终于到手啦!一大块蛋糕被我拿在手中。我咬了一大口,啊,真是美味啊!姐姐突然笑了,这笑让我莫名其妙,一照镜子,呵,我把一块奶油蹭在了鼻子上,活像一个小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姐姐不爱吃奶油,正想着怎么办,忽然看见我鼻子上的奶油,眼睛猛一亮,笑眯眯地说“妹妹,过来!”我想都没想,大步跨了过去。姐姐让我坐下,只见她端来一个盘子,里面有我爱吃的奶油,我以为她要给我吃,赶快张大了嘴。“啪”,一块凉凉的东西贴在了我的脑门上,接着是脸,下巴,我知道是奶油,便伸长了舌头去舔,却听见了一阵大笑。去镜子前一看,哈!镜子里出现了一只小花猫!满脸的奶油,东一块,西一块。我的脸被这种“高级”化妆品涂的好似京剧脸谱一般。不,京剧脸谱的颜色没这么单一,纯白的奶油在镜子里好像小花猫的毛,我舔奶油,何不像一只馋猫!我也笑了,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摇身一变,竟变成了一只馋嘴的小花猫!
童年趣事,件件都像一枚五彩的贝壳,这些五彩的贝壳,托起了我五彩的童年!
小时侯的我特别的调皮捣蛋,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我童年的一件趣事。
记得有一次回家,我看到爸爸正躺在床上睡觉,于是我的小脑袋里便突然冒出了一个“坏”念头,就是画“脸谱”,当然不是在纸上画,而是-----在爸爸的脸上画,我先找出颜料、笔和水,随后我在爸爸的额上小心翼翼的画上了一个大大的“王”字,再用土黄色在爸爸脸的四周画上一堆金灿灿的斑纹,这样就是一只威风十足的老虎了,画完之后我一边为自己的“杰作”感到高兴也一边为爸爸的脸被我画成这样感到惋惜,因为爸爸那张漂亮的脸被我画成这样真是可惜。正在我高兴的看着自己的“杰作”的时候,突然爸爸醒了过来,看着他一脸茫然的样子,我哈哈大笑起来,爸爸莫名其妙的看看我,当他看到满地的水彩颜料和水,看着我那不怀好意的笑,爸爸连忙跑到卫生间去照镜子,当他发现自己的脸上已经被我画成一道一道的时候,他也顾不得脸上有水彩颜料,就飞快的跑进屋,抓起我就是一顿乱打,打的我是咕呱乱叫,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我仍记忆犹心。
你看!我小时侯多调皮呀!直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趣呢!
每个人的童年中都有许许多多有趣的事,我当然也不例外,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在我童年中一件有趣的事情吧。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在姥姥家玩,姥姥家住农村,她养了很多鸡。 有一天,姥姥、舅舅、姥爷出去玩把我一个人扔在家,我很生气,心想,他们怎么这样,出去也不带我。在屋里闲着没事干,便想去鸡舍中,看看那些鸡在干什么。 我刚进去,只听“砰”的一声,一只母鸡生了一个蛋。真好玩,我好奇的摸了摸蛋,咦,热热的,湿湿的。这是,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心想,鸡会生蛋,那鸡舍中所有的鸡一定都会生了,要不掏鸡蛋吧,姥姥回来看到这么多的蛋,还不夸奖我,没准还奖励我呢,对掏鸡蛋!想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一只鸡就掏,那只鸡好像知道自己命运似的,使劲拍着翅膀,想要逃,我呢,死抓着鸡爪不放,看是它厉害还是我厉害,掏了半天没掏出来,怎么回事,怎么掏不出来,难到我的奖励没了吗?我偏不信,这只掏不出来在掏另一只吧,我随手把鸡一扔,又去抓别的鸡,那些鸡看见我走来,一个个上窜下跳,好像老鼠见到猫一样,拔腿就跑,我呢,就不放手,一个劲去抓鸡,这不,还没半个小时我就快变成鸡毛人了。好不容易才抓到一只鸡,我上手就掏,掏的那只鸡“嗷嗷”直叫,又没掏出来,再抓一只……掏的这只鸡直吐白沫,我又……姥姥她们回来了,看见我的狼狈样,不禁哈哈大笑,问清原因,姥姥不仅没夸奖我,还训了我一顿,后来,我才知道除了鸡舍中的那只母鸡外,剩下的全都是公鸡。
这就是我童年中一件有趣的事,它不仅好玩,还时时告戒我:偷鸡不成拾把米,千万不要好心办坏事。
童年是七色的,是热情的,可爱的。童年是这么的美好,那童年趣事又是这样的呢?
我是一个北方的女孩,小时侯的我喜欢在冰天雪地里玩,打雪仗、堆雪人。每当冬天到来时,鹅毛般地大雪从空中飘落下来,一朵朵、一簇簇,像银花,似白蝶。展望天地之间,唯见雪花飘扬,像吹落地花瓣,纷纷扬扬;像七仙女散花,漫天飞舞。人站立在雪中,就像蹲在轧花机上,只看见无数的棉絮花拂向你,给你罩了一身洁白的素花。
早上起来,风定了,雪停了。打开门,一道白色的寒光刺得人眼花缭乱。于是,我和弟弟、表哥拿起铲子就在院子里堆起了雪人,洁白的身子,圆圆的头,煤球做黑眼睛,棉花捏成的鼻子,还向上翘着呢!表哥又用红墨水给雪人涂了嘴巴,一咧一咧,正朝着我们哈哈大笑呢!弟弟用一张红色的纸给雪人做了一顶漂亮的帽子。雪人一下变得神气多了!雪人堆成了,又迎来一场大仗,表哥掷好一个雪球趁我不注意向我发起进攻,还好没大中。当我反击表哥时,他已经被弟弟的雪球打中了,雪球在表哥的头顶上开了画,这时院子里充满了欢笑声。表哥不服气,拿起雪球向弟弟攻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攻击院子里的笑声就更大了。
童年是多么的有趣呀!童年趣事给我带来了欢乐,童年真好。
童年趣事
童年是五彩缤纷的,就像海边漂亮的贝壳;童年是无忧无虑的,就像整天嘻闹的浪娃娃;童年是纯真甜美的,就像山溪中清亮的泉水。说起童年,倒不禁使我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
记得那是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奶奶给我和菊菊每人一粒使人一见就流口水的高级奶糖,这可把我们两只“小馋猫”给乐坏了,真是心花怒放。
我们俩谁也舍不得吃。我说:“咱们吃了好吗?”“好,一起吃!”菊菊答应了。我手脚快,一下两下就拆开了,我拿出糖,伸长脖子去看菊菊的。我一看她的糖,急了:
“你的比我的大!”
“哪里?我的这里缺一点!”
“哼,我的溶掉了!”
“你的颜色浓,牛奶多!”
“……”
我们争来争去没有结果,都觉得自己吃亏。可一说要调换,就连忙转过身,谁也不愿意。我们开始吃糖了,“1、2、3!”我们一起吃了下去。哇!真甜,真鲜,真香!吃了一会儿,我说:“拿出来看看,你大还是我大!”“好!”菊菊说着像只哈巴狗一样把糖顶在舌尖上伸出来。我一看也同她那样伸出舌头,可她说看不清楚,我只好把糖放在舌尖上,半粒在外面,并竭力把舌头向外伸。这时,正好一只小狗钻到我脚下,我躲闪不及,舌尖上的糖一不小心掉在了地上,真是无巧不成书,我整个人向前一冲,右脚正好对着那粒糖,唉呀,怎么办?说时迟,那时快,我还没来得及回过神来,脚已经踩在“宝贝”上了。我真是又急又气:“你这只臭狗、烂狗、死狗!”我对准狗肚子就是一脚,狗吓得连忙逃走了。我抬起脚,用手掰掉粘在鞋底上的糖,左瞧右瞧,舍不得扔掉。“扔掉呀,难道你还想吃吗?”菊菊讽刺我说。我两只粘满糖的手不由自主地搓着,两只眼睛盯着菊菊的嘴巴,就是让我看一看奶糖也好。我不断地咽着口水,恨不得她把糖吐出来,咬半粒给我吃。我再也看不下去了,只觉得鼻子一酸,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下来:“妈妈,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现在,时光老人已经来临,把童年匆匆带走了。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为了一粒糖而斤斤计较,更不会大哭一场。感谢时光老人,因为他把童年编成一本最纯最真最美的书印在我们的心坎里。■
说这么多,希望对你有一定帮助
从我记事起,大姨的班上就养了两只小鸡,一有时间我就去大姨班上看小鸡,不知过了多久,两只小鸡渐渐长大了,又过了许久,母鸡下蛋了,蛋中要孵出小鸡了,21天后,闻声可听一阵小鸡的叫声,看到这情况,听到这声音。我觉得小鸡太可怜了,在母鸡和公鸡都不在家时,帮一下小鸡。机会,终于来了……
那天,母鸡给小小鸡找食去了,淘气的公鸡也不在家,跑出去玩了。趁大姨不注意顺手拿起一个鸡蛋,捧在手心里轻轻抚摸着,一本正经地说:“小鸡不要害怕,一会你就会来到世界上了。”说完,我不再犹豫了,剥开了一个鸡蛋,一只带有余热,未睁开眼睛的小鸡“诞生”了,它看了看我,叫了两声好像在说:“谢谢你,让我早日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可高兴了,又剥开了第二个,当我剥到第四个的时候母鸡回来了,看见我正在“欺负”蛇的小宝宝就猛琢了我一口,顿时鲜血流了出来,我哭哭啼啼地去找大姨,大姨并没说我,反而哭笑不得地说:“小傻瓜,鸡要到一定时候才会出生呢!你这样给它们接生,会死的。”我听完,赶忙跑看小鸡,果然刚刚被我“接生”的小鸡都快死了,而没被我“接生”的都活了下来。我后悔极了,但一切都晚了……
虽然这件事过去很久了,虽然那里我还年幼无知,但这件事一直鞭策着我,让我勇往直前,永不后退。
童年,是欢乐的海洋。在回忆的海边,有无数的贝壳,有灰暗的,勾起一段伤心的往事;有灿烂的,使人想起童年趣事。我在那回忆的海岸,寻觅着最美丽的贝壳,啊,找到了……
那时,我才六岁,是对过生日情有独钟的年龄。我喜欢过生日,因为我会吃到大蛋糕,而那次,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忙碌了一上午的我,终于可以吃到盼望以久的蛋糕啦!瞧,那蛋糕又大又圆,被纯白的奶油覆盖着,上面堆满了各种奶油花儿,好像在对我笑着,可爱极了!蛋糕上还用红果酱写的“生日快乐”。再烛光的映衬下,蛋糕真令我垂涎三尺啊!我迫不及待的想吃掉它。
终于到手啦!一大块蛋糕被我拿在手中。我咬了一大口,啊,真是美味啊!姐姐突然笑了,这笑让我莫名其妙,一照镜子,呵,我把一块奶油蹭在了鼻子上,活像一个小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姐姐不爱吃奶油,正想着怎么办,忽然看见我鼻子上的奶油,眼睛猛一亮,笑眯眯地说“妹妹,过来!”我想都没想,大步跨了过去。姐姐让我坐下,只见她端来一个盘子,里面有我爱吃的奶油,我以为她要给我吃,赶快张大了嘴。“啪”,一块凉凉的东西贴在了我的脑门上,接着是脸,下巴,我知道是奶油,便伸长了舌头去舔,却听见了一阵大笑。去镜子前一看,哈!镜子里出现了一只小花猫!满脸的奶油,东一块,西一块。我的脸被这种“高级”化妆品涂的好似京剧脸谱一般。不,京剧脸谱的颜色没这么单一,纯白的奶油在镜子里好像小花猫的毛,我舔奶油,何不像一只馋猫!我也笑了,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摇身一变,竟变成了一只馋嘴的小花猫!
童年趣事,件件都像一枚五彩的贝壳,这些五彩的贝壳,托起了我五彩的童年!
小时侯的我特别的调皮捣蛋,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我童年的一件趣事。
记得有一次回家,我看到爸爸正躺在床上睡觉,于是我的小脑袋里便突然冒出了一个“坏”念头,就是画“脸谱”,当然不是在纸上画,而是-----在爸爸的脸上画,我先找出颜料、笔和水,随后我在爸爸的额上小心翼翼的画上了一个大大的“王”字,再用土黄色在爸爸脸的四周画上一堆金灿灿的斑纹,这样就是一只威风十足的老虎了,画完之后我一边为自己的“杰作”感到高兴也一边为爸爸的脸被我画成这样感到惋惜,因为爸爸那张漂亮的脸被我画成这样真是可惜。正在我高兴的看着自己的“杰作”的时候,突然爸爸醒了过来,看着他一脸茫然的样子,我哈哈大笑起来,爸爸莫名其妙的看看我,当他看到满地的水彩颜料和水,看着我那不怀好意的笑,爸爸连忙跑到卫生间去照镜子,当他发现自己的脸上已经被我画成一道一道的时候,他也顾不得脸上有水彩颜料,就飞快的跑进屋,抓起我就是一顿乱打,打的我是咕呱乱叫,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我仍记忆犹心。
你看!我小时侯多调皮呀!直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趣呢!
每个人的童年中都有许许多多有趣的事,我当然也不例外,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在我童年中一件有趣的事情吧。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在姥姥家玩,姥姥家住农村,她养了很多鸡。 有一天,姥姥、舅舅、姥爷出去玩把我一个人扔在家,我很生气,心想,他们怎么这样,出去也不带我。在屋里闲着没事干,便想去鸡舍中,看看那些鸡在干什么。 我刚进去,只听“砰”的一声,一只母鸡生了一个蛋。真好玩,我好奇的摸了摸蛋,咦,热热的,湿湿的。这是,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心想,鸡会生蛋,那鸡舍中所有的鸡一定都会生了,要不掏鸡蛋吧,姥姥回来看到这么多的蛋,还不夸奖我,没准还奖励我呢,对掏鸡蛋!想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一只鸡就掏,那只鸡好像知道自己命运似的,使劲拍着翅膀,想要逃,我呢,死抓着鸡爪不放,看是它厉害还是我厉害,掏了半天没掏出来,怎么回事,怎么掏不出来,难到我的奖励没了吗?我偏不信,这只掏不出来在掏另一只吧,我随手把鸡一扔,又去抓别的鸡,那些鸡看见我走来,一个个上窜下跳,好像老鼠见到猫一样,拔腿就跑,我呢,就不放手,一个劲去抓鸡,这不,还没半个小时我就快变成鸡毛人了。好不容易才抓到一只鸡,我上手就掏,掏的那只鸡“嗷嗷”直叫,又没掏出来,再抓一只……掏的这只鸡直吐白沫,我又……姥姥她们回来了,看见我的狼狈样,不禁哈哈大笑,问清原因,姥姥不仅没夸奖我,还训了我一顿,后来,我才知道除了鸡舍中的那只母鸡外,剩下的全都是公鸡。
这就是我童年中一件有趣的事,它不仅好玩,还时时告戒我:偷鸡不成拾把米,千万不要好心办坏事。
童年是七色的,是热情的,可爱的。童年是这么的美好,那童年趣事又是这样的呢?
我是一个北方的女孩,小时侯的我喜欢在冰天雪地里玩,打雪仗、堆雪人。每当冬天到来时,鹅毛般地大雪从空中飘落下来,一朵朵、一簇簇,像银花,似白蝶。展望天地之间,唯见雪花飘扬,像吹落地花瓣,纷纷扬扬;像七仙女散花,漫天飞舞。人站立在雪中,就像蹲在轧花机上,只看见无数的棉絮花拂向你,给你罩了一身洁白的素花。
早上起来,风定了,雪停了。打开门,一道白色的寒光刺得人眼花缭乱。于是,我和弟弟、表哥拿起铲子就在院子里堆起了雪人,洁白的身子,圆圆的头,煤球做黑眼睛,棉花捏成的鼻子,还向上翘着呢!表哥又用红墨水给雪人涂了嘴巴,一咧一咧,正朝着我们哈哈大笑呢!弟弟用一张红色的纸给雪人做了一顶漂亮的帽子。雪人一下变得神气多了!雪人堆成了,又迎来一场大仗,表哥掷好一个雪球趁我不注意向我发起进攻,还好没大中。当我反击表哥时,他已经被弟弟的雪球打中了,雪球在表哥的头顶上开了画,这时院子里充满了欢笑声。表哥不服气,拿起雪球向弟弟攻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攻击院子里的笑声就更大了。
童年是多么的有趣呀!童年趣事给我带来了欢乐,童年真好。
童年趣事
童年是五彩缤纷的,就像海边漂亮的贝壳;童年是无忧无虑的,就像整天嘻闹的浪娃娃;童年是纯真甜美的,就像山溪中清亮的泉水。说起童年,倒不禁使我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
记得那是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奶奶给我和菊菊每人一粒使人一见就流口水的高级奶糖,这可把我们两只“小馋猫”给乐坏了,真是心花怒放。
我们俩谁也舍不得吃。我说:“咱们吃了好吗?”“好,一起吃!”菊菊答应了。我手脚快,一下两下就拆开了,我拿出糖,伸长脖子去看菊菊的。我一看她的糖,急了:
“你的比我的大!”
“哪里?我的这里缺一点!”
“哼,我的溶掉了!”
“你的颜色浓,牛奶多!”
“……”
我们争来争去没有结果,都觉得自己吃亏。可一说要调换,就连忙转过身,谁也不愿意。我们开始吃糖了,“1、2、3!”我们一起吃了下去。哇!真甜,真鲜,真香!吃了一会儿,我说:“拿出来看看,你大还是我大!”“好!”菊菊说着像只哈巴狗一样把糖顶在舌尖上伸出来。我一看也同她那样伸出舌头,可她说看不清楚,我只好把糖放在舌尖上,半粒在外面,并竭力把舌头向外伸。这时,正好一只小狗钻到我脚下,我躲闪不及,舌尖上的糖一不小心掉在了地上,真是无巧不成书,我整个人向前一冲,右脚正好对着那粒糖,唉呀,怎么办?说时迟,那时快,我还没来得及回过神来,脚已经踩在“宝贝”上了。我真是又急又气:“你这只臭狗、烂狗、死狗!”我对准狗肚子就是一脚,狗吓得连忙逃走了。我抬起脚,用手掰掉粘在鞋底上的糖,左瞧右瞧,舍不得扔掉。“扔掉呀,难道你还想吃吗?”菊菊讽刺我说。我两只粘满糖的手不由自主地搓着,两只眼睛盯着菊菊的嘴巴,就是让我看一看奶糖也好。我不断地咽着口水,恨不得她把糖吐出来,咬半粒给我吃。我再也看不下去了,只觉得鼻子一酸,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下来:“妈妈,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现在,时光老人已经来临,把童年匆匆带走了。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为了一粒糖而斤斤计较,更不会大哭一场。感谢时光老人,因为他把童年编成一本最纯最真最美的书印在我们的心坎里。■
回答者:w553604923 - 初学弟子 一级 11-25 17:30
这是我从网上找的‘童年趣事’你参考下
童年是快乐的,童年是美好的。我的童年就非常快乐。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阳光明媚,正好下楼去玩。我把我的那几个好朋友一朱昱、胡晓、蔡李宁洁聚集在一起。我做了个打枪的姿势,他们点了点头,一致同意玩“反恐”。我们分别扮成两个“小偷”,两个“警察”,枪就用小木棍代替。
第—盘,我先当严“小偷”。要先跑,我和我的同伴胡晓跑到一个门栋里躲着,等待着“敌人”的到来;可是等了半天,也没有人影;我悄悄对胡晓说:“这样等没完没了,我出去侦察一下,你在这里不要离开”。说完,我贼溜溜地沿着墙壁走,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仔细察看一番,生怕露出一点“狐狸尾巴”。当我来到一栋楼的拐角处,突然一个轻轻的步子向我走来,我急了,怕“警察”跳出来把我“击毙”。我四处张望,想找到一线生机溜走,可是已来不及了。“警察”朱昱箭步冲到我面前对我“咚、咚—….”猛“开枪”。等我再回到那个门栋找到胡晓时,他垂头丧气地对我说;“你刚一走,,蔡李宁洁就冲进来把我干掉了”。原来“警察”一直盯者我们的动向,等我走了,就采用偷袭战术。
第二盘,我们互换角色。,我和胡晓紧握双手,发誓一定要把“小偷”抓获归案。我们看见他们躲好了,开始了战斗。正当我们胜利在望时,“洛洛,快回家吃饭!”,听到妈妈在大声呼唤。大家都停住了战斗的脚步,我无奈地跑回家。不知他们此时心情怎样,我心里可是仍然想着,这次战斗我们必胜。
怎样?我的童年快乐吧
(女孩子也可以玩的!绝对真实!!!!!)
“童年的梦,七彩的梦;童年的歌,欢乐的歌;童年的脚印一串串;童年的故事一摞摞。”这首歌是否能让你回想起美好的童年生活?在那五彩缤纷的岁月中,发生过许多事情,不像星星一样的明亮。我的童年是美好的,有许多事值得回忆……
从我记事起,大姨的班上就养了两只小鸡,一有时间我就去大姨班上看小鸡,不知过了多久,两只小鸡渐渐长大了,又过了许久,母鸡下蛋了,蛋中要孵出小鸡了,21天后,闻声可听一阵小鸡的叫声,看到这情况,听到这声音。我觉得小鸡太可怜了,在母鸡和公鸡都不在家时,帮一下小鸡。机会,终于来了……
那天,母鸡给小小鸡找食去了,淘气的公鸡也不在家,跑出去玩了。趁大姨不注意顺手拿起一个鸡蛋,捧在手心里轻轻抚摸着,一本正经地说:“小鸡不要害怕,一会你就会来到世界上了。”说完,我不再犹豫了,剥开了一个鸡蛋,一只带有余热,未睁开眼睛的小鸡“诞生”了,它看了看我,叫了两声好像在说:“谢谢你,让我早日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可高兴了,又剥开了第二个,当我剥到第四个的时候母鸡回来了,看见我正在“欺负”蛇的小宝宝就猛琢了我一口,顿时鲜血流了出来,我哭哭啼啼地去找大姨,大姨并没说我,反而哭笑不得地说:“小傻瓜,鸡要到一定时候才会出生呢!你这样给它们接生,会死的。”我听完,赶忙跑看小鸡,果然刚刚被我“接生”的小鸡都快死了,而没被我“接生”的都活了下来。我后悔极了,但一切都晚了……
虽然这件事过去很久了,虽然那里我还年幼无知,但这件事一直鞭策着我,让我勇往直前,永不后退。
童年,是欢乐的海洋。在回忆的海边,有无数的贝壳,有灰暗的,勾起一段伤心的往事;有灿烂的,使人想起童年趣事。我在那回忆的海岸,寻觅着最美丽的贝壳,啊,找到了……
那时,我才六岁,是对过生日情有独钟的年龄。我喜欢过生日,因为我会吃到大蛋糕,而那次,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忙碌了一上午的我,终于可以吃到盼望以久的蛋糕啦!瞧,那蛋糕又大又圆,被纯白的奶油覆盖着,上面堆满了各种奶油花儿,好像在对我笑着,可爱极了!蛋糕上还用红果酱写的“生日快乐”。再烛光的映衬下,蛋糕真令我垂涎三尺啊!我迫不及待的想吃掉它。
终于到手啦!一大块蛋糕被我拿在手中。我咬了一大口,啊,真是美味啊!姐姐突然笑了,这笑让我莫名其妙,一照镜子,呵,我把一块奶油蹭在了鼻子上,活像一个小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姐姐不爱吃奶油,正想着怎么办,忽然看见我鼻子上的奶油,眼睛猛一亮,笑眯眯地说“妹妹,过来!”我想都没想,大步跨了过去。姐姐让我坐下,只见她端来一个盘子,里面有我爱吃的奶油,我以为她要给我吃,赶快张大了嘴。“啪”,一块凉凉的东西贴在了我的脑门上,接着是脸,下巴,我知道是奶油,便伸长了舌头去舔,却听见了一阵大笑。去镜子前一看,哈!镜子里出现了一只小花猫!满脸的奶油,东一块,西一块。我的脸被这种“高级”化妆品涂的好似京剧脸谱一般。不,京剧脸谱的颜色没这么单一,纯白的奶油在镜子里好像小花猫的毛,我舔奶油,何不像一只馋猫!我也笑了,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摇身一变,竟变成了一只馋嘴的小花猫!
童年趣事,件件都像一枚五彩的贝壳,这些五彩的贝壳,托起了我五彩的童年!
小时侯的我特别的调皮捣蛋,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我童年的一件趣事。
记得有一次回家,我看到爸爸正躺在床上睡觉,于是我的小脑袋里便突然冒出了一个“坏”念头,就是画“脸谱”,当然不是在纸上画,而是-----在爸爸的脸上画,我先找出颜料、笔和水,随后我在爸爸的额上小心翼翼的画上了一个大大的“王”字,再用土黄色在爸爸脸的四周画上一堆金灿灿的斑纹,这样就是一只威风十足的老虎了,画完之后我一边为自己的“杰作”感到高兴也一边为爸爸的脸被我画成这样感到惋惜,因为爸爸那张漂亮的脸被我画成这样真是可惜。正在我高兴的看着自己的“杰作”的时候,突然爸爸醒了过来,看着他一脸茫然的样子,我哈哈大笑起来,爸爸莫名其妙的看看我,当他看到满地的水彩颜料和水,看着我那不怀好意的笑,爸爸连忙跑到卫生间去照镜子,当他发现自己的脸上已经被我画成一道一道的时候,他也顾不得脸上有水彩颜料,就飞快的跑进屋,抓起我就是一顿乱打,打的我是咕呱乱叫,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我仍记忆犹心。
你看!我小时侯多调皮呀!直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趣呢!
每个人的童年中都有许许多多有趣的事,我当然也不例外,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在我童年中一件有趣的事情吧。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在姥姥家玩,姥姥家住农村,她养了很多鸡。 有一天,姥姥、舅舅、姥爷出去玩把我一个人扔在家,我很生气,心想,他们怎么这样,出去也不带我。在屋里闲着没事干,便想去鸡舍中,看看那些鸡在干什么。 我刚进去,只听“砰”的一声,一只母鸡生了一个蛋。真好玩,我好奇的摸了摸蛋,咦,热热的,湿湿的。这是,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心想,鸡会生蛋,那鸡舍中所有的鸡一定都会生了,要不掏鸡蛋吧,姥姥回来看到这么多的蛋,还不夸奖我,没准还奖励我呢,对掏鸡蛋!想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一只鸡就掏,那只鸡好像知道自己命运似的,使劲拍着翅膀,想要逃,我呢,死抓着鸡爪不放,看是它厉害还是我厉害,掏了半天没掏出来,怎么回事,怎么掏不出来,难到我的奖励没了吗?我偏不信,这只掏不出来在掏另一只吧,我随手把鸡一扔,又去抓别的鸡,那些鸡看见我走来,一个个上窜下跳,好像老鼠见到猫一样,拔腿就跑,我呢,就不放手,一个劲去抓鸡,这不,还没半个小时我就快变成鸡毛人了。好不容易才抓到一只鸡,我上手就掏,掏的那只鸡“嗷嗷”直叫,又没掏出来,再抓一只……掏的这只鸡直吐白沫,我又……姥姥她们回来了,看见我的狼狈样,不禁哈哈大笑,问清原因,姥姥不仅没夸奖我,还训了我一顿,后来,我才知道除了鸡舍中的那只母鸡外,剩下的全都是公鸡。
这就是我童年中一件有趣的事,它不仅好玩,还时时告戒我:偷鸡不成拾把米,千万不要好心办坏事。
童年是七色的,是热情的,可爱的。童年是这么的美好,那童年趣事又是这样的呢?
我是一个北方的女孩,小时侯的我喜欢在冰天雪地里玩,打雪仗、堆雪人。每当冬天到来时,鹅毛般地大雪从空中飘落下来,一朵朵、一簇簇,像银花,似白蝶。展望天地之间,唯见雪花飘扬,像吹落地花瓣,纷纷扬扬;像七仙女散花,漫天飞舞。人站立在雪中,就像蹲在轧花机上,只看见无数的棉絮花拂向你,给你罩了一身洁白的素花。
早上起来,风定了,雪停了。打开门,一道白色的寒光刺得人眼花缭乱。于是,我和弟弟、表哥拿起铲子就在院子里堆起了雪人,洁白的身子,圆圆的头,煤球做黑眼睛,棉花捏成的鼻子,还向上翘着呢!表哥又用红墨水给雪人涂了嘴巴,一咧一咧,正朝着我们哈哈大笑呢!弟弟用一张红色的纸给雪人做了一顶漂亮的帽子。雪人一下变得神气多了!雪人堆成了,又迎来一场大仗,表哥掷好一个雪球趁我不注意向我发起进攻,还好没大中。当我反击表哥时,他已经被弟弟的雪球打中了,雪球在表哥的头顶上开了画,这时院子里充满了欢笑声。表哥不服气,拿起雪球向弟弟攻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攻击院子里的笑声就更大了。
童年是多么的有趣呀!童年趣事给我带来了欢乐,童年真好。
童年趣事
童年是五彩缤纷的,就像海边漂亮的贝壳;童年是无忧无虑的,就像整天嘻闹的浪娃娃;童年是纯真甜美的,就像山溪中清亮的泉水。说起童年,倒不禁使我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
记得那是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奶奶给我和菊菊每人一粒使人一见就流口水的高级奶糖,这可把我们两只“小馋猫”给乐坏了,真是心花怒放。
我们俩谁也舍不得吃。我说:“咱们吃了好吗?”“好,一起吃!”菊菊答应了。我手脚快,一下两下就拆开了,我拿出糖,伸长脖子去看菊菊的。我一看她的糖,急了:
“你的比我的大!”
“哪里?我的这里缺一点!”
“哼,我的溶掉了!”
“你的颜色浓,牛奶多!”
“……”
我们争来争去没有结果,都觉得自己吃亏。可一说要调换,就连忙转过身,谁也不愿意。我们开始吃糖了,“1、2、3!”我们一起吃了下去。哇!真甜,真鲜,真香!吃了一会儿,我说:“拿出来看看,你大还是我大!”“好!”菊菊说着像只哈巴狗一样把糖顶在舌尖上伸出来。我一看也同她那样伸出舌头,可她说看不清楚,我只好把糖放在舌尖上,半粒在外面,并竭力把舌头向外伸。这时,正好一只小狗钻到我脚下,我躲闪不及,舌尖上的糖一不小心掉在了地上,真是无巧不成书,我整个人向前一冲,右脚正好对着那粒糖,唉呀,怎么办?说时迟,那时快,我还没来得及回过神来,脚已经踩在“宝贝”上了。我真是又急又气:“你这只臭狗、烂狗、死狗!”我对准狗肚子就是一脚,狗吓得连忙逃走了。我抬起脚,用手掰掉粘在鞋底上的糖,左瞧右瞧,舍不得扔掉。“扔掉呀,难道你还想吃吗?”菊菊讽刺我说。我两只粘满糖的手不由自主地搓着,两只眼睛盯着菊菊的嘴巴,就是让我看一看奶糖也好。我不断地咽着口水,恨不得她把糖吐出来,咬半粒给我吃。我再也看不下去了,只觉得鼻子一酸,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下来:“妈妈,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现在,时光老人已经来临,把童年匆匆带走了。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为了一粒糖而斤斤计较,更不会大哭一场。感谢时光老人,因为他把童年编成一本最纯最真最美的书印在我们的心坎里。■
说这么多,希望对你有一定帮助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4-01-16
我的爷爷
秃脑门,花白头发,两撇剑眉,深陷的眼睛,满脸深深浅浅的皱纹,这就是我爷爷。十多年来,我们形影不离,还曾发生过好多有趣的故事呢!
我们常常嬉闹得不分彼此。别以为我是个小姑娘,很文雅很安分的样子,其实我曾是个爱调皮的假小子!我在爷爷脸上画过一幅惊人的“杰作”,让他出尽洋相!
而我们更是互相帮助的朋友。有时,趁他高兴,我大胆地摸摸他的脑袋,说:“这里怎么一马平川呀?”他笑着,故作深沉地:“人多的地方不长草,学问多的地方不长毛呀!”
他说的还真有道理。不信,说一件事给你听听!我开始写作文总是东拉葫芦西扯瓢,眉毛胡子一把抓,一团乱麻!爷爷见了,不慌不忙,拿起红笔,好像拿起一把解剖刀:“哈,让我来个快刀斩乱麻吧!”台灯的光影里,爷爷凝然不动,浓眉下一双眼睛炯炯放光,好像猎人捕捉猎物。灯光下,我发现他一双大手布满了老人斑,爬满了蚯蚓一样的青筋;稀疏的白发丛中,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我好一阵感动!不多会,爷爷舒长手臂,轻吁一口气,大功告成啦!我细细浏览,哈,真是妙手回春呀!我手捧渗透了爷爷心血的作文,觉得沉甸甸的……
爷爷累了,闭目养神。在灯光映照下,那秃脑门上的白发,就像一簇盛开的洁白的梨花。我想,爷爷始终把“奉献”当着一种幸福,我这个小孙女更应该把“给予”当着最大的快乐啊!我悄悄走到爷爷身后,拿出我的看家本领:给爷爷捶背。我的小拳头就像有节奏的鼓点似地,时轻时重,忽缓忽急,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他轻轻摇晃着,好不快活!不知不觉,爷爷竟打起了呼噜……我拿来被单,给他轻轻盖上,然后蹑手蹑脚走开了……
其实,我们之间的故事多着呢,这只是记忆长河里的几朵浪花……
不是吗? 我是他心中的小凤凰,他是我心灵土地上的大树,每一片叶子都写满了爱!我想,不管我将来走到哪里,哪怕是天涯海角;也不管我长大多少,哪怕长成长发披肩的大姑娘,我也绝不会忘记,在我心灵的天地间,永远屹立着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那就是我亲爱的爷爷!
这事说来又是十多年了。
算来我是六岁。因为第二次我见到长子四叔时,他那条有趣的辫子就不见了。
那是夏天秋天之间。我仿佛还没有上过学。妈因怕我到外面同瑞龙他们玩时又打架,或是乱吃东西,每天都要靠到她身边坐着,除了吃晚饭后洗完澡同大哥各人拿五个小钱到道门口去买士元的凉粉外,剩下便都不准出去了!至于为甚又能吃凉粉?那大概是妈知道士元凉粉是玫瑰糖,不至吃后生病吧。本来那时的时疫也真凶,听瑞龙妈说,杨老六一家四口人,从十五得病,不到三天便都死了!
我们是在堂屋背后那小天井内席子上坐着的。妈为我从一个小黑洋铁箱子内取出一束一束方块儿字来念,她便膝头上搁着一个麻篮绩麻。弄子里跑来的风又凉又软,很易引人瞌睡,当我倒在席子上时,妈总每每停了她的工作,为我拿蒲扇来赶那些专爱停留在人脸上的饭蚊子。间或有个时候妈也会睡觉,必到大哥从学校夹着书包回来嚷肚子饿时才醒,那末,夜饭必定便又要晚一点了!
爹好象到乡下江家坪老屋去了好久了,有天忽然要四叔来接我们。接的意思四叔也不大清楚,大概也就是闻到城里时疫的事情吧。妈也不说什么,她知道大姐二姐都在乡里,我自然有她们料理。只嘱咐了四叔不准大哥到乡下溪里去洗澡。
因大哥前几天回来略晚,妈摩他小辫子还湿漉漉的,知他必是同几个同学到大河里洗过澡了,还重重的打了他一顿呢。四 叔是一个长子,人又不大肥,但很精壮。妈常说这是会走路的人。铜仁到我凤皇是一百二十里蛮路,他能扛六十斤担子一早动身,不抹黑就到了,这怎么不算狠!他到了家时,便忙自去厨房烧水洗脚。那夜我们吃的夜饭菜是南瓜炒牛肉。
妈捡菜劝他时,他又选出无辣子的牛肉放到我碗里。真是好四叔呵!
那时人真小,我同大哥还是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为四叔担去的!大哥虽大我五六岁,但在四叔肩上似乎并不什么不匀称。乡下隔城有四十多里,妈怕太阳把我们晒出病来,所以我们天刚一发白就动身,到行有一半的唐峒山时,太阳还才红红的。到了山顶,四叔把我们抱出来各人放了一泡尿,我们便都坐在一株大刺栎树下歇憩。那树的杈桠上搁了无数小石头,树左边又有一个石头堆成的小屋子。四叔为我们解说,小屋子是山神土地,为赶山打野猪人设的;树上石头是寄倦的:凡是走长路的人,只要放一个石头到树上,便不倦了。但大哥问他为甚不也放一个石子时,他却不做声。
他那条辫子细而长正同他身子一样。本来是挽放头上后再加上草帽的,不知是那辫子长了呢还是他太随意,总是动不动又掉下来,当我是在他背后那头时,辫子梢梢便时时在我头上晃。
“芸儿,莫闹!扯着我不好走!”
我伸出手扯着他辫子只是拽,他总是和和气气这样说。
“四满①,到了?”大哥很着急的这么问。
“快了,快了,快了!芸弟都不急,你怎么这样慌?你看我跑!”他略略把脚步放快一点,大哥便又嚷摇的头痛了。
他一路笑大哥不济。
到时,爹正同姨婆五叔四婶他们在院中土坪上各坐在一 条小凳上说话。姨婆有两年不见我了,抱了我亲了又亲。爹又问我们饿了不曾,其实我们到路上吃甜酒、米豆腐已吃胀了。上灯时,方见大姐二姐大姑满姑②各人手上提了一捆地萝卜进来。
我夜里便同大姐等到姨婆房里睡。
乡里有趣多了!既不什么很热,夜里蚊子也很少。大姐到久一点,似乎各样事情都熟习,第二天一早便引我去羊栏边看睡着比猫还小的白羊,牛栏里正歪起颈项在吃奶的牛儿。
我们又到竹园中去看竹子。那时觉得竹子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本来城里的竹子,通常大到屠桌边卖肉做钱筒的已算出奇了!但后园里那些南竹,大姐教我去试抱一下时,两手竟不能相掺。满姑又为偷偷的到园坎上摘了十多个桃子。接着我们便跑到大门外溪沟边上拾得一衣兜花蚌壳。
事事都感到新奇:譬如五叔喂的那十多只白鸭子,它们会一翅从塘坎上飞过溪沟。夜里四叔他们到溪里去照鱼时,却不用什么网,单拿个火把,拿把镰刀。姨婆喂有七八只野鸡,能飞上屋,也能上树,却不飞去;并且,只要你拿一捧包谷米在手,口中略略一逗,它们便争先恐后的到你身边来了。什么事情都有味。我们白天便跑到附近村子里去玩,晚上总是同坐在院中听姨婆学打野猪打獾子的故事。姨婆真好,我们上床时,她还每每为从大油坛里取出炒米、栗子同脆酥酥的豆子给我们吃!
后园坎上那桃子已透熟了,满姑一天总为我们去偷几次。
爹又不大出来,四叔五叔又从不说话,间或碰到姨婆见了时,也不过笑笑的说:“小娥,你又忘记嚷肚子痛了!真不听讲——芸儿,莫听你满姑的话,吃多了要坏肚子!拿把我,不然晚上又吃不得鸡膊腿了!”
乡里去有场集的地方似乎并不很近,而小小村中除每五 天逢一六赶场外通常都无肉卖。因此,我们几乎天天吃鸡,惟我一人年小,鸡的大腿便时时归我。
我们最爱看又怕看的是溪南头那坝上小碾房的磨石同自动的水车;碾房是五叔在料理。那圆圆的磨石,固定在一株木桩上只是转只是转。五叔象个卖灰的人,满身是糠皮,只是在旋转不息的磨石间拿扫把扫那跑出碾槽外的谷米。他似乎并不着一点忙,磨石走到他跟前时一跳又让过磨石了。我们为他着急又佩服他胆子大。水车也有味,是一些七长八短的竹篙子扎成的。它的用处就是在灌水到比溪身还高的田面。
大的有些比屋子还大,小的也还有一床晒簟大校它们接接连连竖立在大路近旁,为溪沟里急水冲着快快地转动,有些还咿哩咿哩发出怪难听的喊声,由车旁竹筒中运水倒到悬空的枧③上去。它的怕人就是筒子里水间或溢出枧外时,那水便砰的倒到路上了,你稍不措意,衣服便打得透湿。我们远远的立着看行路人抱着头冲过去时那样子好笑。满姑虽只大我四岁,但看惯了,她却敢在下面走来走去。大姐同大姑,则知道那个车子溢出后便是那一个接脚,不消说是不怕水淋了!
只我同大哥二姐,却无论如何不敢去尝试。
人生中留下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他们像沙滩上闪光的珠贝,时不时的让你拣起它,细细的咀嚼品味。
夜,静得可怕,连一丝风也没有。天上几颗稀稀疏疏的星星眨着眼睛,远处几户人家的火已熄,可我还坐在沙发上久久不能入睡。
收音机里放着周华健的《朋友》,这使我想起了离开母校的日子:
雨淅沥地下着,我撑者伞,独自徘徊在校园内。这儿多美啊——花团锦簇,绿树成阴。曾几何时,这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处处都是琅琅书声。可是,不久,我将离开这美丽的校园,踏上去异地的求学路了。
校园里的旗杆,笔直地耸立着,多少个周一的早晨,我们在这里举行升旗仪式。那操场上,留下了我们开校运会时的激情。
教学楼已在眼前,那么亲切,那么熟悉,使我想起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一眨眼,往事已烟消云散。只留下老师那亲切的面容和朋友们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了。难忘啊!难忘,为什么会这么快地到来。
我怀疑:
是阳光在我们不经意的每一个日子里悄悄地来临又默默地里去;是美丽的蒲公英花轻轻地飞起又复悠悠的落下。
母校是我的玻璃壳。
我想永远呆在里面,我知道, 这是空想,不可能。最终,我还是走出了自己的玻璃壳向着阳光凝视未来。那一天我才发现天空和泥土相濡以沫。
就这样,我离开了。
现在我常常沉醉在往事里,但我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那已经是过去,不可能回来了。
秃脑门,花白头发,两撇剑眉,深陷的眼睛,满脸深深浅浅的皱纹,这就是我爷爷。十多年来,我们形影不离,还曾发生过好多有趣的故事呢!
我们常常嬉闹得不分彼此。别以为我是个小姑娘,很文雅很安分的样子,其实我曾是个爱调皮的假小子!我在爷爷脸上画过一幅惊人的“杰作”,让他出尽洋相!
而我们更是互相帮助的朋友。有时,趁他高兴,我大胆地摸摸他的脑袋,说:“这里怎么一马平川呀?”他笑着,故作深沉地:“人多的地方不长草,学问多的地方不长毛呀!”
他说的还真有道理。不信,说一件事给你听听!我开始写作文总是东拉葫芦西扯瓢,眉毛胡子一把抓,一团乱麻!爷爷见了,不慌不忙,拿起红笔,好像拿起一把解剖刀:“哈,让我来个快刀斩乱麻吧!”台灯的光影里,爷爷凝然不动,浓眉下一双眼睛炯炯放光,好像猎人捕捉猎物。灯光下,我发现他一双大手布满了老人斑,爬满了蚯蚓一样的青筋;稀疏的白发丛中,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我好一阵感动!不多会,爷爷舒长手臂,轻吁一口气,大功告成啦!我细细浏览,哈,真是妙手回春呀!我手捧渗透了爷爷心血的作文,觉得沉甸甸的……
爷爷累了,闭目养神。在灯光映照下,那秃脑门上的白发,就像一簇盛开的洁白的梨花。我想,爷爷始终把“奉献”当着一种幸福,我这个小孙女更应该把“给予”当着最大的快乐啊!我悄悄走到爷爷身后,拿出我的看家本领:给爷爷捶背。我的小拳头就像有节奏的鼓点似地,时轻时重,忽缓忽急,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他轻轻摇晃着,好不快活!不知不觉,爷爷竟打起了呼噜……我拿来被单,给他轻轻盖上,然后蹑手蹑脚走开了……
其实,我们之间的故事多着呢,这只是记忆长河里的几朵浪花……
不是吗? 我是他心中的小凤凰,他是我心灵土地上的大树,每一片叶子都写满了爱!我想,不管我将来走到哪里,哪怕是天涯海角;也不管我长大多少,哪怕长成长发披肩的大姑娘,我也绝不会忘记,在我心灵的天地间,永远屹立着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那就是我亲爱的爷爷!
这事说来又是十多年了。
算来我是六岁。因为第二次我见到长子四叔时,他那条有趣的辫子就不见了。
那是夏天秋天之间。我仿佛还没有上过学。妈因怕我到外面同瑞龙他们玩时又打架,或是乱吃东西,每天都要靠到她身边坐着,除了吃晚饭后洗完澡同大哥各人拿五个小钱到道门口去买士元的凉粉外,剩下便都不准出去了!至于为甚又能吃凉粉?那大概是妈知道士元凉粉是玫瑰糖,不至吃后生病吧。本来那时的时疫也真凶,听瑞龙妈说,杨老六一家四口人,从十五得病,不到三天便都死了!
我们是在堂屋背后那小天井内席子上坐着的。妈为我从一个小黑洋铁箱子内取出一束一束方块儿字来念,她便膝头上搁着一个麻篮绩麻。弄子里跑来的风又凉又软,很易引人瞌睡,当我倒在席子上时,妈总每每停了她的工作,为我拿蒲扇来赶那些专爱停留在人脸上的饭蚊子。间或有个时候妈也会睡觉,必到大哥从学校夹着书包回来嚷肚子饿时才醒,那末,夜饭必定便又要晚一点了!
爹好象到乡下江家坪老屋去了好久了,有天忽然要四叔来接我们。接的意思四叔也不大清楚,大概也就是闻到城里时疫的事情吧。妈也不说什么,她知道大姐二姐都在乡里,我自然有她们料理。只嘱咐了四叔不准大哥到乡下溪里去洗澡。
因大哥前几天回来略晚,妈摩他小辫子还湿漉漉的,知他必是同几个同学到大河里洗过澡了,还重重的打了他一顿呢。四 叔是一个长子,人又不大肥,但很精壮。妈常说这是会走路的人。铜仁到我凤皇是一百二十里蛮路,他能扛六十斤担子一早动身,不抹黑就到了,这怎么不算狠!他到了家时,便忙自去厨房烧水洗脚。那夜我们吃的夜饭菜是南瓜炒牛肉。
妈捡菜劝他时,他又选出无辣子的牛肉放到我碗里。真是好四叔呵!
那时人真小,我同大哥还是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为四叔担去的!大哥虽大我五六岁,但在四叔肩上似乎并不什么不匀称。乡下隔城有四十多里,妈怕太阳把我们晒出病来,所以我们天刚一发白就动身,到行有一半的唐峒山时,太阳还才红红的。到了山顶,四叔把我们抱出来各人放了一泡尿,我们便都坐在一株大刺栎树下歇憩。那树的杈桠上搁了无数小石头,树左边又有一个石头堆成的小屋子。四叔为我们解说,小屋子是山神土地,为赶山打野猪人设的;树上石头是寄倦的:凡是走长路的人,只要放一个石头到树上,便不倦了。但大哥问他为甚不也放一个石子时,他却不做声。
他那条辫子细而长正同他身子一样。本来是挽放头上后再加上草帽的,不知是那辫子长了呢还是他太随意,总是动不动又掉下来,当我是在他背后那头时,辫子梢梢便时时在我头上晃。
“芸儿,莫闹!扯着我不好走!”
我伸出手扯着他辫子只是拽,他总是和和气气这样说。
“四满①,到了?”大哥很着急的这么问。
“快了,快了,快了!芸弟都不急,你怎么这样慌?你看我跑!”他略略把脚步放快一点,大哥便又嚷摇的头痛了。
他一路笑大哥不济。
到时,爹正同姨婆五叔四婶他们在院中土坪上各坐在一 条小凳上说话。姨婆有两年不见我了,抱了我亲了又亲。爹又问我们饿了不曾,其实我们到路上吃甜酒、米豆腐已吃胀了。上灯时,方见大姐二姐大姑满姑②各人手上提了一捆地萝卜进来。
我夜里便同大姐等到姨婆房里睡。
乡里有趣多了!既不什么很热,夜里蚊子也很少。大姐到久一点,似乎各样事情都熟习,第二天一早便引我去羊栏边看睡着比猫还小的白羊,牛栏里正歪起颈项在吃奶的牛儿。
我们又到竹园中去看竹子。那时觉得竹子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本来城里的竹子,通常大到屠桌边卖肉做钱筒的已算出奇了!但后园里那些南竹,大姐教我去试抱一下时,两手竟不能相掺。满姑又为偷偷的到园坎上摘了十多个桃子。接着我们便跑到大门外溪沟边上拾得一衣兜花蚌壳。
事事都感到新奇:譬如五叔喂的那十多只白鸭子,它们会一翅从塘坎上飞过溪沟。夜里四叔他们到溪里去照鱼时,却不用什么网,单拿个火把,拿把镰刀。姨婆喂有七八只野鸡,能飞上屋,也能上树,却不飞去;并且,只要你拿一捧包谷米在手,口中略略一逗,它们便争先恐后的到你身边来了。什么事情都有味。我们白天便跑到附近村子里去玩,晚上总是同坐在院中听姨婆学打野猪打獾子的故事。姨婆真好,我们上床时,她还每每为从大油坛里取出炒米、栗子同脆酥酥的豆子给我们吃!
后园坎上那桃子已透熟了,满姑一天总为我们去偷几次。
爹又不大出来,四叔五叔又从不说话,间或碰到姨婆见了时,也不过笑笑的说:“小娥,你又忘记嚷肚子痛了!真不听讲——芸儿,莫听你满姑的话,吃多了要坏肚子!拿把我,不然晚上又吃不得鸡膊腿了!”
乡里去有场集的地方似乎并不很近,而小小村中除每五 天逢一六赶场外通常都无肉卖。因此,我们几乎天天吃鸡,惟我一人年小,鸡的大腿便时时归我。
我们最爱看又怕看的是溪南头那坝上小碾房的磨石同自动的水车;碾房是五叔在料理。那圆圆的磨石,固定在一株木桩上只是转只是转。五叔象个卖灰的人,满身是糠皮,只是在旋转不息的磨石间拿扫把扫那跑出碾槽外的谷米。他似乎并不着一点忙,磨石走到他跟前时一跳又让过磨石了。我们为他着急又佩服他胆子大。水车也有味,是一些七长八短的竹篙子扎成的。它的用处就是在灌水到比溪身还高的田面。
大的有些比屋子还大,小的也还有一床晒簟大校它们接接连连竖立在大路近旁,为溪沟里急水冲着快快地转动,有些还咿哩咿哩发出怪难听的喊声,由车旁竹筒中运水倒到悬空的枧③上去。它的怕人就是筒子里水间或溢出枧外时,那水便砰的倒到路上了,你稍不措意,衣服便打得透湿。我们远远的立着看行路人抱着头冲过去时那样子好笑。满姑虽只大我四岁,但看惯了,她却敢在下面走来走去。大姐同大姑,则知道那个车子溢出后便是那一个接脚,不消说是不怕水淋了!
只我同大哥二姐,却无论如何不敢去尝试。
人生中留下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他们像沙滩上闪光的珠贝,时不时的让你拣起它,细细的咀嚼品味。
夜,静得可怕,连一丝风也没有。天上几颗稀稀疏疏的星星眨着眼睛,远处几户人家的火已熄,可我还坐在沙发上久久不能入睡。
收音机里放着周华健的《朋友》,这使我想起了离开母校的日子:
雨淅沥地下着,我撑者伞,独自徘徊在校园内。这儿多美啊——花团锦簇,绿树成阴。曾几何时,这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处处都是琅琅书声。可是,不久,我将离开这美丽的校园,踏上去异地的求学路了。
校园里的旗杆,笔直地耸立着,多少个周一的早晨,我们在这里举行升旗仪式。那操场上,留下了我们开校运会时的激情。
教学楼已在眼前,那么亲切,那么熟悉,使我想起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一眨眼,往事已烟消云散。只留下老师那亲切的面容和朋友们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了。难忘啊!难忘,为什么会这么快地到来。
我怀疑:
是阳光在我们不经意的每一个日子里悄悄地来临又默默地里去;是美丽的蒲公英花轻轻地飞起又复悠悠的落下。
母校是我的玻璃壳。
我想永远呆在里面,我知道, 这是空想,不可能。最终,我还是走出了自己的玻璃壳向着阳光凝视未来。那一天我才发现天空和泥土相濡以沫。
就这样,我离开了。
现在我常常沉醉在往事里,但我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那已经是过去,不可能回来了。
第2个回答 2011-12-15
我坐在窗前,望着西边那颗染红一片天空的火球。看着看着不经让我联想到夕阳就像是伤心事儿,一会儿就下山了,而快乐就好比温暖阳光,陪我们走过人生旅途。但生活中有不能缺少它,就像一天如果没有黄昏就觉得不完整。
记得那时候还小,才6岁左右。放学后。没有立马回家,和同学们去广场玩,写作业。那时候正值放风筝时节,广场上有很多人在那放风筝,那一只只“飞鸟”飞得多高,它们迎风飞舞,好像要挣断那根束缚着他的线,广场上到处是一片欢声笑语,有滑冰的,有滑滑板耍特技的,有跳着优美舞蹈的,有骑自行车冲刺的……我们好像被这种气氛所渲染,显得特别兴奋,我们在草坪上打滚,做游戏,太阳公公好像也想和我们玩,他躲在树后,和我们玩躲猫猫,可他却不知道晚霞姐姐早就向我们透露了他的踪迹。我们在草坪上蹦蹦跳跳,玩得筋疲力尽,一个个都像一只只小花猫了,在恋恋不舍的回家了。可我不知道家里还有一场暴风雨在等着我呢。
一进家门,还没把书包放下,妈妈劈头盖脸的审问就砸下来了,这场景让我想起了“大耳朵图图”当中图图的妈妈生气时,头发会竖起来,口中会喷火,这个想法不禁让我抬起头来,望着妈妈的头发。虽然没有看到妈妈的头发竖起来,但却得到了一个意外发现:妈妈原本白皙的脸蛋,不知是因为天气太热了还是因为骂我骂得太激动了,脸蛋迅速升温,变的像一个红苹果似的。渐渐的耳根子也红了,脖子一红了,并且好像变大了,红肿起来,就像一个红烧鸭脖子,嘴巴好一张一合的,好像一只可口的大鸭子,让我垂涎三尺。我傻傻的望着妈妈,嘴里还不停的发出分泌唾液的声音。妈妈看见我还笑以为我不知悔改,反而不骂了,这是转身叹了口气,拿了块搓板让我跪着自己反思就走了。虽然我心里还在埋怨妈妈发那么大的火,但还是不敢自己起来。最后还是奶奶吧我抱回房间的。
那时候一不知道妈妈为什么生那么大的火,但之后也不敢再那么晚回家了。现在回想起来,在有一点理解妈妈当时的心情:女儿没回来,又那么小,不知道去了哪里,只能干着急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不是说“等待时的时间过的最慢了吗”吗?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完全体会妈妈的感受,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早点回家。
生活就像是一个五味瓶,酸甜苦辣一应俱全,但酸、苦总是吸收那个汪汪大海中的一朵浪花,稍纵即逝,但有在礁石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我望向西边夕阳已经下山,只能在天边找到几朵微微潮红的云朵。
记得那时候还小,才6岁左右。放学后。没有立马回家,和同学们去广场玩,写作业。那时候正值放风筝时节,广场上有很多人在那放风筝,那一只只“飞鸟”飞得多高,它们迎风飞舞,好像要挣断那根束缚着他的线,广场上到处是一片欢声笑语,有滑冰的,有滑滑板耍特技的,有跳着优美舞蹈的,有骑自行车冲刺的……我们好像被这种气氛所渲染,显得特别兴奋,我们在草坪上打滚,做游戏,太阳公公好像也想和我们玩,他躲在树后,和我们玩躲猫猫,可他却不知道晚霞姐姐早就向我们透露了他的踪迹。我们在草坪上蹦蹦跳跳,玩得筋疲力尽,一个个都像一只只小花猫了,在恋恋不舍的回家了。可我不知道家里还有一场暴风雨在等着我呢。
一进家门,还没把书包放下,妈妈劈头盖脸的审问就砸下来了,这场景让我想起了“大耳朵图图”当中图图的妈妈生气时,头发会竖起来,口中会喷火,这个想法不禁让我抬起头来,望着妈妈的头发。虽然没有看到妈妈的头发竖起来,但却得到了一个意外发现:妈妈原本白皙的脸蛋,不知是因为天气太热了还是因为骂我骂得太激动了,脸蛋迅速升温,变的像一个红苹果似的。渐渐的耳根子也红了,脖子一红了,并且好像变大了,红肿起来,就像一个红烧鸭脖子,嘴巴好一张一合的,好像一只可口的大鸭子,让我垂涎三尺。我傻傻的望着妈妈,嘴里还不停的发出分泌唾液的声音。妈妈看见我还笑以为我不知悔改,反而不骂了,这是转身叹了口气,拿了块搓板让我跪着自己反思就走了。虽然我心里还在埋怨妈妈发那么大的火,但还是不敢自己起来。最后还是奶奶吧我抱回房间的。
那时候一不知道妈妈为什么生那么大的火,但之后也不敢再那么晚回家了。现在回想起来,在有一点理解妈妈当时的心情:女儿没回来,又那么小,不知道去了哪里,只能干着急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不是说“等待时的时间过的最慢了吗”吗?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完全体会妈妈的感受,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早点回家。
生活就像是一个五味瓶,酸甜苦辣一应俱全,但酸、苦总是吸收那个汪汪大海中的一朵浪花,稍纵即逝,但有在礁石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我望向西边夕阳已经下山,只能在天边找到几朵微微潮红的云朵。
第3个回答 2010-10-24
记忆的碎片零星地洒落四处,因为长时间被遗忘而稍稍有些暗淡。我从新将它们拾起,串成属于我自己的一首歌。
有时候我很羡慕父亲,因为他能把童年时的一幕幕趣事在脑海中重现。
我的脑海中有时也会闪过一些零碎的画面。但我不知道,如果画一幅画,最主要的色彩会是什么。童年时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家里的阳台。好宽阔的阳台,站在那里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最新鲜的绿色。阳光灿烂的时候,仰起头看着太阳,好像阳光在抚摸我的脸。我唱歌跳舞、画画玩球,那种单纯的、没有理由的快乐强烈得似乎于今天的梦幻。
初中就不再算是童年了,因为我们开始为成绩也为梦想和未来奋斗。我爱我的班级,我们一起享受成长岁月中的缕缕快乐,也一起学习,分享彼此心中的梦想。
我今年已经六年级了,关于童年那些美好的记忆,因为太长时间被遗忘而稍微黯淡了。当我将它们重新串起,轻轻吟唱,仿佛一首悦耳动听的歌。
童年时,令我难忘的是在暑假爸爸和我打羽毛球的时光。天刚蒙蒙亮,爸爸就领着我从基础的发球,握拍教起,到后来就教我技巧。我们开始正式积分时,爸爸总是故意将球打歪,让我跑左跑右。轮到我发球时,我也将球故意打歪,把球却轻轻一接,冲我笑,我生气了,就追着爸满院跑……院里传来我们的笑声。
那已经是七年前了。
我在小学了也谱写了许多动人的歌,六年啊,那段花开的季节,各种新奇的东西眼花缭乱,我们一起上课、玩耍,活动……直到下学,我们脸上仍然洋溢着甜美的笑容。
那也是二、三年级的事了。
当我为第一个同学过生日的时候,手里捧着那玲珑的礼物。我仔细的端详着,那是我们纯洁友谊的证明,那盈盈的烛光,慢慢亮起来时,我感觉心里也有一盏灯,慢慢升起,那是我们友谊的长明灯。
当我们开始为成绩、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时,我们已经五年级了,虽然学习很紧张,但我有时间还是会和一群朋友们狂侃,聊生活、聊志向、聊人生、聊游戏、聊学习心得……我们一起分享自己的快乐,那时,我们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我轻轻的吟唱着,那童年的歌,那永远也会不来的歌,那无忧无虑的歌……我想,有一天,我还会回想起今天的歌……
有时候我很羡慕父亲,因为他能把童年时的一幕幕趣事在脑海中重现。
我的脑海中有时也会闪过一些零碎的画面。但我不知道,如果画一幅画,最主要的色彩会是什么。童年时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家里的阳台。好宽阔的阳台,站在那里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最新鲜的绿色。阳光灿烂的时候,仰起头看着太阳,好像阳光在抚摸我的脸。我唱歌跳舞、画画玩球,那种单纯的、没有理由的快乐强烈得似乎于今天的梦幻。
初中就不再算是童年了,因为我们开始为成绩也为梦想和未来奋斗。我爱我的班级,我们一起享受成长岁月中的缕缕快乐,也一起学习,分享彼此心中的梦想。
我今年已经六年级了,关于童年那些美好的记忆,因为太长时间被遗忘而稍微黯淡了。当我将它们重新串起,轻轻吟唱,仿佛一首悦耳动听的歌。
童年时,令我难忘的是在暑假爸爸和我打羽毛球的时光。天刚蒙蒙亮,爸爸就领着我从基础的发球,握拍教起,到后来就教我技巧。我们开始正式积分时,爸爸总是故意将球打歪,让我跑左跑右。轮到我发球时,我也将球故意打歪,把球却轻轻一接,冲我笑,我生气了,就追着爸满院跑……院里传来我们的笑声。
那已经是七年前了。
我在小学了也谱写了许多动人的歌,六年啊,那段花开的季节,各种新奇的东西眼花缭乱,我们一起上课、玩耍,活动……直到下学,我们脸上仍然洋溢着甜美的笑容。
那也是二、三年级的事了。
当我为第一个同学过生日的时候,手里捧着那玲珑的礼物。我仔细的端详着,那是我们纯洁友谊的证明,那盈盈的烛光,慢慢亮起来时,我感觉心里也有一盏灯,慢慢升起,那是我们友谊的长明灯。
当我们开始为成绩、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时,我们已经五年级了,虽然学习很紧张,但我有时间还是会和一群朋友们狂侃,聊生活、聊志向、聊人生、聊游戏、聊学习心得……我们一起分享自己的快乐,那时,我们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我轻轻的吟唱着,那童年的歌,那永远也会不来的歌,那无忧无虑的歌……我想,有一天,我还会回想起今天的歌……
第4个回答 2014-01-16
在我家的衣橱里,挂着一件发黄的衬衫。它原本不是黄色的,是因为存放时间太长的缘故,它才成为一个“老古董”。
这并不是一件普通的衬衫,它凝聚着妈妈对我无尽的爱。每当看见它,我就不由想起那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
那还在我9岁的时候,我们家住在一幢高层住宅的13楼。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发高烧,爸爸又出差在外,情急之下,妈妈只身一人带我去医院看病。到了医院,排队挂号,排队就诊,排队取药,排队穿刺,接着是漫长的打吊针时间。等这一切全部结束,已经是第二天凌晨2点多钟了,妈妈身心疲惫地扶着我,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出租车把我们送到了家门口,望着高高的楼房,我心里直犯愁:电梯停了,我们如何上楼?我们家住那么高的楼层,走楼梯谈何容易?但是妈妈当机立断,说:“我背你上楼。”我坚决不同意,可刚走两步就头晕,只好由妈妈背着。
一开始妈妈并不是很累,步伐还算轻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楼层的增高,我明显地感到妈妈累了,静静的楼道里,妈妈粗粗的喘气声是那样的清晰。不知不觉,妈妈的额头渗出了豆大的汗珠,身上那件白色真丝衬衫也被汗水浸湿了。我知道,那是爸爸新买给妈妈的衬衫,妈妈特别喜欢那件白衬衫,做什么事都很小心,生怕弄脏它。而此时,她已顾及不到自己的衬衫,我便提醒她:“妈妈,您累了,您的新衬衫也湿了,我们歇会儿再走吧!”妈妈不以为然:“没事,回去洗一洗就好了。”我趴在妈妈背上,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妈妈硬是撑着把我背到了13楼,背到了家。
一进家门,妈妈顾不上休息,赶紧忙着烧开水,冲药,并督促我吃药。把我安顿好了之后,她便换下那件衬衫。我以为妈妈会马上把它洗一洗,可是妈妈拿着衬衫看了好长时间,我疑惑地问道:“妈妈,您的衬衫怎么了?打皱了吗?”妈妈笑了笑:“没关系,用电熨斗熨一熨就好了。”
过了几天,我见妈妈一直没穿那件洗净熨好的衬衫,一问才知道,那件衬衫被勾了好多丝,都是我胸前拉链惹的祸。从那以后,虽然妈妈再也没穿过那件衬衫,但我时常见妈妈打开衣橱摸摸它,看得出,妈妈对这件衬衫仍然是爱不释手。
时隔四年,我们也搬了两次家,但那件衬衫依旧挂在我衣橱里珍藏着。每次看见它,我都会想起几年前发生的那件事,都会深深地感受到母爱的伟大,家庭的温馨,亲情的可贵。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这并不是一件普通的衬衫,它凝聚着妈妈对我无尽的爱。每当看见它,我就不由想起那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
那还在我9岁的时候,我们家住在一幢高层住宅的13楼。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发高烧,爸爸又出差在外,情急之下,妈妈只身一人带我去医院看病。到了医院,排队挂号,排队就诊,排队取药,排队穿刺,接着是漫长的打吊针时间。等这一切全部结束,已经是第二天凌晨2点多钟了,妈妈身心疲惫地扶着我,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出租车把我们送到了家门口,望着高高的楼房,我心里直犯愁:电梯停了,我们如何上楼?我们家住那么高的楼层,走楼梯谈何容易?但是妈妈当机立断,说:“我背你上楼。”我坚决不同意,可刚走两步就头晕,只好由妈妈背着。
一开始妈妈并不是很累,步伐还算轻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楼层的增高,我明显地感到妈妈累了,静静的楼道里,妈妈粗粗的喘气声是那样的清晰。不知不觉,妈妈的额头渗出了豆大的汗珠,身上那件白色真丝衬衫也被汗水浸湿了。我知道,那是爸爸新买给妈妈的衬衫,妈妈特别喜欢那件白衬衫,做什么事都很小心,生怕弄脏它。而此时,她已顾及不到自己的衬衫,我便提醒她:“妈妈,您累了,您的新衬衫也湿了,我们歇会儿再走吧!”妈妈不以为然:“没事,回去洗一洗就好了。”我趴在妈妈背上,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妈妈硬是撑着把我背到了13楼,背到了家。
一进家门,妈妈顾不上休息,赶紧忙着烧开水,冲药,并督促我吃药。把我安顿好了之后,她便换下那件衬衫。我以为妈妈会马上把它洗一洗,可是妈妈拿着衬衫看了好长时间,我疑惑地问道:“妈妈,您的衬衫怎么了?打皱了吗?”妈妈笑了笑:“没关系,用电熨斗熨一熨就好了。”
过了几天,我见妈妈一直没穿那件洗净熨好的衬衫,一问才知道,那件衬衫被勾了好多丝,都是我胸前拉链惹的祸。从那以后,虽然妈妈再也没穿过那件衬衫,但我时常见妈妈打开衣橱摸摸它,看得出,妈妈对这件衬衫仍然是爱不释手。
时隔四年,我们也搬了两次家,但那件衬衫依旧挂在我衣橱里珍藏着。每次看见它,我都会想起几年前发生的那件事,都会深深地感受到母爱的伟大,家庭的温馨,亲情的可贵。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