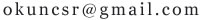第1个回答 2006-01-27
鲁鲁
宗璞
鲁鲁坐在地上,悲凉地叫着。树丛中透出一弯新月,院子的砖地上洒着斑驳的树影
和淡淡的月光。那悲凉的嗥叫声一直穿过院墙,在这山谷的小村中引起一阵阵狗吠。狗
吠声在深夜本来就显得凄惨,而鲁鲁的声音更带着十分的痛苦、绝望,像一把锐利的刀,
把这温暖、平滑的春夜剪碎了。
他大声叫着,声音拖得很长,好像一阵阵哀哭,令人不忍卒听。他那离去了的主人
能听见么?他在哪里呢?鲁鲁觉得自己又处在荒野中了,荒野中什么也没有,他不得不
用嗥叫来证实自己的存在。
院子北端有三间旧房,东头一间还亮着灯,西头一间已经黑了。一会儿,西头这间
响起窸窣的声音,紧接着房门开了,两个孩子穿着本色土布睡衣,蹑手蹑脚走了出来。
10岁左右的姐姐捧着一钵饭,6岁左右的弟弟走近鲁鲁时,便躲在姐姐身后,用力揪住姐
姐的衣服。
“鲁鲁,你吃饭吧,这饭肉多。”姐姐把手里的饭放在鲁鲁身旁。地上原来已摆着
饭盆,一点儿不曾动过。
鲁鲁用悲哀的眼光看着姐姐和弟弟,渐渐安静下来了。他四腿很短,嘴很尖,像只
狐狸;浑身雪白,没有一根杂毛。颈上套着皮项圈,项圈上拴着一根粗绳,系在大树上。
鲁鲁原是一个孤身犹太老人的狗。老人住在村上不远,前天死去了。他的死和他的
生一样,对人对世没有任何影响。后事很快办理完毕。只是这矮脚的白狗守住了房子悲
哭,不肯离去。人们打他,他只是围着房子转。房东灵机一动说:“送给范先生养吧。
这洋狗只合下江人养。”这小村中习惯地把外省人一律称作下江人。于是他给硬拉到范
家,拴在这棵树上,已经三天了。
姐姐弟弟和鲁鲁原来就是朋友。他们有时到犹太老人那里去玩。他们大概是老人唯
二的客人了。老人能用纸叠出整栋的房屋,各房间里还有各种摆设。姐姐弟弟带来的花
玻璃球便是小囡囡,在纸做的房间里滚来滚去。老人还让鲁鲁和他们握手,鲁鲁便伸出
一只前脚,和他们轮流握上好几次。他常跳上老人坐椅的宽大扶手,把他那雪白的头靠
在老人雪白的头旁边,瞅着姐姐和弟弟。他那时的眼光是驯良、温和的,几乎带着笑意。
现在老人不见了,只剩下了鲁鲁,悲凉地嗥叫着的鲁鲁。
“鲁鲁,你就住在我们家。你懂中国话吗?”姐姐温柔地说。“拉拉手吧?”三天
来,这话姐姐已经说了好几遍。鲁鲁总是突然又发出一阵悲号,并不伸出脚来。
但是鲁鲁这次没有哭,只是咻咻地喘着,好像跑了很久。
姐姐伸手去摸他的头,弟弟忙拉住姐姐。鲁鲁咬人是出名的,一点不出声音,专门
咬人的脚后跟。“他不会咬我。”姐姐说,“你咬吗?鲁鲁?”随即把手放在他头上。
鲁鲁一阵颤栗,连毛都微耸起来。老人总是抚摸他,从头摸到脊背。那只大手很有力,
这只小手很轻,但却这样温柔,使鲁鲁安心。他仍咻咻地喘着,向姐姐伸出了前脚。
“好鲁鲁!”姐姐高兴地和他握手。“妈妈!鲁鲁愿意住在我们家了!”
妈妈走出房来,在姐姐介绍下和鲁鲁握手,当然还有弟弟。妈妈轻声责备姐姐说:
“你怎么把肉都给了鲁鲁?我们明天吃什么?”
姐姐垂了头,不说话。弟弟忙说:“明天我们什么也不吃。”
妈妈叹息道:“还有爸爸呢,他太累了。——你们早该睡了,鲁鲁今晚不要叫了,
好么?”
范家人都睡了。只有爸爸仍在煤油灯下著书。鲁鲁几次又想哭一哭,但是望见窗上
几乎是趴在桌上的黑影,便把悲声吞了回去,在喉咙里咕噜着,变成低低的轻吼。
鲁鲁吃饭了。虽然有时还免不了嚎叫,情绪显然已有好转。妈妈和姐姐解掉拴他的
粗绳,但还不时叮嘱弟弟,不要敞开院门。这小院是在一座大庙里,庙里复房别院,房
屋很多,许多城里人迁乡躲空袭,原来空荡荡的古庙,充满了人间烟火。
姐姐还引鲁鲁去见爸爸。她要鲁鲁坐起来,把两只前脚伸在空中拜一拜。“作揖,
作揖!”弟弟叫。鲁鲁的情绪尚未恢复到可以玩耍,但他照做了。“他懂中国话!”姐
弟两人都很高兴。鲁鲁放下前脚,又主动和爸爸握手。平常好像什么都视而不见的爸爸,
把鲁鲁前后打量一番,说:“鲁鲁是什么意思?是意绪文吧?它像只狐狸,应该叫银狐。”
爸爸的话在学校很受重视,在家却说了也等于没说,所以鲁鲁还是叫鲁鲁。
鲁鲁很快也和猫儿菲菲做了朋友。菲菲先很害怕,警惕地躬着身子向后退,一面发
出“吡——”的声音,表示自己也不是好惹的。鲁鲁却无一点敌意。他知道主人家的一
切都应该保护。他伸出前脚给猫,惹得孩子们笑个不停。终于菲菲明白了鲁鲁是朋友,
他们互相嗅鼻子,宣布和平共处。
过了十多天,大家认为鲁鲁可以出门了。他总是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大家都很放心。
有一天,鲁鲁出了门,踌躇了一下,忽然往犹太老人原来的住处走去了。那里锁着门,
他便坐在门口嚎叫起来。还是那样悲凉,那样哀痛。他想起自己的不幸,他的心曾遗失
过了。他努力思索老人的去向。这时几个人围过来。“嚎什么!畜生!”人们向他扔石
头。他站起身跑了,却没有回家,一直下山,向着城里跑去了。
鲁鲁跑着,伸出了舌头,他的腿很短,跑不快。他尽力快跑,因为他有一个谜,他
要去解开这个谜。
乡间路上没有车,也少行人。路两边是各种野生的灌木,自然形成两道绿篱。白狗
像一片飘荡的羽毛,在绿篱间移动。
间或有别的狗跑来,那大都是笨狗,两眼上各有一小块白毛,乡人称为四眼狗。他
们想和鲁鲁嗅鼻子,或打一架,鲁鲁都躲开了。他只是拼命地跑,跑着去解开一个谜。
他跑了大半天,黄昏时进了城,在一座旧洋房前停住了。
门关着,他就坐在门外等,不时发出长长的哀叫。这里是犹太老人和鲁鲁的旧住处。
主人是回到这里来了罢?怎么还听不见鲁鲁的哭声呢?有人推开窗户,有人走出来看,
但都没有那苍然的白发。人们说:“这是那洋老头的白狗。”“怎么跑回来了!”却没
有人问一问洋老头的究竟。
鲁鲁在门口蹲了两天两夜。人们气愤起来,下决心处理他了。第三天早上,几个拿
着绳索棍棒的人朝他走来。一个人叫他:“鲁鲁!”一面丢来一根骨头。他不动。他很
饿,又渴,又想睡。他想起那淡黄的土布衣裳,那温柔的小手拿着的饭盆。他最后看着
屋门,希望在这一瞬间老人会走出来。但是没有。他跳起身,向人们腿间冲过去,向城
外跑去了。
他得到的谜底是再也见不到老人了。他不知道那老人的去处,是每个人,连他鲁鲁,
终究都要去的。
妈妈和姐姐都抱怨弟弟,说是弟弟把鲁鲁放了出去。弟弟表现出男子汉的风度,自
管在大树下玩。他不说话,可心里很难过。傻鲁鲁!怎么能离开爱自己的人呢!妈妈走
过来,把鲁鲁的饭盆、水盆撂在一起,预备扔掉。已经第三天黄昏了,不会回来了。可
是姐姐又把盆子摆开。刚才三天呢,鲁鲁会回来的。
这时有什么东西在院门上抓挠。妈妈小心地走到门前听。
姐姐忽然叫起来冲过去开了门。“鲁鲁!”果然是鲁鲁,正坐在门口咻咻地望着他
们。姐姐弯身抱着他的头,他舐姐姐的手。“鲁鲁!”弟弟也跑过去欢迎。他也舐弟弟
的手,小心地绕着弟弟跑了两圈,留神不把他撞倒。他蹭蹭妈妈,给她作揖,但是不舐
她,因为知道她不喜欢。鲁鲁还懂得进屋去找爸爸,钻在书桌下蹭爸爸的腿。那晚全家
都高兴极了。连菲菲都对鲁鲁表示欢迎,怯怯地走上来和鲁鲁嗅鼻子。
从此鲁鲁正式成为这个家的一员了。他忠实地看家,严格地听从命令,除了常在夜
晚出门,简直无懈可击。他会超出狗的业务范围,帮菲菲捉老鼠。老鼠钻在阴沟里,菲
菲着急地跑来跑去,怕它逃了,鲁鲁便去守住一头,菲菲守住另一头。鲁鲁把尖嘴伸进
盖着石板的阴沟,低声吼着。老鼠果然从另一头溜出来,落在菲菲的爪下。由此爸爸考
证说,鲁鲁本是一条猎狗,至少是猎狗的后裔。
姐姐和弟弟到山下去买豆腐,鲁鲁总是跟着。他很愿意咬住篮子,但是他太矮了,
只好空身跑。他常常跑在前面,不见了,然后忽然从草丛中冲出来。他总是及时收住脚
步,从未撞倒过孩子。卖豆腐的老人有时扔给鲁鲁一块肉骨头,鲁鲁便给他作揖,引得
老人哈哈大笑。姐姐弟弟有时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鲁鲁便耐心地等在一边。似乎他
对那游戏也感兴趣。
村边有一条晶莹的小溪,岸上有些闲花野草,浓密的柳荫沿着河堤铺开去。他们三
个常到这里,在柳荫下跑来跑去,或坐着讲故事,住在邻省T市的唐伯伯,是爸爸的好友,
一次到范家来,看见这幅画面,曾慨叹道他若是画家,一定画出这绿柳下、小河旁的两
个穿土布衣裳的孩子和一条白狗,好抚一抚战争的创伤。唐伯伯还说鲁鲁出自狗中名门
世族。但范家人并不关心这个。鲁鲁自己也毫无兴趣。
其实鲁鲁并不总是好听故事。他常跳到溪水里游泳。他是天生的游泳家,尖尖的嘴
总是露在绿波面上。妈妈可不赞成他们到水边去。每次鲁鲁毛湿了,便责备他:“你又
带他们到哪儿去了!他们掉到水里怎么办!”她说着,鲁鲁抿着耳朵听着,好像他是那
最大的孩子。
虽然妈妈责备,因姐姐弟弟保证决不下水,他们还是可以常到溪边去玩,不算是错
误。一次鲁鲁真犯了错误。爸爸进城上课去了,他一周照例有三天在城里。妈妈到邻家
守护一个病孩。妈妈上过两年护士学校,在这山村里义不容辞地成为医生。她临出门前
一再对鲁鲁说:“要是家里没有你,我不能把孩子扔在家。有你我就放心了。我把他们
两个交给你,行吗?”鲁鲁懂事地听着,摇着尾巴。“你夜里可不能出去,就在房里睡,
行吗?”鲁鲁觉得妈妈的手抚在背上的力量,他对于信任是从不辜负的。
鲁鲁常在夜里到附近山中去打活食。这里山林茂密,野兔、松鼠很多。他跑了一夜
回来,总是精神抖擞,毛皮发出润泽的光。那是野性的、生命的光辉。活食辅助了范家
的霉红米饭,那米是当作工资发下来的,霉味胜过粮食的香味。鲁鲁对米中一把把抓得
起来的肉虫和米饭都不感兴趣。但这几天,他寸步不离地跟着姐姐弟弟,晚上也不出去。
如果第四天不是赶集,他们三个到集上去了的话,鲁鲁秉赋的狗的弱点也还不会暴露。
这山村下面的大路是附近几个村赶集的地方,七天两头赶,每次都十分热闹。鸡鱼
肉蛋,盆盆罐罐,还有鸟儿猫儿,都有卖的。姐姐来买松毛,那是引火用的,一辫辫编
起来的松针,买完了便拉着弟弟的手快走。对那些明知没有钱买的好东西,根本不看。
弟弟也支持她,加劲地迈着小腿。走着走着,发现鲁鲁不见了。“鲁鲁。”姐姐小声叫。
这时听见卖肉的一带许多人又笑又嚷:“白狗耍把戏!来!翻个筋斗!会吗?”他们连
忙挤过去,见鲁鲁正坐着作揖,要肉吃。
“鲁鲁!”姐姐厉声叫道。鲁鲁忙站起来跑到姐姐身边,仍回头看挂着的牛肉。那
里还挂着猪肉、羊肉、驴肉、马肉。最吸引鲁鲁的是牛肉。他多想吃!那鲜嫩的、带血
的牛肉,他以前天天吃的。尤其是那生肉的气味,使他想起追捕、厮杀、自由、胜利,
想起没有尽头的林莽和山野,使他晕头转向。
卖肉人认得姐姐弟弟,笑着说:“这洋狗到范先生家了。”
说着顺手割下一块,往姐姐篮里塞。村民都很同情这些穷酸教书先生,听说一个个
学问不小,可养条狗都没本事。
姐姐怎么也不肯要,拉着弟弟就走。这时鲁鲁从旁猛地一窜,叼了那块肉,撒开四
条短腿,跑了。
“鲁鲁!”姐姐提着装满松毛的大篮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追,弟弟也跟着跑。人们
一阵哄笑,那是善意的、好玩的哄笑,但听起来并不舒服。
等他们跑到家,鲁鲁正把肉摆在面前,坐定了看着。他讨好地迎着姐姐,一脸奉承,
分明是要姐姐批准他吃那块肉。
姐姐扔了篮子,双手捂着脸,哭了。
弟弟着急地给她递手绢,又跺脚训斥鲁鲁:“你要吃肉,你走吧!上山里去,上别
人家去!”鲁鲁也着急地绕着姐姐转,伸出前脚轻轻抓她,用头蹭她,对那块肉没有再
看一眼。
姐姐把肉埋在院中树下。后来妈妈还了肉钱,也没有责备鲁鲁。因为事情过了,责
备他是没有用的。鲁鲁却竟渐渐习惯少肉的生活,隔几天才夜猎一次。和荒野的搏斗比
起来,他似乎更依恋人所给予的温暖。爸爸说,原来箪食瓢饮,狗也能做到的。
鲁鲁还犯过一回严重错误,那是无可挽回的。他和菲菲是好朋友,常闹着玩。他常
把菲菲一拱,让她连翻几个身,菲菲会立刻又扑上来,和他打闹。冷天时菲菲会离开自
己的窝,挨着鲁鲁睡。这一年菲菲生了一窝小猫,对鲁鲁凶起来。鲁鲁不识趣,还伸嘴
到她窝里,嗅嗅她的小猫。菲菲一掌打在鲁鲁鼻子上,把鼻子抓破了。鲁鲁有些生气,
一半也是闹着玩,把菲菲轻轻咬住,往门外一扔。不料菲菲惨叫一声,在地上扑腾几下,
就断了气。鲁鲁慌了,过去用鼻子拱她,把她连翻几个身,但她不像往日一样再扑上来,
她再也不能动了。
妈妈走出房间看时,见鲁鲁坐在菲菲旁边,唧唧咛咛地叫。他见了妈妈,先是愣了
一下,随即趴在地下,腹部着地,一点一点往妈妈脚边蹭。一面偷着翻眼看妈妈脸色。
妈妈好不生气:“你这只狗!不知轻重!一窝小猫怎么办!你给养着!”
妈妈把猫窝杵在鲁鲁面前。鲁鲁吓得又往后蹭,还是不敢站起来。姐姐弟弟都为鲁
鲁说情,妈妈执意要打。鲁鲁慢慢退进了里屋。大家都以为他躲打,跟进去看,见他蹭
到爸爸脚边,用后腿站起来向爸爸作揖,一脸可怜相,原来是求爸爸说情。爸爸摸摸他
的头,看看妈妈的脸色,乖觉地说:“少打几下,行么?”妈妈倒是破天荒准了情,说
决不多打,不过鲁鲁是狗,不打几下,不会记住教训,她只打了鲁鲁三下,每下都很重,
鲁鲁哼哼唧唧地小哭,可是服贴地趴着受打。房门、院门都开着,他没有一点逃走的意
思,连爸爸也离开书桌看着鲁鲁说:“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看来你大杖也不会走的。”
鲁鲁受过杖,便趴在自己窝里。妈妈说他要忏悔,不准姐姐弟弟理他。姐姐很为菲
菲和小猫难受,也为鲁鲁难受。她知道鲁鲁不是故意的。晚饭没有鲁鲁的份,姐姐悄悄
拿了水和剩饭给他。鲁鲁呜咽着舐她的手。
和鲁鲁的错误比起来,他的功绩要大得多了。一天下午,有一家请妈妈去看一位孕
妇。她本来约好往一个较远的村庄去给一个病人送药,这任务便落在姐姐身上。姐姐高
兴地把药装好。弟弟和鲁鲁都要跟去,因为那段路远,弟弟又不大舒服,遂决定鲁鲁陪
弟弟在家。妈妈和姐姐一起出门,分道走了。鲁鲁和弟弟送到庙门口,看着姐姐的土布
衣裳的淡黄色消失在绿丛中。
妈妈到那孕妇家,才知她就要临盆。便等着料理,直到婴儿呱呱坠地,一切停妥才
走。到家已是夜里10点多了,只见家中冷清清点着一盏煤油灯。鲁鲁哼唧着在屋里转来
转去。
弟弟一见妈妈便扑上来哭了。“姐姐,”他说,“姐姐还没回家——。”
爸爸不在家。妈妈定了定神,转身到最近的同事家,叫起那家的教书先生,又叫起
房东,又叫起他们认为该叫的人。
人们焦急地准备着灯笼火把。这时鲁鲁仍在妈妈身边哼着,还踩在妈妈脚上,引她
注意。弟弟忽然说:“鲁鲁要去找姐姐。”
妈妈一愣,说:“快去!鲁鲁,快去!”鲁鲁像离弦的箭一样,一下窜出好远,很
快就被黑暗吞没了。
鲁鲁用力跑着。姐姐带着的草药味,和着姐姐本身的气味,形成淡淡的芳香,指引
他向前跑。一切对他都不存在。黑夜,树木,路旁汩汩的流水,都是那样虚幻,只有姐
姐的缥缈的气味,是最实在的。可他居然一度离开那气味,不向前过桥,却抄近下河,
游过溪水,又插上小路。那气味又有了,鲁鲁一点没有为自己的聪明得意,只是认真地
跑着,一直跑进了坐落在另一个山谷的村庄。
村里一片漆黑,人们都睡了。他跑到一家门前,着急地挠门。气味断了,姐姐分明
走进门去了。他挠了几下,绕着院墙跑到后门,忽然又闻见那气味,只没有了草药。姐
姐是从后门出来,走过村子,上了通向山里的蜿蜒小路。鲁鲁一刻也不敢停,伸长舌头,
努力地跑。树更多了,草更深了。植物在夜间的浓烈气息使得鲁鲁迷惑,他仔细辨认那
熟悉的气味,在草丛中追寻。草莽中的小生物吓得四面奔逃。鲁鲁无暇注意那是什么。
那时便有最鲜美的活食在他嘴下,他也不会碰一碰的。
终于在一棵树下,一块大石旁,鲁鲁看见了那土布衣裳的淡黄色。姐姐靠在大石上
睡着了。鲁鲁喜欢得横窜竖跳,自己乐了一阵,然后坐在地上,仔细看着姐姐,然后又
绕她走了两圈,才伸前爪轻轻推她。
姐姐醒了。她惊讶地四处看着,又见一弯新月,照着黑黝黝的树木、草莽、山和石。
她恍然地说:“鲁鲁,该回家了。
妈妈急坏了。”
她想抓住鲁鲁的项圈,但她已经太高了,遂脱下外衣,拴在项圈上。鲁鲁乖乖地引
路,一路不时回头看姐姐,发出呜呜的高兴的声音。
“你知道么?鲁鲁,我只想试试,能不能也做一个吕克大梦。”①姐姐和他推心置
腹地说。“没想到这么晚了。不过离20年还差得远。” ①吕克大梦,指美国前期浪漫主义作家华盛顿·欧文(1783—1859)的著名作品。
小说中写一个农民瑞·普凡·温克尔上山打猎,遇见一群玩九柱戏的人,温克尔喝了他
们的酒,沉睡了20年,醒来见城廓全非。——作者原注
他们走到堤上时,看见远处树丛间一闪一闪的亮光。不一会儿人声沸腾,是找姐姐
的队伍来了。他们先看见雪白的鲁鲁,好几个声音叫他,问他,就像他会回答似的。他
的回答是把姐姐越引越近,姐姐投在妈妈怀里时,他担心地坐在地上看。他怕姐姐要受
罚,因为谁让妈妈着急生气,都要受罚的,可是妈妈只拥着她,温和地说:“你不怕醒
来就见不着妈妈了么?”“我快睡着时,忽然害怕了,怕一睡20年。可是已经止不住,
糊里糊涂睡着了。”人们一阵大笑,忙着议论,那山上有狼,多危险!谁也不再理鲁鲁
了。
爸爸从城里回来后,特地找鲁鲁握手,谢谢他。鲁鲁却已经不大记得自己的功绩,
只是这几天饭里居然放了牛肉,使他很高兴。
又过些时,姐姐弟弟都在附近学校上学了。那也是城里迁来的。姐姐上中学,弟弟
上小学。鲁鲁每天在庙门口看着他们走远,又在山坡下等他们回来。他还是在草丛里跑,
跟着去买豆腐。又有一阵姐姐经常生病,每次她躺在床上,鲁鲁都很不安,好像要遇到
什么危险似的。卖豆腐老人特地来说,姐姐多半得罪了山灵,应该到鲁鲁找到姐姐的地
方去上供。爸爸妈妈向他道谢,却说什么营养不良,肺结核。鲁鲁不懂他们的话,如果
懂得,他一定会代姐姐去拜访山灵的。
好在姐姐多半还是像常人一样活动,鲁鲁的不安总是短暂的。日子如同村边小溪潺
潺的清流,不慌不忙,自得其乐。
若是鲁鲁这时病逝,他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狗了。但是他很健康,雪白的长毛亮闪
闪的,身体的线条十分挺秀。没人知道鲁鲁的年纪,却可以看出,他离衰老还远。
村边小溪静静地流,不知大江大河里怎样掀着巨浪。终于有一天,日本投降的消息
传到这小村,整个小村沸腾了,赛过任何一次赶集。人们以为熬出头了。爸爸把妈妈一
下子紧紧抱住,使得另外三个成员都很惊讶。爸爸流着眼泪说:“你辛苦了,你太辛苦
了。”妈妈呜呜地哭起来。爸爸又把姐姐弟弟也揽了过来,四人抱在一起。鲁鲁连忙也
把头往缝隙里贴。
这个经历了无数风雨艰辛的亲爱的小家庭,怎么能少得了鲁鲁呢。
“回北平去!”弟弟得意地说。姐姐蹲下去抱住鲁鲁的头。
她已经是一个窈窕的少女了。他们决没有想到鲁鲁是不能去的。
范家已经家徒四壁,只有一双宝贝儿女和爸爸几年来在煤油灯下写的手稿。他们要
走很方便。可是还有鲁鲁呢。鲁鲁留在这里,会发疯的。最后决定带他到T市,送给爱狗
的唐伯伯。
经过一阵忙乱,一家人上了汽车。在那一阵忙乱中,鲁鲁总是很不安,夜里无休止
地做梦。他梦见爸爸、妈妈、姐姐和弟弟都走了。只剩下他,孤零零在荒野中奔跑。而
且什么气味也闻不见,这使他又害怕又伤心。他在梦里大声哭,妈妈就过来推醒他,然
后和爸爸讨论:“狗也会做梦么?”“我想——至少鲁鲁会的。”
鲁鲁居然也上了车。他高兴极了,安心极了。他特别讨好地在妈妈身上蹭。妈妈叫
起来:“去!去!车本来就够颠的了。”鲁鲁连忙钻在姐姐弟弟中间,三个伙伴一起随
着车的颠簸摇动,看着青山慢慢往后移;路在前面忽然断了,转过山腰,又显现出来,
总是无限地伸展着——。
上路第二天,姐姐就病了。爸爸说她无福消受这一段风景。她在车上躺着,到旅店
也躺着。鲁鲁的不安超过了她任何一次病时。他一刻不离地挤在她脚前。眼光惊恐而凄
凉。这使妈妈觉得不吉利,很不高兴。“我们的孩子不至于怎样。你不用担心,鲁鲁。”
她把他赶出房门,他就守在门口。弟弟很同情他,向他详细说明情况,说回到北平可以
治好姐姐的病,说交通不便,不能带鲁鲁去,自己和姐姐都很伤心;还说唐伯伯是最好
的人,一定会和鲁鲁要好。鲁鲁不懂这么多话,但是安静地听着,不时舐舐弟弟的手。
T市附近,有一个著名的大瀑布。10里外便听得水声隆隆。车经这里,人们都下车到
观瀑亭上去看。姐姐发着烧,还执意要下车。于是爸爸在左,妈妈在右,鲁鲁在前,弟
弟在后,向亭上走去。急遽的水流从几十丈的绝壁跌落下来,在青山翠峦中形成一个小
湖,水气迷蒙,一直飘到观瀑亭上。姐姐觉得那白花花的厚重的半透明的水幔和雷鸣般
的轰响仿佛离她很远。她努力想走近些看,但它们越来越远,她什么也看不见了,倚在
爸爸肩上晕了过去。
从此鲁鲁再也没有看见姐姐。没有几天,他就显得憔悴,白毛失去了光泽。唐家的
狗饭一律有牛肉,他却嗅嗅便走开,不管弟弟怎样哄劝。这时的弟弟已经比姐姐高,是
撞不倒的了。一天,爸爸和弟弟带他上街,在一座大房子前站了半天。
鲁鲁很讨厌那房子的气味,哼哼唧唧要走。他若知道姐姐正在楼上一扇窗里最后一
次看他,他会情愿在那里站一辈子,永不离开。
范家人走时,唐伯伯叫人把鲁鲁关在花园里。他们到医院接了姐姐,一直上了飞机。
姐姐和弟弟为了不能再见鲁鲁,一起哭了一场。他们听不见鲁鲁在花园里发出的撕裂了
的、变了声的嗥叫,他们看不见鲁鲁因为一次又一次想挣脱绳索,磨掉了毛的脖子。他
们飞得高高的,遗落了儿时的伙伴。
鲁鲁发疯似地寻找主人,时间持续得这样久,以致唐伯伯以为他真要疯了。唐伯伯
总是试着和他握手,同情地、客气地说:“请你住在我家,这不是已经说好了么,鲁鲁。”
鲁鲁终于渐渐平静下来。有一天,又不见了。过了半年,大家早以为他已离开这世
界,他竟又回到唐家。他瘦多了,完全变成一只灰狗,身上好几处没有了毛,露出粉红
的皮肤;颈上的皮项圈不见了,替代物是原来那一省的狗牌。可见他曾回去,又一次去
寻找谜底。若是鲁鲁会写字,大概会写出他怎样戴露披霜,登山涉水;怎样被打被拴,
而每一次都能逃走,继续他千里迢迢的旅程;怎样重见到小山上的古庙,却寻不到原住
在那里的主人。也许他什么也写不出,因为他并不注意外界的凄楚,他只是要去解开内
心的一个谜。他去了,又历尽辛苦回来,为了不违反主人的安排。当然,他究竟怎样想
的,没有人,也没有狗能够懂得。
唐家人久闻鲁鲁的事迹,却不知他有观赏瀑布的癖好。他常常跑出城去,坐在大瀑
布前,久久地望着那跌宕跳荡、白帐幔似的落水,发出悲凉的、撞人心弦的哀号。
宗璞
鲁鲁坐在地上,悲凉地叫着。树丛中透出一弯新月,院子的砖地上洒着斑驳的树影
和淡淡的月光。那悲凉的嗥叫声一直穿过院墙,在这山谷的小村中引起一阵阵狗吠。狗
吠声在深夜本来就显得凄惨,而鲁鲁的声音更带着十分的痛苦、绝望,像一把锐利的刀,
把这温暖、平滑的春夜剪碎了。
他大声叫着,声音拖得很长,好像一阵阵哀哭,令人不忍卒听。他那离去了的主人
能听见么?他在哪里呢?鲁鲁觉得自己又处在荒野中了,荒野中什么也没有,他不得不
用嗥叫来证实自己的存在。
院子北端有三间旧房,东头一间还亮着灯,西头一间已经黑了。一会儿,西头这间
响起窸窣的声音,紧接着房门开了,两个孩子穿着本色土布睡衣,蹑手蹑脚走了出来。
10岁左右的姐姐捧着一钵饭,6岁左右的弟弟走近鲁鲁时,便躲在姐姐身后,用力揪住姐
姐的衣服。
“鲁鲁,你吃饭吧,这饭肉多。”姐姐把手里的饭放在鲁鲁身旁。地上原来已摆着
饭盆,一点儿不曾动过。
鲁鲁用悲哀的眼光看着姐姐和弟弟,渐渐安静下来了。他四腿很短,嘴很尖,像只
狐狸;浑身雪白,没有一根杂毛。颈上套着皮项圈,项圈上拴着一根粗绳,系在大树上。
鲁鲁原是一个孤身犹太老人的狗。老人住在村上不远,前天死去了。他的死和他的
生一样,对人对世没有任何影响。后事很快办理完毕。只是这矮脚的白狗守住了房子悲
哭,不肯离去。人们打他,他只是围着房子转。房东灵机一动说:“送给范先生养吧。
这洋狗只合下江人养。”这小村中习惯地把外省人一律称作下江人。于是他给硬拉到范
家,拴在这棵树上,已经三天了。
姐姐弟弟和鲁鲁原来就是朋友。他们有时到犹太老人那里去玩。他们大概是老人唯
二的客人了。老人能用纸叠出整栋的房屋,各房间里还有各种摆设。姐姐弟弟带来的花
玻璃球便是小囡囡,在纸做的房间里滚来滚去。老人还让鲁鲁和他们握手,鲁鲁便伸出
一只前脚,和他们轮流握上好几次。他常跳上老人坐椅的宽大扶手,把他那雪白的头靠
在老人雪白的头旁边,瞅着姐姐和弟弟。他那时的眼光是驯良、温和的,几乎带着笑意。
现在老人不见了,只剩下了鲁鲁,悲凉地嗥叫着的鲁鲁。
“鲁鲁,你就住在我们家。你懂中国话吗?”姐姐温柔地说。“拉拉手吧?”三天
来,这话姐姐已经说了好几遍。鲁鲁总是突然又发出一阵悲号,并不伸出脚来。
但是鲁鲁这次没有哭,只是咻咻地喘着,好像跑了很久。
姐姐伸手去摸他的头,弟弟忙拉住姐姐。鲁鲁咬人是出名的,一点不出声音,专门
咬人的脚后跟。“他不会咬我。”姐姐说,“你咬吗?鲁鲁?”随即把手放在他头上。
鲁鲁一阵颤栗,连毛都微耸起来。老人总是抚摸他,从头摸到脊背。那只大手很有力,
这只小手很轻,但却这样温柔,使鲁鲁安心。他仍咻咻地喘着,向姐姐伸出了前脚。
“好鲁鲁!”姐姐高兴地和他握手。“妈妈!鲁鲁愿意住在我们家了!”
妈妈走出房来,在姐姐介绍下和鲁鲁握手,当然还有弟弟。妈妈轻声责备姐姐说:
“你怎么把肉都给了鲁鲁?我们明天吃什么?”
姐姐垂了头,不说话。弟弟忙说:“明天我们什么也不吃。”
妈妈叹息道:“还有爸爸呢,他太累了。——你们早该睡了,鲁鲁今晚不要叫了,
好么?”
范家人都睡了。只有爸爸仍在煤油灯下著书。鲁鲁几次又想哭一哭,但是望见窗上
几乎是趴在桌上的黑影,便把悲声吞了回去,在喉咙里咕噜着,变成低低的轻吼。
鲁鲁吃饭了。虽然有时还免不了嚎叫,情绪显然已有好转。妈妈和姐姐解掉拴他的
粗绳,但还不时叮嘱弟弟,不要敞开院门。这小院是在一座大庙里,庙里复房别院,房
屋很多,许多城里人迁乡躲空袭,原来空荡荡的古庙,充满了人间烟火。
姐姐还引鲁鲁去见爸爸。她要鲁鲁坐起来,把两只前脚伸在空中拜一拜。“作揖,
作揖!”弟弟叫。鲁鲁的情绪尚未恢复到可以玩耍,但他照做了。“他懂中国话!”姐
弟两人都很高兴。鲁鲁放下前脚,又主动和爸爸握手。平常好像什么都视而不见的爸爸,
把鲁鲁前后打量一番,说:“鲁鲁是什么意思?是意绪文吧?它像只狐狸,应该叫银狐。”
爸爸的话在学校很受重视,在家却说了也等于没说,所以鲁鲁还是叫鲁鲁。
鲁鲁很快也和猫儿菲菲做了朋友。菲菲先很害怕,警惕地躬着身子向后退,一面发
出“吡——”的声音,表示自己也不是好惹的。鲁鲁却无一点敌意。他知道主人家的一
切都应该保护。他伸出前脚给猫,惹得孩子们笑个不停。终于菲菲明白了鲁鲁是朋友,
他们互相嗅鼻子,宣布和平共处。
过了十多天,大家认为鲁鲁可以出门了。他总是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大家都很放心。
有一天,鲁鲁出了门,踌躇了一下,忽然往犹太老人原来的住处走去了。那里锁着门,
他便坐在门口嚎叫起来。还是那样悲凉,那样哀痛。他想起自己的不幸,他的心曾遗失
过了。他努力思索老人的去向。这时几个人围过来。“嚎什么!畜生!”人们向他扔石
头。他站起身跑了,却没有回家,一直下山,向着城里跑去了。
鲁鲁跑着,伸出了舌头,他的腿很短,跑不快。他尽力快跑,因为他有一个谜,他
要去解开这个谜。
乡间路上没有车,也少行人。路两边是各种野生的灌木,自然形成两道绿篱。白狗
像一片飘荡的羽毛,在绿篱间移动。
间或有别的狗跑来,那大都是笨狗,两眼上各有一小块白毛,乡人称为四眼狗。他
们想和鲁鲁嗅鼻子,或打一架,鲁鲁都躲开了。他只是拼命地跑,跑着去解开一个谜。
他跑了大半天,黄昏时进了城,在一座旧洋房前停住了。
门关着,他就坐在门外等,不时发出长长的哀叫。这里是犹太老人和鲁鲁的旧住处。
主人是回到这里来了罢?怎么还听不见鲁鲁的哭声呢?有人推开窗户,有人走出来看,
但都没有那苍然的白发。人们说:“这是那洋老头的白狗。”“怎么跑回来了!”却没
有人问一问洋老头的究竟。
鲁鲁在门口蹲了两天两夜。人们气愤起来,下决心处理他了。第三天早上,几个拿
着绳索棍棒的人朝他走来。一个人叫他:“鲁鲁!”一面丢来一根骨头。他不动。他很
饿,又渴,又想睡。他想起那淡黄的土布衣裳,那温柔的小手拿着的饭盆。他最后看着
屋门,希望在这一瞬间老人会走出来。但是没有。他跳起身,向人们腿间冲过去,向城
外跑去了。
他得到的谜底是再也见不到老人了。他不知道那老人的去处,是每个人,连他鲁鲁,
终究都要去的。
妈妈和姐姐都抱怨弟弟,说是弟弟把鲁鲁放了出去。弟弟表现出男子汉的风度,自
管在大树下玩。他不说话,可心里很难过。傻鲁鲁!怎么能离开爱自己的人呢!妈妈走
过来,把鲁鲁的饭盆、水盆撂在一起,预备扔掉。已经第三天黄昏了,不会回来了。可
是姐姐又把盆子摆开。刚才三天呢,鲁鲁会回来的。
这时有什么东西在院门上抓挠。妈妈小心地走到门前听。
姐姐忽然叫起来冲过去开了门。“鲁鲁!”果然是鲁鲁,正坐在门口咻咻地望着他
们。姐姐弯身抱着他的头,他舐姐姐的手。“鲁鲁!”弟弟也跑过去欢迎。他也舐弟弟
的手,小心地绕着弟弟跑了两圈,留神不把他撞倒。他蹭蹭妈妈,给她作揖,但是不舐
她,因为知道她不喜欢。鲁鲁还懂得进屋去找爸爸,钻在书桌下蹭爸爸的腿。那晚全家
都高兴极了。连菲菲都对鲁鲁表示欢迎,怯怯地走上来和鲁鲁嗅鼻子。
从此鲁鲁正式成为这个家的一员了。他忠实地看家,严格地听从命令,除了常在夜
晚出门,简直无懈可击。他会超出狗的业务范围,帮菲菲捉老鼠。老鼠钻在阴沟里,菲
菲着急地跑来跑去,怕它逃了,鲁鲁便去守住一头,菲菲守住另一头。鲁鲁把尖嘴伸进
盖着石板的阴沟,低声吼着。老鼠果然从另一头溜出来,落在菲菲的爪下。由此爸爸考
证说,鲁鲁本是一条猎狗,至少是猎狗的后裔。
姐姐和弟弟到山下去买豆腐,鲁鲁总是跟着。他很愿意咬住篮子,但是他太矮了,
只好空身跑。他常常跑在前面,不见了,然后忽然从草丛中冲出来。他总是及时收住脚
步,从未撞倒过孩子。卖豆腐的老人有时扔给鲁鲁一块肉骨头,鲁鲁便给他作揖,引得
老人哈哈大笑。姐姐弟弟有时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鲁鲁便耐心地等在一边。似乎他
对那游戏也感兴趣。
村边有一条晶莹的小溪,岸上有些闲花野草,浓密的柳荫沿着河堤铺开去。他们三
个常到这里,在柳荫下跑来跑去,或坐着讲故事,住在邻省T市的唐伯伯,是爸爸的好友,
一次到范家来,看见这幅画面,曾慨叹道他若是画家,一定画出这绿柳下、小河旁的两
个穿土布衣裳的孩子和一条白狗,好抚一抚战争的创伤。唐伯伯还说鲁鲁出自狗中名门
世族。但范家人并不关心这个。鲁鲁自己也毫无兴趣。
其实鲁鲁并不总是好听故事。他常跳到溪水里游泳。他是天生的游泳家,尖尖的嘴
总是露在绿波面上。妈妈可不赞成他们到水边去。每次鲁鲁毛湿了,便责备他:“你又
带他们到哪儿去了!他们掉到水里怎么办!”她说着,鲁鲁抿着耳朵听着,好像他是那
最大的孩子。
虽然妈妈责备,因姐姐弟弟保证决不下水,他们还是可以常到溪边去玩,不算是错
误。一次鲁鲁真犯了错误。爸爸进城上课去了,他一周照例有三天在城里。妈妈到邻家
守护一个病孩。妈妈上过两年护士学校,在这山村里义不容辞地成为医生。她临出门前
一再对鲁鲁说:“要是家里没有你,我不能把孩子扔在家。有你我就放心了。我把他们
两个交给你,行吗?”鲁鲁懂事地听着,摇着尾巴。“你夜里可不能出去,就在房里睡,
行吗?”鲁鲁觉得妈妈的手抚在背上的力量,他对于信任是从不辜负的。
鲁鲁常在夜里到附近山中去打活食。这里山林茂密,野兔、松鼠很多。他跑了一夜
回来,总是精神抖擞,毛皮发出润泽的光。那是野性的、生命的光辉。活食辅助了范家
的霉红米饭,那米是当作工资发下来的,霉味胜过粮食的香味。鲁鲁对米中一把把抓得
起来的肉虫和米饭都不感兴趣。但这几天,他寸步不离地跟着姐姐弟弟,晚上也不出去。
如果第四天不是赶集,他们三个到集上去了的话,鲁鲁秉赋的狗的弱点也还不会暴露。
这山村下面的大路是附近几个村赶集的地方,七天两头赶,每次都十分热闹。鸡鱼
肉蛋,盆盆罐罐,还有鸟儿猫儿,都有卖的。姐姐来买松毛,那是引火用的,一辫辫编
起来的松针,买完了便拉着弟弟的手快走。对那些明知没有钱买的好东西,根本不看。
弟弟也支持她,加劲地迈着小腿。走着走着,发现鲁鲁不见了。“鲁鲁。”姐姐小声叫。
这时听见卖肉的一带许多人又笑又嚷:“白狗耍把戏!来!翻个筋斗!会吗?”他们连
忙挤过去,见鲁鲁正坐着作揖,要肉吃。
“鲁鲁!”姐姐厉声叫道。鲁鲁忙站起来跑到姐姐身边,仍回头看挂着的牛肉。那
里还挂着猪肉、羊肉、驴肉、马肉。最吸引鲁鲁的是牛肉。他多想吃!那鲜嫩的、带血
的牛肉,他以前天天吃的。尤其是那生肉的气味,使他想起追捕、厮杀、自由、胜利,
想起没有尽头的林莽和山野,使他晕头转向。
卖肉人认得姐姐弟弟,笑着说:“这洋狗到范先生家了。”
说着顺手割下一块,往姐姐篮里塞。村民都很同情这些穷酸教书先生,听说一个个
学问不小,可养条狗都没本事。
姐姐怎么也不肯要,拉着弟弟就走。这时鲁鲁从旁猛地一窜,叼了那块肉,撒开四
条短腿,跑了。
“鲁鲁!”姐姐提着装满松毛的大篮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追,弟弟也跟着跑。人们
一阵哄笑,那是善意的、好玩的哄笑,但听起来并不舒服。
等他们跑到家,鲁鲁正把肉摆在面前,坐定了看着。他讨好地迎着姐姐,一脸奉承,
分明是要姐姐批准他吃那块肉。
姐姐扔了篮子,双手捂着脸,哭了。
弟弟着急地给她递手绢,又跺脚训斥鲁鲁:“你要吃肉,你走吧!上山里去,上别
人家去!”鲁鲁也着急地绕着姐姐转,伸出前脚轻轻抓她,用头蹭她,对那块肉没有再
看一眼。
姐姐把肉埋在院中树下。后来妈妈还了肉钱,也没有责备鲁鲁。因为事情过了,责
备他是没有用的。鲁鲁却竟渐渐习惯少肉的生活,隔几天才夜猎一次。和荒野的搏斗比
起来,他似乎更依恋人所给予的温暖。爸爸说,原来箪食瓢饮,狗也能做到的。
鲁鲁还犯过一回严重错误,那是无可挽回的。他和菲菲是好朋友,常闹着玩。他常
把菲菲一拱,让她连翻几个身,菲菲会立刻又扑上来,和他打闹。冷天时菲菲会离开自
己的窝,挨着鲁鲁睡。这一年菲菲生了一窝小猫,对鲁鲁凶起来。鲁鲁不识趣,还伸嘴
到她窝里,嗅嗅她的小猫。菲菲一掌打在鲁鲁鼻子上,把鼻子抓破了。鲁鲁有些生气,
一半也是闹着玩,把菲菲轻轻咬住,往门外一扔。不料菲菲惨叫一声,在地上扑腾几下,
就断了气。鲁鲁慌了,过去用鼻子拱她,把她连翻几个身,但她不像往日一样再扑上来,
她再也不能动了。
妈妈走出房间看时,见鲁鲁坐在菲菲旁边,唧唧咛咛地叫。他见了妈妈,先是愣了
一下,随即趴在地下,腹部着地,一点一点往妈妈脚边蹭。一面偷着翻眼看妈妈脸色。
妈妈好不生气:“你这只狗!不知轻重!一窝小猫怎么办!你给养着!”
妈妈把猫窝杵在鲁鲁面前。鲁鲁吓得又往后蹭,还是不敢站起来。姐姐弟弟都为鲁
鲁说情,妈妈执意要打。鲁鲁慢慢退进了里屋。大家都以为他躲打,跟进去看,见他蹭
到爸爸脚边,用后腿站起来向爸爸作揖,一脸可怜相,原来是求爸爸说情。爸爸摸摸他
的头,看看妈妈的脸色,乖觉地说:“少打几下,行么?”妈妈倒是破天荒准了情,说
决不多打,不过鲁鲁是狗,不打几下,不会记住教训,她只打了鲁鲁三下,每下都很重,
鲁鲁哼哼唧唧地小哭,可是服贴地趴着受打。房门、院门都开着,他没有一点逃走的意
思,连爸爸也离开书桌看着鲁鲁说:“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看来你大杖也不会走的。”
鲁鲁受过杖,便趴在自己窝里。妈妈说他要忏悔,不准姐姐弟弟理他。姐姐很为菲
菲和小猫难受,也为鲁鲁难受。她知道鲁鲁不是故意的。晚饭没有鲁鲁的份,姐姐悄悄
拿了水和剩饭给他。鲁鲁呜咽着舐她的手。
和鲁鲁的错误比起来,他的功绩要大得多了。一天下午,有一家请妈妈去看一位孕
妇。她本来约好往一个较远的村庄去给一个病人送药,这任务便落在姐姐身上。姐姐高
兴地把药装好。弟弟和鲁鲁都要跟去,因为那段路远,弟弟又不大舒服,遂决定鲁鲁陪
弟弟在家。妈妈和姐姐一起出门,分道走了。鲁鲁和弟弟送到庙门口,看着姐姐的土布
衣裳的淡黄色消失在绿丛中。
妈妈到那孕妇家,才知她就要临盆。便等着料理,直到婴儿呱呱坠地,一切停妥才
走。到家已是夜里10点多了,只见家中冷清清点着一盏煤油灯。鲁鲁哼唧着在屋里转来
转去。
弟弟一见妈妈便扑上来哭了。“姐姐,”他说,“姐姐还没回家——。”
爸爸不在家。妈妈定了定神,转身到最近的同事家,叫起那家的教书先生,又叫起
房东,又叫起他们认为该叫的人。
人们焦急地准备着灯笼火把。这时鲁鲁仍在妈妈身边哼着,还踩在妈妈脚上,引她
注意。弟弟忽然说:“鲁鲁要去找姐姐。”
妈妈一愣,说:“快去!鲁鲁,快去!”鲁鲁像离弦的箭一样,一下窜出好远,很
快就被黑暗吞没了。
鲁鲁用力跑着。姐姐带着的草药味,和着姐姐本身的气味,形成淡淡的芳香,指引
他向前跑。一切对他都不存在。黑夜,树木,路旁汩汩的流水,都是那样虚幻,只有姐
姐的缥缈的气味,是最实在的。可他居然一度离开那气味,不向前过桥,却抄近下河,
游过溪水,又插上小路。那气味又有了,鲁鲁一点没有为自己的聪明得意,只是认真地
跑着,一直跑进了坐落在另一个山谷的村庄。
村里一片漆黑,人们都睡了。他跑到一家门前,着急地挠门。气味断了,姐姐分明
走进门去了。他挠了几下,绕着院墙跑到后门,忽然又闻见那气味,只没有了草药。姐
姐是从后门出来,走过村子,上了通向山里的蜿蜒小路。鲁鲁一刻也不敢停,伸长舌头,
努力地跑。树更多了,草更深了。植物在夜间的浓烈气息使得鲁鲁迷惑,他仔细辨认那
熟悉的气味,在草丛中追寻。草莽中的小生物吓得四面奔逃。鲁鲁无暇注意那是什么。
那时便有最鲜美的活食在他嘴下,他也不会碰一碰的。
终于在一棵树下,一块大石旁,鲁鲁看见了那土布衣裳的淡黄色。姐姐靠在大石上
睡着了。鲁鲁喜欢得横窜竖跳,自己乐了一阵,然后坐在地上,仔细看着姐姐,然后又
绕她走了两圈,才伸前爪轻轻推她。
姐姐醒了。她惊讶地四处看着,又见一弯新月,照着黑黝黝的树木、草莽、山和石。
她恍然地说:“鲁鲁,该回家了。
妈妈急坏了。”
她想抓住鲁鲁的项圈,但她已经太高了,遂脱下外衣,拴在项圈上。鲁鲁乖乖地引
路,一路不时回头看姐姐,发出呜呜的高兴的声音。
“你知道么?鲁鲁,我只想试试,能不能也做一个吕克大梦。”①姐姐和他推心置
腹地说。“没想到这么晚了。不过离20年还差得远。” ①吕克大梦,指美国前期浪漫主义作家华盛顿·欧文(1783—1859)的著名作品。
小说中写一个农民瑞·普凡·温克尔上山打猎,遇见一群玩九柱戏的人,温克尔喝了他
们的酒,沉睡了20年,醒来见城廓全非。——作者原注
他们走到堤上时,看见远处树丛间一闪一闪的亮光。不一会儿人声沸腾,是找姐姐
的队伍来了。他们先看见雪白的鲁鲁,好几个声音叫他,问他,就像他会回答似的。他
的回答是把姐姐越引越近,姐姐投在妈妈怀里时,他担心地坐在地上看。他怕姐姐要受
罚,因为谁让妈妈着急生气,都要受罚的,可是妈妈只拥着她,温和地说:“你不怕醒
来就见不着妈妈了么?”“我快睡着时,忽然害怕了,怕一睡20年。可是已经止不住,
糊里糊涂睡着了。”人们一阵大笑,忙着议论,那山上有狼,多危险!谁也不再理鲁鲁
了。
爸爸从城里回来后,特地找鲁鲁握手,谢谢他。鲁鲁却已经不大记得自己的功绩,
只是这几天饭里居然放了牛肉,使他很高兴。
又过些时,姐姐弟弟都在附近学校上学了。那也是城里迁来的。姐姐上中学,弟弟
上小学。鲁鲁每天在庙门口看着他们走远,又在山坡下等他们回来。他还是在草丛里跑,
跟着去买豆腐。又有一阵姐姐经常生病,每次她躺在床上,鲁鲁都很不安,好像要遇到
什么危险似的。卖豆腐老人特地来说,姐姐多半得罪了山灵,应该到鲁鲁找到姐姐的地
方去上供。爸爸妈妈向他道谢,却说什么营养不良,肺结核。鲁鲁不懂他们的话,如果
懂得,他一定会代姐姐去拜访山灵的。
好在姐姐多半还是像常人一样活动,鲁鲁的不安总是短暂的。日子如同村边小溪潺
潺的清流,不慌不忙,自得其乐。
若是鲁鲁这时病逝,他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狗了。但是他很健康,雪白的长毛亮闪
闪的,身体的线条十分挺秀。没人知道鲁鲁的年纪,却可以看出,他离衰老还远。
村边小溪静静地流,不知大江大河里怎样掀着巨浪。终于有一天,日本投降的消息
传到这小村,整个小村沸腾了,赛过任何一次赶集。人们以为熬出头了。爸爸把妈妈一
下子紧紧抱住,使得另外三个成员都很惊讶。爸爸流着眼泪说:“你辛苦了,你太辛苦
了。”妈妈呜呜地哭起来。爸爸又把姐姐弟弟也揽了过来,四人抱在一起。鲁鲁连忙也
把头往缝隙里贴。
这个经历了无数风雨艰辛的亲爱的小家庭,怎么能少得了鲁鲁呢。
“回北平去!”弟弟得意地说。姐姐蹲下去抱住鲁鲁的头。
她已经是一个窈窕的少女了。他们决没有想到鲁鲁是不能去的。
范家已经家徒四壁,只有一双宝贝儿女和爸爸几年来在煤油灯下写的手稿。他们要
走很方便。可是还有鲁鲁呢。鲁鲁留在这里,会发疯的。最后决定带他到T市,送给爱狗
的唐伯伯。
经过一阵忙乱,一家人上了汽车。在那一阵忙乱中,鲁鲁总是很不安,夜里无休止
地做梦。他梦见爸爸、妈妈、姐姐和弟弟都走了。只剩下他,孤零零在荒野中奔跑。而
且什么气味也闻不见,这使他又害怕又伤心。他在梦里大声哭,妈妈就过来推醒他,然
后和爸爸讨论:“狗也会做梦么?”“我想——至少鲁鲁会的。”
鲁鲁居然也上了车。他高兴极了,安心极了。他特别讨好地在妈妈身上蹭。妈妈叫
起来:“去!去!车本来就够颠的了。”鲁鲁连忙钻在姐姐弟弟中间,三个伙伴一起随
着车的颠簸摇动,看着青山慢慢往后移;路在前面忽然断了,转过山腰,又显现出来,
总是无限地伸展着——。
上路第二天,姐姐就病了。爸爸说她无福消受这一段风景。她在车上躺着,到旅店
也躺着。鲁鲁的不安超过了她任何一次病时。他一刻不离地挤在她脚前。眼光惊恐而凄
凉。这使妈妈觉得不吉利,很不高兴。“我们的孩子不至于怎样。你不用担心,鲁鲁。”
她把他赶出房门,他就守在门口。弟弟很同情他,向他详细说明情况,说回到北平可以
治好姐姐的病,说交通不便,不能带鲁鲁去,自己和姐姐都很伤心;还说唐伯伯是最好
的人,一定会和鲁鲁要好。鲁鲁不懂这么多话,但是安静地听着,不时舐舐弟弟的手。
T市附近,有一个著名的大瀑布。10里外便听得水声隆隆。车经这里,人们都下车到
观瀑亭上去看。姐姐发着烧,还执意要下车。于是爸爸在左,妈妈在右,鲁鲁在前,弟
弟在后,向亭上走去。急遽的水流从几十丈的绝壁跌落下来,在青山翠峦中形成一个小
湖,水气迷蒙,一直飘到观瀑亭上。姐姐觉得那白花花的厚重的半透明的水幔和雷鸣般
的轰响仿佛离她很远。她努力想走近些看,但它们越来越远,她什么也看不见了,倚在
爸爸肩上晕了过去。
从此鲁鲁再也没有看见姐姐。没有几天,他就显得憔悴,白毛失去了光泽。唐家的
狗饭一律有牛肉,他却嗅嗅便走开,不管弟弟怎样哄劝。这时的弟弟已经比姐姐高,是
撞不倒的了。一天,爸爸和弟弟带他上街,在一座大房子前站了半天。
鲁鲁很讨厌那房子的气味,哼哼唧唧要走。他若知道姐姐正在楼上一扇窗里最后一
次看他,他会情愿在那里站一辈子,永不离开。
范家人走时,唐伯伯叫人把鲁鲁关在花园里。他们到医院接了姐姐,一直上了飞机。
姐姐和弟弟为了不能再见鲁鲁,一起哭了一场。他们听不见鲁鲁在花园里发出的撕裂了
的、变了声的嗥叫,他们看不见鲁鲁因为一次又一次想挣脱绳索,磨掉了毛的脖子。他
们飞得高高的,遗落了儿时的伙伴。
鲁鲁发疯似地寻找主人,时间持续得这样久,以致唐伯伯以为他真要疯了。唐伯伯
总是试着和他握手,同情地、客气地说:“请你住在我家,这不是已经说好了么,鲁鲁。”
鲁鲁终于渐渐平静下来。有一天,又不见了。过了半年,大家早以为他已离开这世
界,他竟又回到唐家。他瘦多了,完全变成一只灰狗,身上好几处没有了毛,露出粉红
的皮肤;颈上的皮项圈不见了,替代物是原来那一省的狗牌。可见他曾回去,又一次去
寻找谜底。若是鲁鲁会写字,大概会写出他怎样戴露披霜,登山涉水;怎样被打被拴,
而每一次都能逃走,继续他千里迢迢的旅程;怎样重见到小山上的古庙,却寻不到原住
在那里的主人。也许他什么也写不出,因为他并不注意外界的凄楚,他只是要去解开内
心的一个谜。他去了,又历尽辛苦回来,为了不违反主人的安排。当然,他究竟怎样想
的,没有人,也没有狗能够懂得。
唐家人久闻鲁鲁的事迹,却不知他有观赏瀑布的癖好。他常常跑出城去,坐在大瀑
布前,久久地望着那跌宕跳荡、白帐幔似的落水,发出悲凉的、撞人心弦的哀号。
参考资料:(选自《十月》1980年第6期)
第2个回答 2006-01-27
我读小学的时候,家里养了一条狗,我记不起是我抑或是我哥给它取的名字了。它的毛色是黑的,黑的发亮,黑的在没有月光的夜间只能见到它一双发亮的眼睛。我也忘了它从哪里来到我家的,它的父亲母亲又是谁。在我的记忆里,它身材并不高大,但很凶,眼睛里总是闪烁着两束凶光,仿佛特别仇恨它生活的这个世界。除了对我们家的人显现出一点狗的温柔外,它对村子里的其他人都是凶巴巴的,对村子里的男女老幼不仅大叫大喊,而且还要冲上去咬他们的裤脚。我对它说过不要这样,这样下去对它没有什么好结果,但它对我的多次教育置若罔闻不理不睬。结果我不说你也明白,后来它死了,当然是被几个成年人打死的,成年人中包括我父亲在内。我也不可怜它以及它的死。它的死变成了和我家有点亲戚关系的成年人的酒桌上的佳肴,变成了那个物质匮乏年代的一次小小的宴席。我本来不打算加入那个宴席,但弥漫在空气中的狗肉的香味实在诱人,我吃了一块狗肉后觉得味道很好,后来又吃了几块,以至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忘掉它留给我的美好的味觉。
我的一位朋友以前在他乡下的家里养了一条狗。我对那狗的记忆很深,因为它威胁过已经是成年人的我。它身材高大威猛,有一身好看的棕色的毛发。有一次我去朋友家里凑热闹,它一见到我就向我冲上来,我被吓得转身往友人家的楼上逃。它不屈不挠,步步紧逼,把我逼到阳台的角落里。幸亏友人叫住了它,不然我真的吓得想跳楼。不过,这狗就是优秀,我再次去友人家玩耍的时候,它就看了我一眼,不再大喊大叫。我相信它一定把我身体的气味记住了,储存进了它不凡的嗅觉系统了。它出色的表现,印证了我在路上种种不必要的过滤和担忧。后来,它被人在夜间用迷魂药害得神志恍惚,我的友人为他的优秀的狗洒下了同情的热泪。
我住进城里后,在居住区经常见到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狗。它们在主人手中的绳子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烂漫的生活。有时候,特别是在我疲倦的时候,它们的这种无忧无虑的被豢养的寄生的念头,曾经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我知道这不可能也不想,所以仅一闪而过。
猴年的年末下了一场大雪,大雪下得我心软。当我在电视上见到雪夜里的外省人忙于疲惫寻找居所的时候,我心里也下了一场软绵绵的雪。是的,别以为人比狗活得好,在一个动物被尊宠的时代,在一个爱狗似乎胜于爱人的时代,这仅仅是一些善良的人心中的一个同样善良的愿望。
狗年驾到,关于狗的话题也多起来。看到满街得意洋洋自由自在摇头摆尾闪烁于阳光下的宠物,也许我应该为狗们感到高兴和庆幸,短短二十年功夫,它们的地位简直升天了。真的,除了漂亮可爱的国宝大熊猫,当今还有哪种动物像狗那样备受人类的宠爱呢?
西方人是早就爱狗的。狗一直是西方人的宠物和朋友,享受着与人平起平坐的待遇。记得幼年从电影上看到的西洋狗,就已经是戴着颈圈皮带吃肉喝奶的了。那时候就不止一次沮丧地想过,与其在国内挨饿,倒不如死了投胎到西方做一条狗更享福。西方的狗确实享福,待遇实在太优厚了。而且不是个别,而是大众。在西方,许多家庭都养狗,而且不止一条。休闲时分,主人便带上狗一起到公园或河边遛。为了把宠物培养得更出色,主人还会想方设法送狗去贵族学校或条件优越的培训班,让它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成为一只能做各种乖巧动作的优雅高贵的狗。有一句话说:西方人养的狗比他们养的孩子还多,此话许多西方人都承认并为之而自豪。到西方友人家中作客,讨好主人最好的办法,便是夸奖他们家的狗如何聪明可爱,如果能和狗来一番搂抱之类的亲热,效果会更理想。当然,对于后者,我们中国人很不习惯因而也很难做到。
这些年,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崇洋的人越来越多,国人养狗之风日盛。街上到处走着大摇大摆遛狗的人,许多时髦女郎也仿效洋人把狗搂在怀里作亲热状。在我眼里,这些情景多少有点勉强而做作,因为太不符合汉民族的传统习惯。
对狗的态度,国人和洋人历来不同。就说英语和汉语吧,说到狗,其义也相去甚远。英语中的dog,完全没有骂人的意思;但狗在汉语中,就有着卑贱的含义。谁若说“你这条狗”,那一定是在辱骂对方,如进一步说“狗东西”,“狗崽子”,那简直就是咬牙切齿的挑衅,几乎准备要动武的了。在汉语里,很多不好的、被贬损的东西都与狗有关。汉人恨狗的历史非常悠久。不管什么东西,一旦跟狗扯上关系,那就是很臭的了:狗腿子、狗主意、狗头军师、狼心狗肺……把狗诅咒得彻头彻尾,最后还要痛打落水狗,连一点宽恕的余地都不留了。
不过话说回来,汉人对狗,有时也不是那么绝对一棍子打死的。追溯更久远的历史,狗的地位其实并不如此可悲。那时候,狗还能和龙、虎等有地位的动物相提并论,在十二生肖中占据一席,可想而知,那时的狗,还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否则何来资格占据呢?占据了,狗就堂而皇之算个东西了,狗的地位就摆在那儿了。从此泱泱中华大国,就有了为数相当的一大批属狗的公民了。故此可以推想,即便后来汉语对狗诋毁得如此厉害,但至少有相当多的汉人不为所动,还是相当喜欢狗的,否则,在全国各地,尤其在辽阔广大的农村,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把自己心爱的孩子唤作“阿狗”、“小狗”、“狗狗”呢?这些称呼都是非常亲昵动人的爱称,充满了温馨的人伦之乐。
而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尤其跨入新的世纪,狗们更是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如今的狗已是鹤立鸡群,大大超出了十二生肖中自己的同类,跃升为人类喜爱的宠物,几乎与人类平起平坐了。狗被人喜爱,也确实有它的道理。狗其实是性情温驯的动物,天生与人亲近,特别懂人性,能与人沟通,善解人意,狗的这一优点实在突出,远胜同类。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好,见到人会大摇其尾,会亲热地舔人的手背,那轻柔,那温暖,令人畜有心电之感,默契之感。狗的耐性也出类拔萃,静静地,一蹲就是一两个小时,偎依在主人脚边,主人起身走,它会紧跟不舍,一步一趋,如影随形,那份亲热,确实让人感动。而狗最高的美德是忠诚,忠诚守宅,效忠主人,甚至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舍身救主,这样的故事听过不少。只有狗,才能建立如此功勋。难怪狗能受到人类的加倍宠爱了。
早些年,我曾听我的朋友的父亲——一位来自农村的老人——讲述他在乡下养过的一条狗的故事,让我记忆犹深。这狗不仅夜里守宅,白天还帮着干活:黄昏,它会到放鸭的河边汪汪吠叫,把鸭子赶出水来,然后尾随护送回家;老人的老伴在田头做活,家养的山羊拴在田头啃草,收工时分,老伴一手挎篮子,一手牵羊,狗就唔唔叫着,上前舔舔老伴的手,老伴把拴羊的橛子扔下,狗就咬住木橛子把羊牵回家。
前苏联作家特罗耶波尔斯基写过一部叫《白比姆黑耳朵》的小说,写了白狗比姆的忠诚。他写道:“世界上任何一只狗都不会把普普通通的忠诚看作是什么特别的品格,然而,人们却偏要把狗的这种感情提到丰功伟绩的高度,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像狗那样具有对待朋友忠诚不渝的品德。”
人对动物确实不了解。即便人已成为这个世界的灵长,趾高气扬地迈进了高级的文明形态,但他对其余的动物了解多少呢?禽兽有着各自的灵性,各自生命神性的光辉,被人类赞美并且崇尚的美好品质,很多动物其实也都具备。人类看到狗的忠诚,虎的勇猛,狮的威武,狼的刚毅和狐狸的机巧。人类在远古时期就明白自身本性中先天欠缺的成分,并懂得从禽兽那里借取力量。但人对动物的研究和了解还是太肤浅太肤浅了,人总是高高悬于众生之上,即便科学再发达,人类也永远不能完全破解动物世界的奥秘。
禽兽在人境之外,但它们之中的许多都具有人性,正如人性里有着许多类似兽性的基因。我们应该敬畏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它们的生命同样是高贵和美丽的。古人云:“鸢飞鱼跃,道无不在。”上帝说:所有生命平等,共存共在。人类应该牢记。
我的一位朋友以前在他乡下的家里养了一条狗。我对那狗的记忆很深,因为它威胁过已经是成年人的我。它身材高大威猛,有一身好看的棕色的毛发。有一次我去朋友家里凑热闹,它一见到我就向我冲上来,我被吓得转身往友人家的楼上逃。它不屈不挠,步步紧逼,把我逼到阳台的角落里。幸亏友人叫住了它,不然我真的吓得想跳楼。不过,这狗就是优秀,我再次去友人家玩耍的时候,它就看了我一眼,不再大喊大叫。我相信它一定把我身体的气味记住了,储存进了它不凡的嗅觉系统了。它出色的表现,印证了我在路上种种不必要的过滤和担忧。后来,它被人在夜间用迷魂药害得神志恍惚,我的友人为他的优秀的狗洒下了同情的热泪。
我住进城里后,在居住区经常见到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狗。它们在主人手中的绳子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烂漫的生活。有时候,特别是在我疲倦的时候,它们的这种无忧无虑的被豢养的寄生的念头,曾经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我知道这不可能也不想,所以仅一闪而过。
猴年的年末下了一场大雪,大雪下得我心软。当我在电视上见到雪夜里的外省人忙于疲惫寻找居所的时候,我心里也下了一场软绵绵的雪。是的,别以为人比狗活得好,在一个动物被尊宠的时代,在一个爱狗似乎胜于爱人的时代,这仅仅是一些善良的人心中的一个同样善良的愿望。
狗年驾到,关于狗的话题也多起来。看到满街得意洋洋自由自在摇头摆尾闪烁于阳光下的宠物,也许我应该为狗们感到高兴和庆幸,短短二十年功夫,它们的地位简直升天了。真的,除了漂亮可爱的国宝大熊猫,当今还有哪种动物像狗那样备受人类的宠爱呢?
西方人是早就爱狗的。狗一直是西方人的宠物和朋友,享受着与人平起平坐的待遇。记得幼年从电影上看到的西洋狗,就已经是戴着颈圈皮带吃肉喝奶的了。那时候就不止一次沮丧地想过,与其在国内挨饿,倒不如死了投胎到西方做一条狗更享福。西方的狗确实享福,待遇实在太优厚了。而且不是个别,而是大众。在西方,许多家庭都养狗,而且不止一条。休闲时分,主人便带上狗一起到公园或河边遛。为了把宠物培养得更出色,主人还会想方设法送狗去贵族学校或条件优越的培训班,让它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成为一只能做各种乖巧动作的优雅高贵的狗。有一句话说:西方人养的狗比他们养的孩子还多,此话许多西方人都承认并为之而自豪。到西方友人家中作客,讨好主人最好的办法,便是夸奖他们家的狗如何聪明可爱,如果能和狗来一番搂抱之类的亲热,效果会更理想。当然,对于后者,我们中国人很不习惯因而也很难做到。
这些年,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崇洋的人越来越多,国人养狗之风日盛。街上到处走着大摇大摆遛狗的人,许多时髦女郎也仿效洋人把狗搂在怀里作亲热状。在我眼里,这些情景多少有点勉强而做作,因为太不符合汉民族的传统习惯。
对狗的态度,国人和洋人历来不同。就说英语和汉语吧,说到狗,其义也相去甚远。英语中的dog,完全没有骂人的意思;但狗在汉语中,就有着卑贱的含义。谁若说“你这条狗”,那一定是在辱骂对方,如进一步说“狗东西”,“狗崽子”,那简直就是咬牙切齿的挑衅,几乎准备要动武的了。在汉语里,很多不好的、被贬损的东西都与狗有关。汉人恨狗的历史非常悠久。不管什么东西,一旦跟狗扯上关系,那就是很臭的了:狗腿子、狗主意、狗头军师、狼心狗肺……把狗诅咒得彻头彻尾,最后还要痛打落水狗,连一点宽恕的余地都不留了。
不过话说回来,汉人对狗,有时也不是那么绝对一棍子打死的。追溯更久远的历史,狗的地位其实并不如此可悲。那时候,狗还能和龙、虎等有地位的动物相提并论,在十二生肖中占据一席,可想而知,那时的狗,还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否则何来资格占据呢?占据了,狗就堂而皇之算个东西了,狗的地位就摆在那儿了。从此泱泱中华大国,就有了为数相当的一大批属狗的公民了。故此可以推想,即便后来汉语对狗诋毁得如此厉害,但至少有相当多的汉人不为所动,还是相当喜欢狗的,否则,在全国各地,尤其在辽阔广大的农村,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把自己心爱的孩子唤作“阿狗”、“小狗”、“狗狗”呢?这些称呼都是非常亲昵动人的爱称,充满了温馨的人伦之乐。
而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尤其跨入新的世纪,狗们更是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如今的狗已是鹤立鸡群,大大超出了十二生肖中自己的同类,跃升为人类喜爱的宠物,几乎与人类平起平坐了。狗被人喜爱,也确实有它的道理。狗其实是性情温驯的动物,天生与人亲近,特别懂人性,能与人沟通,善解人意,狗的这一优点实在突出,远胜同类。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好,见到人会大摇其尾,会亲热地舔人的手背,那轻柔,那温暖,令人畜有心电之感,默契之感。狗的耐性也出类拔萃,静静地,一蹲就是一两个小时,偎依在主人脚边,主人起身走,它会紧跟不舍,一步一趋,如影随形,那份亲热,确实让人感动。而狗最高的美德是忠诚,忠诚守宅,效忠主人,甚至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舍身救主,这样的故事听过不少。只有狗,才能建立如此功勋。难怪狗能受到人类的加倍宠爱了。
早些年,我曾听我的朋友的父亲——一位来自农村的老人——讲述他在乡下养过的一条狗的故事,让我记忆犹深。这狗不仅夜里守宅,白天还帮着干活:黄昏,它会到放鸭的河边汪汪吠叫,把鸭子赶出水来,然后尾随护送回家;老人的老伴在田头做活,家养的山羊拴在田头啃草,收工时分,老伴一手挎篮子,一手牵羊,狗就唔唔叫着,上前舔舔老伴的手,老伴把拴羊的橛子扔下,狗就咬住木橛子把羊牵回家。
前苏联作家特罗耶波尔斯基写过一部叫《白比姆黑耳朵》的小说,写了白狗比姆的忠诚。他写道:“世界上任何一只狗都不会把普普通通的忠诚看作是什么特别的品格,然而,人们却偏要把狗的这种感情提到丰功伟绩的高度,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像狗那样具有对待朋友忠诚不渝的品德。”
人对动物确实不了解。即便人已成为这个世界的灵长,趾高气扬地迈进了高级的文明形态,但他对其余的动物了解多少呢?禽兽有着各自的灵性,各自生命神性的光辉,被人类赞美并且崇尚的美好品质,很多动物其实也都具备。人类看到狗的忠诚,虎的勇猛,狮的威武,狼的刚毅和狐狸的机巧。人类在远古时期就明白自身本性中先天欠缺的成分,并懂得从禽兽那里借取力量。但人对动物的研究和了解还是太肤浅太肤浅了,人总是高高悬于众生之上,即便科学再发达,人类也永远不能完全破解动物世界的奥秘。
禽兽在人境之外,但它们之中的许多都具有人性,正如人性里有着许多类似兽性的基因。我们应该敬畏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它们的生命同样是高贵和美丽的。古人云:“鸢飞鱼跃,道无不在。”上帝说:所有生命平等,共存共在。人类应该牢记。
第3个回答 2006-01-27
狗不是一个幸福的动物,因为它的快乐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最亲近的人主宰它的一生,生存与死亡,饱与饿,冷与暖,渴
能自己的躯体,会是最亲近的餐中食,这就叫做与狼共舞
最亲近的人主宰它的一生,生存与死亡,饱与饿,冷与暖,渴
能自己的躯体,会是最亲近的餐中食,这就叫做与狼共舞
第4个回答 2006-01-28
<西游记>啸天犬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5个回答 2020-07-01
亲亲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