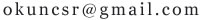歌与诵:诗与赋的分途及音乐对汉代诗歌的影响
在中国诗体的演变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汉代诗歌体式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赋这种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的出现和五言诗与乐府诗的产生,这恰恰与音乐有着极大的关系。为说这一问题,让我们先从赋的演变开始谈起。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说明,歌与不歌,是诗与赋的一条重要区别或者说是根本区别。那么,这种“不歌而诵”的赋是如何产生的呢?按班固的话说,这与战国时代的风气有关,是从古诗中流变出来的。本来,《诗经》中的诗都是可歌的,同时作为一种贵族的文化修养,在春秋以前所谓的“赋诗言志”也是当时的诸侯卿大夫用“诗”来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传》中又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指的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到了战国以后,由于“礼崩乐坏”,由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所以产生了屈原这样的贤人失志之赋。班固的这段话的原文见于《汉书·艺文志》,非常重要,可惜的是过去人们往往都把它忽略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音乐与诗歌的关系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仔细想来,从屈原作《离骚》、《九章》和《天问》开始,配乐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经不再重要。以后宋玉除了模仿屈原的作品而作《九辩》之外,又作了一系列以赋为名的作品,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它们与《离骚》不同,已经完全不能歌唱。正是这些以赋为名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体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诗中流变出一种新的文体——赋。
现在学者们大都认为,汉初诗歌的发展受楚国诗歌与音乐的影响非常之大。这可以包括诗赋两个方面的影响,学者们都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楚辞》对汉代诗与赋的影响分开来谈,说赋往往从宋玉开始,说诗则笼统地把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内。其实如果从音乐与诗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同时参照班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汉赋还是汉诗,都可以从屈原那里找到根源,并且有比较分明的发展趋势。从赋的方面说,我们不能低估《离骚》、《九章》的影响。这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文体方面的影响。我们知道,汉赋可以分为散体大赋和骚体赋两种,其中骚体赋的源头就是屈原的《离骚》。第二是音乐方面的影响。如班固所说,赋的文体特征是“不歌而诵”,骚体赋既然从文体上受《离骚》的影响,我们推测从音乐上也应该受其影响,这反过来似乎也证明《离骚》、《九章》在屈原创作之初可能只是被用来口头吟唱,并没有配乐,所以后代的骚体赋无论从形式还是从表现方式上看都是对屈原作品的直接继承。从诗的方面说,我们说汉初诗歌受楚国诗歌的影响,主要应该指受《九歌》的影响。这也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说汉初的歌诗都是可唱的,而楚辞中直接冠以“歌”名的,只有《九歌》。可见,汉初的歌诗首先继承的就是《九歌》的“歌”的传统。其次,我们看汉初那些楚歌的语言形式,就会发现其句式特点也正好与《九歌》相同,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项羽、刘邦都是楚人,都曾有楚歌传世,《垓下歌》、《大风歌》都是这样的句式。传为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有些篇章中没有“兮”字在中间的句式,当代学者们却都认为是班固在记录时把它省掉了,原本也应该是如《九歌》样中间有“兮”字的典型句式。楚歌的这种句式,在西汉中期以后一直保存下来,成为汉代歌诗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如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汉武帝刘彻的《匏子歌》、《秋风辞》等都是如此。这说明,歌与诵不仅是歌诗与汉赋在文体上的区分,同时也说明,是否配乐可歌也是影响并左右汉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影响汉初诗歌发展的重要因素。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汉赋脱离了音乐演唱而走向独立发展之路以后,它与诗的这种区别也逐渐被学者们认识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作《诗赋略》,明确地提出“不歌而诵谓之赋”,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乐的诗称之为“歌诗”。而汉代的诗,也就是“歌诗”之所以得到新的发展,又恰恰与新的音乐产生和异族音乐的输入有关。
从现有的文献材料来看,在汉代诗歌园地里,最主要的歌诗类别有三种,一种是楚歌,一种是相和歌,一种是鼓吹铙歌。它们的分别,最初不是由于文体上的差异,而是由于不同的音乐乐调来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演唱方式。
汉初诗歌以楚歌为主,一方面是由于楚歌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统治者对楚歌的偏爱。刘邦本是楚人,汉初皇室贵族喜爱楚歌也是自然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汉帝国的日益强大和民族大融合的形成,楚歌独领风骚的局面不复存在。汉武帝为了制造新的颂神曲,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歌谣,还包括乐谱(“声曲折”),这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同时,横吹鼓吹的输入,也为汉代歌诗形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鼓吹乐是在先秦鼓乐、吹乐以及军中凯乐的基础上,融汇北方少数民族的横吹、鼓吹而形成的音乐。《乐府诗集》卷十六引刘huán@②《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八音”是对中国古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的总称。此处言非“八音”,正是指异族音乐而言。据班固《汉书·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按楼烦属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精骑善射。马上鼓吹,以箫笳为主,正是其民族音乐特色。《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又云:“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节,乘舆以为武乐。”以此,知异族音乐输入之后,朝廷甚至有专门负责掌管的“鼓吹署”。这种新乐的乐器以中原之铙、鼓与北狄西域诸国的鸣笳、箫与胡角为主。因而,它与先秦的鼓乐与吹乐不同,与以丝竹为主的相和诸调在风格上判然有别。对此,晋人陆机的《鼓吹赋》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而相和歌作为汉乐府中的主要艺术形式,它的主要艺术特征最初也表现在音乐方面。《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晋书·乐志》也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分析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可知,第一,这里所说的《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最早属于汉世的“街陌谣讴”,第二,这些歌曲在当时属于“相和”曲一类,而这一类曲子的基本演唱方式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以后进一步发展,则演变成相和诸调,如相和六引、平调曲、清调曲、楚调曲、瑟调曲以及大曲等复杂的形式。
楚歌、鼓吹铙歌和相和歌这三种汉代主要的歌诗演唱形式,也影响汉代歌诗的语言形式发展。楚歌产生的比较早,来源比较单一,其语言形式基本上沿袭了《九歌》。鼓吹曲受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歌曲的影响,其语言形式与楚歌完全不同。其代表作为《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全为杂言。而相和诸调虽然也以杂言居多,却出现了许多整齐的五言诗,如《江南可采莲》、《君子行》、《陌上桑》、《白头吟》等等。由此可见,音乐对汉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从《诗经》中《风》、《雅》、《颂》的区别到汉代诗赋的分流以及楚歌、铙歌与相和歌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之大。限于篇幅,本文在这里不能就有关问题做详细展开式的论述,而主要是想提出这一问题以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角度变换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本质问题。试想,如果我们把诗歌不再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的艺术,而是与音乐密不可分的复合型艺术,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以往的中国诗歌研究,就会发现明显的不足。所以我以为,认真地研究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是深化当前中国诗歌研究的重要方面,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在中国诗体的演变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汉代诗歌体式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赋这种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的出现和五言诗与乐府诗的产生,这恰恰与音乐有着极大的关系。为说这一问题,让我们先从赋的演变开始谈起。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说明,歌与不歌,是诗与赋的一条重要区别或者说是根本区别。那么,这种“不歌而诵”的赋是如何产生的呢?按班固的话说,这与战国时代的风气有关,是从古诗中流变出来的。本来,《诗经》中的诗都是可歌的,同时作为一种贵族的文化修养,在春秋以前所谓的“赋诗言志”也是当时的诸侯卿大夫用“诗”来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传》中又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指的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到了战国以后,由于“礼崩乐坏”,由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所以产生了屈原这样的贤人失志之赋。班固的这段话的原文见于《汉书·艺文志》,非常重要,可惜的是过去人们往往都把它忽略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音乐与诗歌的关系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仔细想来,从屈原作《离骚》、《九章》和《天问》开始,配乐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经不再重要。以后宋玉除了模仿屈原的作品而作《九辩》之外,又作了一系列以赋为名的作品,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它们与《离骚》不同,已经完全不能歌唱。正是这些以赋为名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体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诗中流变出一种新的文体——赋。
现在学者们大都认为,汉初诗歌的发展受楚国诗歌与音乐的影响非常之大。这可以包括诗赋两个方面的影响,学者们都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楚辞》对汉代诗与赋的影响分开来谈,说赋往往从宋玉开始,说诗则笼统地把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内。其实如果从音乐与诗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同时参照班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汉赋还是汉诗,都可以从屈原那里找到根源,并且有比较分明的发展趋势。从赋的方面说,我们不能低估《离骚》、《九章》的影响。这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文体方面的影响。我们知道,汉赋可以分为散体大赋和骚体赋两种,其中骚体赋的源头就是屈原的《离骚》。第二是音乐方面的影响。如班固所说,赋的文体特征是“不歌而诵”,骚体赋既然从文体上受《离骚》的影响,我们推测从音乐上也应该受其影响,这反过来似乎也证明《离骚》、《九章》在屈原创作之初可能只是被用来口头吟唱,并没有配乐,所以后代的骚体赋无论从形式还是从表现方式上看都是对屈原作品的直接继承。从诗的方面说,我们说汉初诗歌受楚国诗歌的影响,主要应该指受《九歌》的影响。这也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说汉初的歌诗都是可唱的,而楚辞中直接冠以“歌”名的,只有《九歌》。可见,汉初的歌诗首先继承的就是《九歌》的“歌”的传统。其次,我们看汉初那些楚歌的语言形式,就会发现其句式特点也正好与《九歌》相同,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项羽、刘邦都是楚人,都曾有楚歌传世,《垓下歌》、《大风歌》都是这样的句式。传为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有些篇章中没有“兮”字在中间的句式,当代学者们却都认为是班固在记录时把它省掉了,原本也应该是如《九歌》样中间有“兮”字的典型句式。楚歌的这种句式,在西汉中期以后一直保存下来,成为汉代歌诗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如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汉武帝刘彻的《匏子歌》、《秋风辞》等都是如此。这说明,歌与诵不仅是歌诗与汉赋在文体上的区分,同时也说明,是否配乐可歌也是影响并左右汉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影响汉初诗歌发展的重要因素。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汉赋脱离了音乐演唱而走向独立发展之路以后,它与诗的这种区别也逐渐被学者们认识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作《诗赋略》,明确地提出“不歌而诵谓之赋”,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乐的诗称之为“歌诗”。而汉代的诗,也就是“歌诗”之所以得到新的发展,又恰恰与新的音乐产生和异族音乐的输入有关。
从现有的文献材料来看,在汉代诗歌园地里,最主要的歌诗类别有三种,一种是楚歌,一种是相和歌,一种是鼓吹铙歌。它们的分别,最初不是由于文体上的差异,而是由于不同的音乐乐调来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演唱方式。
汉初诗歌以楚歌为主,一方面是由于楚歌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统治者对楚歌的偏爱。刘邦本是楚人,汉初皇室贵族喜爱楚歌也是自然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汉帝国的日益强大和民族大融合的形成,楚歌独领风骚的局面不复存在。汉武帝为了制造新的颂神曲,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歌谣,还包括乐谱(“声曲折”),这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同时,横吹鼓吹的输入,也为汉代歌诗形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鼓吹乐是在先秦鼓乐、吹乐以及军中凯乐的基础上,融汇北方少数民族的横吹、鼓吹而形成的音乐。《乐府诗集》卷十六引刘huán@②《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八音”是对中国古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的总称。此处言非“八音”,正是指异族音乐而言。据班固《汉书·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按楼烦属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精骑善射。马上鼓吹,以箫笳为主,正是其民族音乐特色。《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又云:“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节,乘舆以为武乐。”以此,知异族音乐输入之后,朝廷甚至有专门负责掌管的“鼓吹署”。这种新乐的乐器以中原之铙、鼓与北狄西域诸国的鸣笳、箫与胡角为主。因而,它与先秦的鼓乐与吹乐不同,与以丝竹为主的相和诸调在风格上判然有别。对此,晋人陆机的《鼓吹赋》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而相和歌作为汉乐府中的主要艺术形式,它的主要艺术特征最初也表现在音乐方面。《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晋书·乐志》也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分析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可知,第一,这里所说的《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最早属于汉世的“街陌谣讴”,第二,这些歌曲在当时属于“相和”曲一类,而这一类曲子的基本演唱方式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以后进一步发展,则演变成相和诸调,如相和六引、平调曲、清调曲、楚调曲、瑟调曲以及大曲等复杂的形式。
楚歌、鼓吹铙歌和相和歌这三种汉代主要的歌诗演唱形式,也影响汉代歌诗的语言形式发展。楚歌产生的比较早,来源比较单一,其语言形式基本上沿袭了《九歌》。鼓吹曲受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歌曲的影响,其语言形式与楚歌完全不同。其代表作为《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全为杂言。而相和诸调虽然也以杂言居多,却出现了许多整齐的五言诗,如《江南可采莲》、《君子行》、《陌上桑》、《白头吟》等等。由此可见,音乐对汉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从《诗经》中《风》、《雅》、《颂》的区别到汉代诗赋的分流以及楚歌、铙歌与相和歌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之大。限于篇幅,本文在这里不能就有关问题做详细展开式的论述,而主要是想提出这一问题以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角度变换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本质问题。试想,如果我们把诗歌不再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的艺术,而是与音乐密不可分的复合型艺术,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以往的中国诗歌研究,就会发现明显的不足。所以我以为,认真地研究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是深化当前中国诗歌研究的重要方面,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无其他回答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