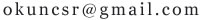中国文学发展到元代,由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以及文学本身的种种原因,传统的诗词古文创作局限于少数文人的范围,新起来的戏曲小说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好,流行南北。诗词古文的语言风格一味模唐仿宋,有人还甚至标榜学习周秦汉魏,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曲高和寡,与那语言浅近通俗的戏曲、小说相比较就不易的人们接受。戏曲、小说的题材大都取自人民群众所关心和熟悉的生活,同时由于作者多数出身于社会中下层,他们看问题,谈人论事,也都和人民群众好恶接近,所以戏曲小说,特别是杂剧成了元代趺学创作中最受欢迎的剧艺。前人把它和唐诗、宋词并称,作为一个朝代文学艺术的代表,许多作家也享受很高的荣誉。
诗词只是在少数文人学士之问传播,散文多经世、酬世应用之作,不像戏曲小说在大庭广众的勾栏中说唱演出。戏剧演出必须争取看官听众,故事须群众喜见乐闻。因为演员和少数作者都要靠此谋生。不像诗词作者并不以写诗作词为生,多数是公余闲暇,或家有钱财,舞文弄墨,自我陶醉或者发发牢骚而已。当然也有少数人把写作诗词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不过总的说来,戏曲小说真正能做到雅俗共赏,而诗词古文却只能在官场和骚人雅士中问流传,主要是士大夫独抒怀抱或互相唱和。
一般说来,元代文学中少数诗词、古文,多数小说、散曲、杂剧、南曲戏文等等中的一个共同东西,就是或多或少反映出来了那种同情民生疾苦和抗议民族压迫的忧国忧民思想。这个思想是蒙古统治阶级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和疯狂奴役劳动人民的必然产物。但是诗词、戏剧等除开这个共同点以外,也还各有其自身的特征。文学体裁的运用,和作家的社会地位自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体裁有雅俗新旧,采用某种体裁却和作家的身份地位以及文学修养有关系。传统的诗词古文更多的被社会地位高而持有正统思想的人所选用,至于戏剧小说本不登大雅之堂,写作者大半社会地位低下而思想受到传统束缚较少。这样诗词古文是一个情调,而戏曲小说另是一个情调。惟有散曲较为复杂,它和杂剧相近,只是体制长短不同,有曲子而无科白,仅供清唱,不能上演。思想内容有时和杂剧接近,有时和诗词接近。换句话说,诗词古文的总的特点是作者多半是社会地位较高,题材偏于酬世赠答、寻亲访友和离愁别恨。反映出来的是封建社会上层人士的生活情况。有时也出现一些反映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作品。至于戏剧小说的作者一般是“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人士,作品题材也偏于人民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民间传说和普通人民日常生活。这里,作为上流人士的怡情遣兴、怨乱伤离的诗词,和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的戏剧小说,不仅是题材不同,而在内容上也有很大的区别。诗词中,官场得失和人世悲欢离合成了常见的主题,而戏剧小说中,出现了一些敢于摆脱封建道德枷锁的叛逆人物,性格泼辣明快,却是诗词中少见的。这中问散曲的情况比较复杂,普通知识分子写,达官贵人也写,多数场合是供给伎女在筵席上唱的,也就沾染上一些不健康的情感。但叹世、归隐之类的作品大量出现,却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总之,元代文学创作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中个人得丧悲欢和社会生活面貌。而由于作者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和政治地位的差异,加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复杂关系,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分别表现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理想。其中用通俗的语言描述新生的事物并以新的道德标准评价生活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文学史上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
元代文学中诗词、散文、小说、戏剧等体裁的消长变化,就文学本身说,还表现为由篇幅短小过渡到长篇巨制,由作者个人抒情,或者评论、记事变为叙事和代言。单纯诗词、单纯散文体裁之外,有诗词有散文的混合体制戏剧、小说的大量出现,这种文化充分体现新的体裁的出现比起旧体诗词、古文便于塑造完美的艺术形象和容纳深广而复杂的社会生活。
此外,元代虽然为期只有百年左右,但由于岁月迁流,人事代谢,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此起彼落,历史不断前进,文学也跟着向前发展,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也表现不同的特色。
元代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成吉思汗攻人金中都后使人寻觅辽朝宗室,得耶律楚材。后耶律楚材随从成吉思汗西征,写了许多描绘北方少数民族生活的诗篇。耶律楚材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他于成吉思汗死后,太宗窝阔台当权时,曾上书窝阔台,建议成立燕京编修所和平阳经籍所,保存汉族古籍,吸收一批汉族儒生,对于保护文化,和给文学活动创造了条件。《元史·耶律楚材传》说:“楚材奏言:‘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尔,可官其人。’楚材日:‘请校试之。’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这是元灭金后,吸收最多的一批文人学士。当时“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此外元好问的《上耶律中书书》说:“窃见南中大夫士归河朔者在所有之。”时辈如“平阳王状元纲、东明王状元鹗,滨人王夔,临淄人李浩,秦人张徽、杨涣然、李庭训,河中李献卿,武安乐夔,固安李天翼,沛县刘汝翼,齐人谢良弼,郑人吕大鹏,山西魏瑶,泽人李恒简、李禹翼,燕人张圣俞,太原张纬、李谦、冀致君、张辉卿、高鸣,孟津李蔚,真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铉,云中李微,中山杨果,东平李彦,西华徐世隆,济阳张辅之,燕人曹居一、王铸,浑源刘祁及其弟郁、李同,平定贾庭扬、杨恕,济南杜仁杰,洛水张仲经,虞乡麻革,东明商挺,渔阳赵著,平阳赵维道,汝南杨鸿,河中张肃,河朔勾龙瀛,东胜程思温及其从弟思忠,凡此诸人,虽其学业操行,参差不齐,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元好问开了这一串名单,希望耶律楚材推荐引进。后来这些人有的出来做官,有的没有做官。这些人中有不少学者文人,诗人作家。其中杨果、杜仁杰、商挺还是散曲作者。
杜仁杰有[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构阑),描写院本演出情况。其中有一句说“爨罢将幺拔”,与陶宗仪所说院本演唱者为五人,谓之“五花爨弄”正合。今山西洪洞元代壁画大行散乐忠都秀的演出,前排亦是五人。疑忠都秀即中都秀,乃金中都的名演员而流落山西各地,所演者亦为院本。不过金末院本与杂剧十分接近,所以陶宗仪说金代院本杂剧是一回事,到元朝才“厘而为二”。杂剧初期可能和院本演出形式差不多,杂剧本由院本蜕变而来,胡祗遹在《赠宋氏序》已指出这一点。金代末年的院本演出中的“五花爨弄”,实元杂剧四折加楔子这种形式的渊源所自。早期院本杂剧多由妓女演出,故杜仁杰所描述的院本演出的演员都是女的,杂剧既从院本演化而来,故演出形式亦承袭衣钵。耶律楚材《赠蒲察元帅》诗中说:“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伎拔胡琴。”这里“碧髯官伎”也是女的。他另有一首《戏作》诗说:“歌姬窈窕髯遮口,舞伎轻盈眼放光。”既然要女扮男装,似乎不是纯粹的歌舞,而是带表演的,正如杜仁杰所描绘那样“一个装做张太公”,是演戏的。蒲察元帅当是金朝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他降元后,仍官原职,和杜仁杰是同时人。他们所见的应是初期的杂剧。元代军中有戏班,叫做女乐。初期杂剧大都是写婚姻爱情的,杜仁杰散曲中所写的就是《调风月》院本。关汉卿有《诈妮子调风月》杂剧,虽然不是一回事,但调情却是相同的。白朴的《裴少俊墙头马上》、《董秀英花月东墙记》等,莫不皆然。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以金人撤离中都为背景,创作年代似亦较早,而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如果作者王实甫与关汉卿为同时人,当为元代早期作品。
元好问向耶律楚材推荐的一批人中,有的还是著名的诗人如杨奂、麻革。杨奂除写散曲外,也能写诗。他们诗中流露出两种思想感情:一是归隐,一是对金亡的悼念。有位诗人杨宏道在一首《六国朝》词中说:“虚名何益,薄宦徒劳,得预俊游中,观望好。”面对现实社会,袖手旁观,代表一些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杨奂说:“林泉忧患少,京国是非多。”亦复如此。元好问于金亡后,不再做官,过的也是这种生活。一般说,元代初期,确切地说应叫蒙哥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北方政治虽然统一,但文化并没有建立一个中心。当时文人活动大都集中在山西、河北两个地区。所谓河汾诗派就是以山西元好阀为主帅,这派诗的特点是“当金元混扰困郁之中,其词藻风标如层峰荡波,金坚玉莹,绝无突梯脂韦之习,纤靡弛弱之句。”作者有麻革、张宇、陈赓、陈庾、房嗥、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而以元好问“为之冠”。所谓“不观遗山之诗,无以知河汾之学;不观河汾之诗,无以知遗山之大”,他们大都不满于江西诗派,而摹仿中晚唐。至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金朝灭亡,怀着淡淡的留恋,如陈庾的《清明后书怀》说:“江山信美非吾土,怀抱何时得好开。”曹之谦的《北宫》说:“登临欲问前朝事,红日西沉碧水东。”二是这些诗人都自甘贫贱,不做新朝的官,消极不合作,怀才不用,不住大城市,经常各地奔走。这样他们有机会看到祖国河山壮丽,写出了一些刚健清新的风景诗。如麻革的《阻雪华下》、陈赓的《游龙洞词》、段克己的《乙巳清明游清阳峡》。当我们读到“东山气象太猛悍,万马骎骎来楚甸。中分不肯割鸿沟,锻砺戈矛期一战”时,感到气魄雄伟,和那写风景幽美,山清水秀的山水诗完全不一样,这种写山水同时也表现了人物的傲岸。三是这些诗人来往各地于长途跋涉之中,注意到人民的穷困生活,写出一些同情民生疾苦的诗。如房嗥的《贫家女》说:“终身辛苦不下机,身上却无丝一缕。”曹之谦的《自赵城还府》说:“独怜疲俗诛求困,愁叹声多不可闻。”
除河汾诗派外,有一个和元好问几乎同时的老作家李俊民,他的作品内容和河汾诗派也大致相同。他的《寄伊阳令周文之括户》说:“疲俗脂膏今已尽,看看鞭算及舟车。”揭露了官吏的压迫和掠夺。统治者无穷无尽的诛求,人民的困苦不堪,这种现象在当时是普遍的,不是个别现象,杨宏道《空村谣》就作了有力的说明。
元太宗窝阔台、耶律楚材、元好问相继去世,宪宗蒙哥让他的弟弟忽必烈治理汉族人民居住的地方。忽必烈是一位“思大有为于天下”的人,在这以前他早就搜罗了一批汉族知名文士刘秉忠、王鹗、张之谦、窦默、姚枢、许衡、赵复、魏瑶、赵璧等人作他的助手。连大名鼎鼎的元好问也和史天泽的幕僚张德辉一起北上见忽必烈,称奉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就是依靠这个汉人慕僚集团,用汉法治理汉人,得到汉人地主儒生的广泛支持。宪宗蒙哥于l259年攻宋合川,死于军中,忽必烈此时也正围攻宋的鄂州,闻讯即许宋议和,返回开平,召集塔察儿等宗王大将举行选汗大会,忽必烈被推为大汗。即位后,依据汉人封建王朝的传统,颁布即位诏,称皇帝(世祖)。自成吉思汗建立国家以来,从未建立年号,忽必烈建元中统,表示他是中原汉地封建王朝的继承人,后来他听从刘秉忠的建议,又改国号为大元。正当忽必烈在开平举行选汗时,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认为选汗应在鄂嫩河、克鲁伦河地方举行,忽必烈在汉地进行选举,显然违背传统惯例,不予承认。乃在和林另行召集大会,蒙哥诸子及察合台系宗王数人,拥立阿里不哥为汗,出现一国二主的现象。经过几次战争,忽必烈打败了阿里不哥,但西北几个汗国从此实际上走向独立,和元朝中央只维持名义从属关系,他们大部分仍过着游牧生活,他们的文学创作和中原不同。
忽必烈于夺取并巩固了汗位后,即着手继续进行侵宋战争。1267年南宋叛将刘整献攻宋之策,先攻襄阳,撤除南宋屏障。忽必烈依计而行,先后攻占樊城、襄阳,并大练水军,准备沿江东下,乘胜灭宋。忽必烈召集姚枢、许衡等商议,大家都说“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正是时机。乃移师东向,一举而攻下临安,宋帝投降,国亡。这次出兵,忽必烈告诫统帅伯颜,要效法曹彬,“勿得妄加杀掠”,但是一位前锋张弘范却直认不讳地说:“我军百万战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屠杀还是凄惨的。
忽必烈在争夺汗位,侵宋灭宋期间,北方一些汉族文人感到进退两难。前一段的难是夹在蒙古诸王贵族的纠纷之中,难处。因为这种纠纷中牵涉到治理国家使用汉人不使用汉人问题。后一段的难是赞成伐宋还是不赞成伐宋。赵复是从宋过来的,就认为宋父母之国,不可伐。郝经、徐世隆却希望两国共存共荣,郝经《宿州夜雨》诗说:“星麾何日平康了,两国长令似一王。”刘因于无可奈何之中,作赋哀悼,姚枢、许衡赞成,这时候的难是难办。许衡说:“国家既自朔漠人中原,居汉地,主汉民,其当用汉法无疑也。”得到忽必烈的信任,但不断遭到其他蒙古贵族的反对,他时而做官,时而辞官,在《训子》诗中说“身居畎亩思致君”,而在《偶成》一诗中又说“老作山家亦分甘”。有一首《辞召命》的诗说:“一天雷雨诚偃畏,千载风云漫企思,留取闲身卧田舍,静看蝴蝶挂蛛丝。”他的思想十分矛盾。产生这种矛盾思想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元代重武轻文的情况下,虽然被起用而不被倚重,有屈才之感。另一是在民族矛盾中,怕遇到意想不到的祸害。许衡这种人不像河汾诗派那些人甘心隐姓埋名,做诗而不做官。所以怀才不遇和隐居情思成了这个时期的重要主题。许衡诗中的思想也代表了一些出仕做官的汉人的共同感受。
忽必烈灭宋后,在中国北方和南方都引起了波动,而南方文坛,变化更大,反响强烈。文天祥《过零丁洋》诗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对以暴力强加于人的反抗,十分坚决。他的《正气歌》更是激励人心的作品。谢翱、谢枋得、郑思肖、林景熙、邓剡、汪元量等人的诗词一扫宋季江湖、四灵的空洞纤弱的积弊,发扬刚健悲壮的作风。尤其是汪元量,他被俘至燕京,后放归,为道士,漫游各地,写了不少诗词。他的组诗《潮州歌》九十八首最有名。一般说,宋亡后诗人词人对待新朝采取三种不同的态度。除上面所讲抗元不仕这种人外,还有一种背宋仕元。如方回、王沂孙、仇远、赵孟頫等。还有一种人采取消极态度,他们既不抗,也不仕,过着隐居生活,写的诗词,托物寄兴,情调低沉。如蒋捷、张炎、刘辰翁、周密等人。蒋捷的《贺新郎》(兵后寓吴),刘辰翁的《柳梢青》(春感),张炎的《南浦》(春水),周密的《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其中似有寓意而不明显,至于仕元的王沂孙、仇远所写的诗词,情调和周密等人大致相同。他们过往甚密,并结为诗社。还有一些诗人控诉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如尹廷高的《过故里感怀》,吴澄的《怀黄县丞时避乱寓华盖山》,刘诜的《感旧行》等。自然也还有些人的作品,对国家兴亡,无动于衷。
这个时期的北方诗人思想情况,波动不如南方大,所写诗词有点接近张炎、蒋捷。徐世隆《挽文丞相》诗说:“大元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义似汉王封齿日,忠如蜀将斩颜时。乾坤日月华夷见,岑海风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编不尽,老夫和泪写新诗。”言外之意,对不仕元朝,还是同情的。北方汉人由于长期在辽金统治之下,过了几个世代,对于南宋赵家,感情已经不是那么深厚了。况且蒙哥把女真和汉族人民统统目为汉人,政治待遇一样,冲淡了民族的观念,对南宋的灭亡自然不太关心了。至于忽必烈叫赵孟頫写诗讥讽留梦炎,未免使人难堪。龙仁夫《题琵琶亭》诗,说:“老大蛾眉负所天,尚留余韵人哀弦。江心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过别船。”据《隐居通议》说:“诸吕家于江州,仕宋累朝穷富极贵。及北兵至,自文焕而下,相率纳款,无一人抗节报国。”有人在琵琶亭上题了这首诗,“一日吕老见而挥泪,语意深婉,佳句也。”这首诗的确是婉而多讽,也算是元灭宋后文学创作上的一点余波。
但在北方杂剧中反映这一历史情况更曲折。马致远的《汉宫秋》不让昭君出塞,而写她投江自尽,或有深意。《艺林伐山》载:“宋宫人王婉容,随徽钦北去。粘罕见之,求为子妇。婉容自刎车中,虏人葬之道傍。”元宋无有诗记其事云:“贞烈那堪黠虏求,玉颜甘没塞垣秋。孤愤若是邻青冢,地下昭君见亦羞。”马致远不使昭君远嫁成亲,地下与婉容相见,自不羞惭。但不知马致远写此剧时,是否有此一层意思。马致远写得最多的是“神仙道化”剧,曾被人说成“万花丛里马神仙”。自然他不是最初写神仙道化剧的人。最早作者似是史樟。史樟乃散曲家史天泽的儿子,常麻衣草履,以散仙自名,称为“史九散仙”一作“史九敬先”。写有《老庄周一枕蝴蝶梦》杂剧。这个剧本第一折[混江龙]唱词有“名利似汤浇瑞雪,荣华如秉烛当风。”第二折李府尹道白中有“莫恋五花官诰,莫爱七贤朝帽。惧祸忧谗何日了,几人能到老。”“惧祸忧谗”是元初汉族文人进入官场,在民族矛盾中最担惊受怕的一件事,看来神仙道化剧所宣传的得道成仙和儒生弃官归隐有同样的现实意义。这个剧和马致远《太华山陈抟高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等所宣传的都是清心寡欲,同属于全真教。全真教派的重要人物邱处机曾受到成吉思汗的召见,享受到一些特殊待遇。在蒙哥时期曾盛极一时。宪宗蒙哥时期,全真教道士横行霸道,毁坏孔庙和释迦佛像,并占领佛寺达四百八十二处,因此佛道发生激烈冲突。宪宗四年(1254)全真道教和佛教在哈剌和林展开御前辩论,道教的教义被驳倒而失败,道经被称为伪经而遭焚毁。后于至元十七年道教又和儒士争论失败,许多道士被迫还俗,北方全真教的势力逐渐衰落。元代掌管宗教的机构是宣政院,但道教却由征辟隐士、召举贤良的集贤院兼管,南北道教,各树宗派,未能统一。全真派衰落后,神仙道化剧也渐渐少了。
关汉卿的《窦娥冤》也作于元灭宋后,时间在至元二十八年以后,民族矛盾渐趋和缓。从他的散曲《杭州景》看来,他对赵宋并无特殊感情,他的剧作也不反映南宋灭亡这一波动南北的事件。《窦娥冤》中反映了两件事却是元代所特有的。一是窦天章借蔡婆的二十两银子,一年后本利变成四十两。这是元代回回商人传来的高利贷,所谓羊羔息。另一个是楚州太守桃杌向来告状的人下跪。祗候说:“相公,他是告状的,怎生跪着他?”桃杌回答说:“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这虽是一句戏言,但元代地方官薪俸微薄,往往不足以自养,几乎是无官不贪赃枉法。大德七年十二月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款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件。这事实就说明,戏言中包藏着一些真实。元代这么多冤狱,人民希望平反冤狱,这样就出现了公案戏。公案戏除《窦娥冤》外,李潜夫的《灰阑记》,也很出色。
这个时期散曲作家卢挚有《[双调]水仙子》(西湖)四首,说:“谁僝僽鸱夷子,也新添两鬓丝,是个淡净的西施。”这支曲子写的是西湖雪景,但伍子胥、西施都是和吴国灭亡有关的人物,可能寓意宋亡。卢挚不仅是一个散曲家,他的诗文也很有名,为人所称赏。他的文被认为与姚燧并肩,诗亦同刘因不相上下。苏天爵说:“国家平定中原,士踵金宋余习,率皆粗豪衰茶。涿郡卢公始以清新飘逸为之倡。”他在元代文学发展变化中,起了一点推动的作用。当时有个著名歌妓珠帘秀和他以散曲互相赠答,可见其人并非保守的道学家。珠帘秀和当时一些著名文人学士如王浑、胡祗通、冯子振、关汉卿都有往来,虽为妓女,但身价颇高。谢枋得、郑思肖并谓元代社会中人分十等,八倡九儒,所谓倡,殆指珠帘秀这种人说的。元世祖忽必烈对赵良弼说:“高丽小国,匠人菜人,皆胜汉人,至于儒人通经书,学孔孟,汉人只是课赋吟诗,将何用!”可见元代对于儒人,并非笼统轻视。轻视的只是那些只知“课赋吟诗”的人,而对于“通经书,学孔孟”还是重视的。姚枢、许衡等人的社会地位决不在妓人之下。
元人攻宋,引起了文学上一场风波,经过十多年才恢复平静。元世祖忽必烈不重视诗词,认为吟诗作赋无用,也就不注意这些作品,所以没有人因为写诗作词受到迫害。相反的却是他还派人请这些人出来做官。只是有人肯出来,有人不肯出来。明人吴讷说:“元世祖初克江南,畸人逸士浮沉里闾间,多以诗酒玩世。元贞、大德以后稍出。”戴表元写《读书有感》说:“如今已免多人笑,老大知无欲嫁心。”拒绝征召。赵孟頫、袁桷、邓文原等接受礼聘。赵孟頫以“宋室王孙人仕,风流儒雅,冠绝一时。”他和袁桷互相唱和,“诗学为之一变。”他们这些南方人和北方的元明善、姚燧、马祖常等人一起,写诗古体模仿汉魏,律诗学盛唐,风格清丽而遒壮,开始形成南北诗风统一的格调。欧阳玄说:“承平日久,四方俊彦,萃于京师,笙镛相宣,风雅迭唱。…‘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古。”所谓金宋季世之弊,即金宋人崇奉苏黄,而宋季诗人学晚唐,这个变化标志着元代诗歌发展的新里程。
如上所言,元政府派程钜夫到江南搜访隐逸,礼聘贤才,吴澄、赵孟頫、袁桷等人相继出仕,有些剧作家也跟着北上。《录鬼簿》卷上说:“范居中,字子正,杭州人,大德问被旨赴都,公亦北行。以才高不见遇,卒于家。有乐府南北腔行于世。”他和施惠、黄天泽、沈珙合编了一个剧本叫《鹩鹩裘》。《太和正音谱》把他的杂剧列入杰作,并说:“其词势非笔舌可能拟,真词林之英杰。”评价颇高。但他没有赵孟頫等人的幸运,却“才高不见遇”,回到杭州老家。他著有乐府“南北腔”,当即南北合套,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亦有南北合套现象。南北曲的声腔是不一样的。元人徐士荣《新街曲》说:“东街南曲声婉扬,西街北曲声激昂。佳人唱曲不下楼,楼下白马青丝缰。昨日开筵击鼍鼓,今夜合席调笙簧。乐声一似曲声杂,人意岂如物意长。”一个套曲里面有两种声腔,即一会儿“婉扬”,一会儿“激昂”,这是北曲进入杭州后和南曲结合后产生的现象。北杂剧和南戏文互相影响的结果,这是~种戏剧改革的尝试,不过这种改革是一个失败的改革,所以范居中“才高不见遇”。南戏改革应是南戏吸收北杂剧一些优点,如唱曲采用联套,科诨减少,结构严密,集中刻画人物性格等等,不是南北合套,叫人听起来不谐和,破坏了审美享受。只有把《刘知远诸宫调》改为《白兔记》,关汉卿的《拜月亭》改为《月亭记》比较成功。也表现南戏的进步和发展。
元代杂剧作家参加征召失意而归,除范居中外,不见记载。但职位不振,沉抑下僚的作家却是很多的。被称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郑光祖,他的《王粲登楼》就表现一个“空学成补天才”,而“寻不着上天梯”的人牢骚不平和怀才不遇者的怨气。乔吉流落江湖四十年,宫天挺终身为人陷害而不见用,处境和郑光祖相同。乔吉除写杂剧外,散曲也写得十分出色。他说:“看遍洛阳花似锦,荣也在你;枯,也在你。”表现他一生潦倒,壮志销磨。
元朝政府征召隐逸,虽然有些人不遇而归,但总的说来还是成功的。袁士元《题寒江独钓图》说:“堪笑江湖几钓徒,朝来相唤暮相呼。只今风雪蒙头处,回首烟波一个无。”隐士们全都出仕了。后来有些人,不征召也自动北上求官。方回《再送王俞戴溪》说:“宇宙喜一统,于今三十年。江南诸将相,北上扬其鞭。书生亦觅官,裹粮趋幽燕。”被称为元代四大文学家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多数是歌颂民安物阜的,但都掌握了写作技巧,而虞集名气尤大。虞集的《风人松》词有一句“杏花春雨江南”,字句十分凝炼,当时人极为赞赏,他自己也很满意。吴师道《陈监丞安雅堂集序》说陈旅作文“用心甚苦,功甚深,藻绩组织,不极其工不止。”虞集、陈旅的文风上这种变化,当时有一种代表性,因为不只是诗文,杂剧、散曲也如此。郑光祖、张可久、乔吉等人的作品表现典雅工丽,讲究辞藻,渐渐丧失了早期戏曲中的朴野。
在虞、杨、范、揭之外,这时别树一帜的是马祖常、萨都刺。他们都是少数民族的诗人,而萨都刺的词写得尤其出色。他的[满江红](《金陵怀古》),吊古伤今,胸怀磊落,继承和发扬了苏东坡、辛弃疾以后豪放派的风格。
诗词只是在少数文人学士之问传播,散文多经世、酬世应用之作,不像戏曲小说在大庭广众的勾栏中说唱演出。戏剧演出必须争取看官听众,故事须群众喜见乐闻。因为演员和少数作者都要靠此谋生。不像诗词作者并不以写诗作词为生,多数是公余闲暇,或家有钱财,舞文弄墨,自我陶醉或者发发牢骚而已。当然也有少数人把写作诗词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不过总的说来,戏曲小说真正能做到雅俗共赏,而诗词古文却只能在官场和骚人雅士中问流传,主要是士大夫独抒怀抱或互相唱和。
一般说来,元代文学中少数诗词、古文,多数小说、散曲、杂剧、南曲戏文等等中的一个共同东西,就是或多或少反映出来了那种同情民生疾苦和抗议民族压迫的忧国忧民思想。这个思想是蒙古统治阶级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和疯狂奴役劳动人民的必然产物。但是诗词、戏剧等除开这个共同点以外,也还各有其自身的特征。文学体裁的运用,和作家的社会地位自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体裁有雅俗新旧,采用某种体裁却和作家的身份地位以及文学修养有关系。传统的诗词古文更多的被社会地位高而持有正统思想的人所选用,至于戏剧小说本不登大雅之堂,写作者大半社会地位低下而思想受到传统束缚较少。这样诗词古文是一个情调,而戏曲小说另是一个情调。惟有散曲较为复杂,它和杂剧相近,只是体制长短不同,有曲子而无科白,仅供清唱,不能上演。思想内容有时和杂剧接近,有时和诗词接近。换句话说,诗词古文的总的特点是作者多半是社会地位较高,题材偏于酬世赠答、寻亲访友和离愁别恨。反映出来的是封建社会上层人士的生活情况。有时也出现一些反映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作品。至于戏剧小说的作者一般是“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人士,作品题材也偏于人民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民间传说和普通人民日常生活。这里,作为上流人士的怡情遣兴、怨乱伤离的诗词,和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的戏剧小说,不仅是题材不同,而在内容上也有很大的区别。诗词中,官场得失和人世悲欢离合成了常见的主题,而戏剧小说中,出现了一些敢于摆脱封建道德枷锁的叛逆人物,性格泼辣明快,却是诗词中少见的。这中问散曲的情况比较复杂,普通知识分子写,达官贵人也写,多数场合是供给伎女在筵席上唱的,也就沾染上一些不健康的情感。但叹世、归隐之类的作品大量出现,却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总之,元代文学创作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中个人得丧悲欢和社会生活面貌。而由于作者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和政治地位的差异,加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复杂关系,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分别表现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理想。其中用通俗的语言描述新生的事物并以新的道德标准评价生活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文学史上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
元代文学中诗词、散文、小说、戏剧等体裁的消长变化,就文学本身说,还表现为由篇幅短小过渡到长篇巨制,由作者个人抒情,或者评论、记事变为叙事和代言。单纯诗词、单纯散文体裁之外,有诗词有散文的混合体制戏剧、小说的大量出现,这种文化充分体现新的体裁的出现比起旧体诗词、古文便于塑造完美的艺术形象和容纳深广而复杂的社会生活。
此外,元代虽然为期只有百年左右,但由于岁月迁流,人事代谢,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此起彼落,历史不断前进,文学也跟着向前发展,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也表现不同的特色。
元代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成吉思汗攻人金中都后使人寻觅辽朝宗室,得耶律楚材。后耶律楚材随从成吉思汗西征,写了许多描绘北方少数民族生活的诗篇。耶律楚材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他于成吉思汗死后,太宗窝阔台当权时,曾上书窝阔台,建议成立燕京编修所和平阳经籍所,保存汉族古籍,吸收一批汉族儒生,对于保护文化,和给文学活动创造了条件。《元史·耶律楚材传》说:“楚材奏言:‘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尔,可官其人。’楚材日:‘请校试之。’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这是元灭金后,吸收最多的一批文人学士。当时“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此外元好问的《上耶律中书书》说:“窃见南中大夫士归河朔者在所有之。”时辈如“平阳王状元纲、东明王状元鹗,滨人王夔,临淄人李浩,秦人张徽、杨涣然、李庭训,河中李献卿,武安乐夔,固安李天翼,沛县刘汝翼,齐人谢良弼,郑人吕大鹏,山西魏瑶,泽人李恒简、李禹翼,燕人张圣俞,太原张纬、李谦、冀致君、张辉卿、高鸣,孟津李蔚,真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铉,云中李微,中山杨果,东平李彦,西华徐世隆,济阳张辅之,燕人曹居一、王铸,浑源刘祁及其弟郁、李同,平定贾庭扬、杨恕,济南杜仁杰,洛水张仲经,虞乡麻革,东明商挺,渔阳赵著,平阳赵维道,汝南杨鸿,河中张肃,河朔勾龙瀛,东胜程思温及其从弟思忠,凡此诸人,虽其学业操行,参差不齐,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元好问开了这一串名单,希望耶律楚材推荐引进。后来这些人有的出来做官,有的没有做官。这些人中有不少学者文人,诗人作家。其中杨果、杜仁杰、商挺还是散曲作者。
杜仁杰有[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构阑),描写院本演出情况。其中有一句说“爨罢将幺拔”,与陶宗仪所说院本演唱者为五人,谓之“五花爨弄”正合。今山西洪洞元代壁画大行散乐忠都秀的演出,前排亦是五人。疑忠都秀即中都秀,乃金中都的名演员而流落山西各地,所演者亦为院本。不过金末院本与杂剧十分接近,所以陶宗仪说金代院本杂剧是一回事,到元朝才“厘而为二”。杂剧初期可能和院本演出形式差不多,杂剧本由院本蜕变而来,胡祗遹在《赠宋氏序》已指出这一点。金代末年的院本演出中的“五花爨弄”,实元杂剧四折加楔子这种形式的渊源所自。早期院本杂剧多由妓女演出,故杜仁杰所描述的院本演出的演员都是女的,杂剧既从院本演化而来,故演出形式亦承袭衣钵。耶律楚材《赠蒲察元帅》诗中说:“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伎拔胡琴。”这里“碧髯官伎”也是女的。他另有一首《戏作》诗说:“歌姬窈窕髯遮口,舞伎轻盈眼放光。”既然要女扮男装,似乎不是纯粹的歌舞,而是带表演的,正如杜仁杰所描绘那样“一个装做张太公”,是演戏的。蒲察元帅当是金朝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他降元后,仍官原职,和杜仁杰是同时人。他们所见的应是初期的杂剧。元代军中有戏班,叫做女乐。初期杂剧大都是写婚姻爱情的,杜仁杰散曲中所写的就是《调风月》院本。关汉卿有《诈妮子调风月》杂剧,虽然不是一回事,但调情却是相同的。白朴的《裴少俊墙头马上》、《董秀英花月东墙记》等,莫不皆然。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以金人撤离中都为背景,创作年代似亦较早,而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如果作者王实甫与关汉卿为同时人,当为元代早期作品。
元好问向耶律楚材推荐的一批人中,有的还是著名的诗人如杨奂、麻革。杨奂除写散曲外,也能写诗。他们诗中流露出两种思想感情:一是归隐,一是对金亡的悼念。有位诗人杨宏道在一首《六国朝》词中说:“虚名何益,薄宦徒劳,得预俊游中,观望好。”面对现实社会,袖手旁观,代表一些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杨奂说:“林泉忧患少,京国是非多。”亦复如此。元好问于金亡后,不再做官,过的也是这种生活。一般说,元代初期,确切地说应叫蒙哥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北方政治虽然统一,但文化并没有建立一个中心。当时文人活动大都集中在山西、河北两个地区。所谓河汾诗派就是以山西元好阀为主帅,这派诗的特点是“当金元混扰困郁之中,其词藻风标如层峰荡波,金坚玉莹,绝无突梯脂韦之习,纤靡弛弱之句。”作者有麻革、张宇、陈赓、陈庾、房嗥、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而以元好问“为之冠”。所谓“不观遗山之诗,无以知河汾之学;不观河汾之诗,无以知遗山之大”,他们大都不满于江西诗派,而摹仿中晚唐。至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金朝灭亡,怀着淡淡的留恋,如陈庾的《清明后书怀》说:“江山信美非吾土,怀抱何时得好开。”曹之谦的《北宫》说:“登临欲问前朝事,红日西沉碧水东。”二是这些诗人都自甘贫贱,不做新朝的官,消极不合作,怀才不用,不住大城市,经常各地奔走。这样他们有机会看到祖国河山壮丽,写出了一些刚健清新的风景诗。如麻革的《阻雪华下》、陈赓的《游龙洞词》、段克己的《乙巳清明游清阳峡》。当我们读到“东山气象太猛悍,万马骎骎来楚甸。中分不肯割鸿沟,锻砺戈矛期一战”时,感到气魄雄伟,和那写风景幽美,山清水秀的山水诗完全不一样,这种写山水同时也表现了人物的傲岸。三是这些诗人来往各地于长途跋涉之中,注意到人民的穷困生活,写出一些同情民生疾苦的诗。如房嗥的《贫家女》说:“终身辛苦不下机,身上却无丝一缕。”曹之谦的《自赵城还府》说:“独怜疲俗诛求困,愁叹声多不可闻。”
除河汾诗派外,有一个和元好问几乎同时的老作家李俊民,他的作品内容和河汾诗派也大致相同。他的《寄伊阳令周文之括户》说:“疲俗脂膏今已尽,看看鞭算及舟车。”揭露了官吏的压迫和掠夺。统治者无穷无尽的诛求,人民的困苦不堪,这种现象在当时是普遍的,不是个别现象,杨宏道《空村谣》就作了有力的说明。
元太宗窝阔台、耶律楚材、元好问相继去世,宪宗蒙哥让他的弟弟忽必烈治理汉族人民居住的地方。忽必烈是一位“思大有为于天下”的人,在这以前他早就搜罗了一批汉族知名文士刘秉忠、王鹗、张之谦、窦默、姚枢、许衡、赵复、魏瑶、赵璧等人作他的助手。连大名鼎鼎的元好问也和史天泽的幕僚张德辉一起北上见忽必烈,称奉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就是依靠这个汉人慕僚集团,用汉法治理汉人,得到汉人地主儒生的广泛支持。宪宗蒙哥于l259年攻宋合川,死于军中,忽必烈此时也正围攻宋的鄂州,闻讯即许宋议和,返回开平,召集塔察儿等宗王大将举行选汗大会,忽必烈被推为大汗。即位后,依据汉人封建王朝的传统,颁布即位诏,称皇帝(世祖)。自成吉思汗建立国家以来,从未建立年号,忽必烈建元中统,表示他是中原汉地封建王朝的继承人,后来他听从刘秉忠的建议,又改国号为大元。正当忽必烈在开平举行选汗时,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认为选汗应在鄂嫩河、克鲁伦河地方举行,忽必烈在汉地进行选举,显然违背传统惯例,不予承认。乃在和林另行召集大会,蒙哥诸子及察合台系宗王数人,拥立阿里不哥为汗,出现一国二主的现象。经过几次战争,忽必烈打败了阿里不哥,但西北几个汗国从此实际上走向独立,和元朝中央只维持名义从属关系,他们大部分仍过着游牧生活,他们的文学创作和中原不同。
忽必烈于夺取并巩固了汗位后,即着手继续进行侵宋战争。1267年南宋叛将刘整献攻宋之策,先攻襄阳,撤除南宋屏障。忽必烈依计而行,先后攻占樊城、襄阳,并大练水军,准备沿江东下,乘胜灭宋。忽必烈召集姚枢、许衡等商议,大家都说“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正是时机。乃移师东向,一举而攻下临安,宋帝投降,国亡。这次出兵,忽必烈告诫统帅伯颜,要效法曹彬,“勿得妄加杀掠”,但是一位前锋张弘范却直认不讳地说:“我军百万战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屠杀还是凄惨的。
忽必烈在争夺汗位,侵宋灭宋期间,北方一些汉族文人感到进退两难。前一段的难是夹在蒙古诸王贵族的纠纷之中,难处。因为这种纠纷中牵涉到治理国家使用汉人不使用汉人问题。后一段的难是赞成伐宋还是不赞成伐宋。赵复是从宋过来的,就认为宋父母之国,不可伐。郝经、徐世隆却希望两国共存共荣,郝经《宿州夜雨》诗说:“星麾何日平康了,两国长令似一王。”刘因于无可奈何之中,作赋哀悼,姚枢、许衡赞成,这时候的难是难办。许衡说:“国家既自朔漠人中原,居汉地,主汉民,其当用汉法无疑也。”得到忽必烈的信任,但不断遭到其他蒙古贵族的反对,他时而做官,时而辞官,在《训子》诗中说“身居畎亩思致君”,而在《偶成》一诗中又说“老作山家亦分甘”。有一首《辞召命》的诗说:“一天雷雨诚偃畏,千载风云漫企思,留取闲身卧田舍,静看蝴蝶挂蛛丝。”他的思想十分矛盾。产生这种矛盾思想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元代重武轻文的情况下,虽然被起用而不被倚重,有屈才之感。另一是在民族矛盾中,怕遇到意想不到的祸害。许衡这种人不像河汾诗派那些人甘心隐姓埋名,做诗而不做官。所以怀才不遇和隐居情思成了这个时期的重要主题。许衡诗中的思想也代表了一些出仕做官的汉人的共同感受。
忽必烈灭宋后,在中国北方和南方都引起了波动,而南方文坛,变化更大,反响强烈。文天祥《过零丁洋》诗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对以暴力强加于人的反抗,十分坚决。他的《正气歌》更是激励人心的作品。谢翱、谢枋得、郑思肖、林景熙、邓剡、汪元量等人的诗词一扫宋季江湖、四灵的空洞纤弱的积弊,发扬刚健悲壮的作风。尤其是汪元量,他被俘至燕京,后放归,为道士,漫游各地,写了不少诗词。他的组诗《潮州歌》九十八首最有名。一般说,宋亡后诗人词人对待新朝采取三种不同的态度。除上面所讲抗元不仕这种人外,还有一种背宋仕元。如方回、王沂孙、仇远、赵孟頫等。还有一种人采取消极态度,他们既不抗,也不仕,过着隐居生活,写的诗词,托物寄兴,情调低沉。如蒋捷、张炎、刘辰翁、周密等人。蒋捷的《贺新郎》(兵后寓吴),刘辰翁的《柳梢青》(春感),张炎的《南浦》(春水),周密的《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其中似有寓意而不明显,至于仕元的王沂孙、仇远所写的诗词,情调和周密等人大致相同。他们过往甚密,并结为诗社。还有一些诗人控诉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如尹廷高的《过故里感怀》,吴澄的《怀黄县丞时避乱寓华盖山》,刘诜的《感旧行》等。自然也还有些人的作品,对国家兴亡,无动于衷。
这个时期的北方诗人思想情况,波动不如南方大,所写诗词有点接近张炎、蒋捷。徐世隆《挽文丞相》诗说:“大元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义似汉王封齿日,忠如蜀将斩颜时。乾坤日月华夷见,岑海风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编不尽,老夫和泪写新诗。”言外之意,对不仕元朝,还是同情的。北方汉人由于长期在辽金统治之下,过了几个世代,对于南宋赵家,感情已经不是那么深厚了。况且蒙哥把女真和汉族人民统统目为汉人,政治待遇一样,冲淡了民族的观念,对南宋的灭亡自然不太关心了。至于忽必烈叫赵孟頫写诗讥讽留梦炎,未免使人难堪。龙仁夫《题琵琶亭》诗,说:“老大蛾眉负所天,尚留余韵人哀弦。江心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过别船。”据《隐居通议》说:“诸吕家于江州,仕宋累朝穷富极贵。及北兵至,自文焕而下,相率纳款,无一人抗节报国。”有人在琵琶亭上题了这首诗,“一日吕老见而挥泪,语意深婉,佳句也。”这首诗的确是婉而多讽,也算是元灭宋后文学创作上的一点余波。
但在北方杂剧中反映这一历史情况更曲折。马致远的《汉宫秋》不让昭君出塞,而写她投江自尽,或有深意。《艺林伐山》载:“宋宫人王婉容,随徽钦北去。粘罕见之,求为子妇。婉容自刎车中,虏人葬之道傍。”元宋无有诗记其事云:“贞烈那堪黠虏求,玉颜甘没塞垣秋。孤愤若是邻青冢,地下昭君见亦羞。”马致远不使昭君远嫁成亲,地下与婉容相见,自不羞惭。但不知马致远写此剧时,是否有此一层意思。马致远写得最多的是“神仙道化”剧,曾被人说成“万花丛里马神仙”。自然他不是最初写神仙道化剧的人。最早作者似是史樟。史樟乃散曲家史天泽的儿子,常麻衣草履,以散仙自名,称为“史九散仙”一作“史九敬先”。写有《老庄周一枕蝴蝶梦》杂剧。这个剧本第一折[混江龙]唱词有“名利似汤浇瑞雪,荣华如秉烛当风。”第二折李府尹道白中有“莫恋五花官诰,莫爱七贤朝帽。惧祸忧谗何日了,几人能到老。”“惧祸忧谗”是元初汉族文人进入官场,在民族矛盾中最担惊受怕的一件事,看来神仙道化剧所宣传的得道成仙和儒生弃官归隐有同样的现实意义。这个剧和马致远《太华山陈抟高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等所宣传的都是清心寡欲,同属于全真教。全真教派的重要人物邱处机曾受到成吉思汗的召见,享受到一些特殊待遇。在蒙哥时期曾盛极一时。宪宗蒙哥时期,全真教道士横行霸道,毁坏孔庙和释迦佛像,并占领佛寺达四百八十二处,因此佛道发生激烈冲突。宪宗四年(1254)全真道教和佛教在哈剌和林展开御前辩论,道教的教义被驳倒而失败,道经被称为伪经而遭焚毁。后于至元十七年道教又和儒士争论失败,许多道士被迫还俗,北方全真教的势力逐渐衰落。元代掌管宗教的机构是宣政院,但道教却由征辟隐士、召举贤良的集贤院兼管,南北道教,各树宗派,未能统一。全真派衰落后,神仙道化剧也渐渐少了。
关汉卿的《窦娥冤》也作于元灭宋后,时间在至元二十八年以后,民族矛盾渐趋和缓。从他的散曲《杭州景》看来,他对赵宋并无特殊感情,他的剧作也不反映南宋灭亡这一波动南北的事件。《窦娥冤》中反映了两件事却是元代所特有的。一是窦天章借蔡婆的二十两银子,一年后本利变成四十两。这是元代回回商人传来的高利贷,所谓羊羔息。另一个是楚州太守桃杌向来告状的人下跪。祗候说:“相公,他是告状的,怎生跪着他?”桃杌回答说:“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这虽是一句戏言,但元代地方官薪俸微薄,往往不足以自养,几乎是无官不贪赃枉法。大德七年十二月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款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件。这事实就说明,戏言中包藏着一些真实。元代这么多冤狱,人民希望平反冤狱,这样就出现了公案戏。公案戏除《窦娥冤》外,李潜夫的《灰阑记》,也很出色。
这个时期散曲作家卢挚有《[双调]水仙子》(西湖)四首,说:“谁僝僽鸱夷子,也新添两鬓丝,是个淡净的西施。”这支曲子写的是西湖雪景,但伍子胥、西施都是和吴国灭亡有关的人物,可能寓意宋亡。卢挚不仅是一个散曲家,他的诗文也很有名,为人所称赏。他的文被认为与姚燧并肩,诗亦同刘因不相上下。苏天爵说:“国家平定中原,士踵金宋余习,率皆粗豪衰茶。涿郡卢公始以清新飘逸为之倡。”他在元代文学发展变化中,起了一点推动的作用。当时有个著名歌妓珠帘秀和他以散曲互相赠答,可见其人并非保守的道学家。珠帘秀和当时一些著名文人学士如王浑、胡祗通、冯子振、关汉卿都有往来,虽为妓女,但身价颇高。谢枋得、郑思肖并谓元代社会中人分十等,八倡九儒,所谓倡,殆指珠帘秀这种人说的。元世祖忽必烈对赵良弼说:“高丽小国,匠人菜人,皆胜汉人,至于儒人通经书,学孔孟,汉人只是课赋吟诗,将何用!”可见元代对于儒人,并非笼统轻视。轻视的只是那些只知“课赋吟诗”的人,而对于“通经书,学孔孟”还是重视的。姚枢、许衡等人的社会地位决不在妓人之下。
元人攻宋,引起了文学上一场风波,经过十多年才恢复平静。元世祖忽必烈不重视诗词,认为吟诗作赋无用,也就不注意这些作品,所以没有人因为写诗作词受到迫害。相反的却是他还派人请这些人出来做官。只是有人肯出来,有人不肯出来。明人吴讷说:“元世祖初克江南,畸人逸士浮沉里闾间,多以诗酒玩世。元贞、大德以后稍出。”戴表元写《读书有感》说:“如今已免多人笑,老大知无欲嫁心。”拒绝征召。赵孟頫、袁桷、邓文原等接受礼聘。赵孟頫以“宋室王孙人仕,风流儒雅,冠绝一时。”他和袁桷互相唱和,“诗学为之一变。”他们这些南方人和北方的元明善、姚燧、马祖常等人一起,写诗古体模仿汉魏,律诗学盛唐,风格清丽而遒壮,开始形成南北诗风统一的格调。欧阳玄说:“承平日久,四方俊彦,萃于京师,笙镛相宣,风雅迭唱。…‘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古。”所谓金宋季世之弊,即金宋人崇奉苏黄,而宋季诗人学晚唐,这个变化标志着元代诗歌发展的新里程。
如上所言,元政府派程钜夫到江南搜访隐逸,礼聘贤才,吴澄、赵孟頫、袁桷等人相继出仕,有些剧作家也跟着北上。《录鬼簿》卷上说:“范居中,字子正,杭州人,大德问被旨赴都,公亦北行。以才高不见遇,卒于家。有乐府南北腔行于世。”他和施惠、黄天泽、沈珙合编了一个剧本叫《鹩鹩裘》。《太和正音谱》把他的杂剧列入杰作,并说:“其词势非笔舌可能拟,真词林之英杰。”评价颇高。但他没有赵孟頫等人的幸运,却“才高不见遇”,回到杭州老家。他著有乐府“南北腔”,当即南北合套,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亦有南北合套现象。南北曲的声腔是不一样的。元人徐士荣《新街曲》说:“东街南曲声婉扬,西街北曲声激昂。佳人唱曲不下楼,楼下白马青丝缰。昨日开筵击鼍鼓,今夜合席调笙簧。乐声一似曲声杂,人意岂如物意长。”一个套曲里面有两种声腔,即一会儿“婉扬”,一会儿“激昂”,这是北曲进入杭州后和南曲结合后产生的现象。北杂剧和南戏文互相影响的结果,这是~种戏剧改革的尝试,不过这种改革是一个失败的改革,所以范居中“才高不见遇”。南戏改革应是南戏吸收北杂剧一些优点,如唱曲采用联套,科诨减少,结构严密,集中刻画人物性格等等,不是南北合套,叫人听起来不谐和,破坏了审美享受。只有把《刘知远诸宫调》改为《白兔记》,关汉卿的《拜月亭》改为《月亭记》比较成功。也表现南戏的进步和发展。
元代杂剧作家参加征召失意而归,除范居中外,不见记载。但职位不振,沉抑下僚的作家却是很多的。被称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郑光祖,他的《王粲登楼》就表现一个“空学成补天才”,而“寻不着上天梯”的人牢骚不平和怀才不遇者的怨气。乔吉流落江湖四十年,宫天挺终身为人陷害而不见用,处境和郑光祖相同。乔吉除写杂剧外,散曲也写得十分出色。他说:“看遍洛阳花似锦,荣也在你;枯,也在你。”表现他一生潦倒,壮志销磨。
元朝政府征召隐逸,虽然有些人不遇而归,但总的说来还是成功的。袁士元《题寒江独钓图》说:“堪笑江湖几钓徒,朝来相唤暮相呼。只今风雪蒙头处,回首烟波一个无。”隐士们全都出仕了。后来有些人,不征召也自动北上求官。方回《再送王俞戴溪》说:“宇宙喜一统,于今三十年。江南诸将相,北上扬其鞭。书生亦觅官,裹粮趋幽燕。”被称为元代四大文学家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多数是歌颂民安物阜的,但都掌握了写作技巧,而虞集名气尤大。虞集的《风人松》词有一句“杏花春雨江南”,字句十分凝炼,当时人极为赞赏,他自己也很满意。吴师道《陈监丞安雅堂集序》说陈旅作文“用心甚苦,功甚深,藻绩组织,不极其工不止。”虞集、陈旅的文风上这种变化,当时有一种代表性,因为不只是诗文,杂剧、散曲也如此。郑光祖、张可久、乔吉等人的作品表现典雅工丽,讲究辞藻,渐渐丧失了早期戏曲中的朴野。
在虞、杨、范、揭之外,这时别树一帜的是马祖常、萨都刺。他们都是少数民族的诗人,而萨都刺的词写得尤其出色。他的[满江红](《金陵怀古》),吊古伤今,胸怀磊落,继承和发扬了苏东坡、辛弃疾以后豪放派的风格。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1-03-25
中国文学发展到元代,由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以及文学本身的种种原因,传统的诗词古文创作局限于少数文人的范围,新起来的戏曲小说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好,流行南北。诗词古文的语言风格一味模唐仿宋,有人还甚至标榜学习周秦汉魏,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曲高和寡,与那语言浅近通俗的戏曲、小说相比较就不易的人们接受。戏曲、小说的题材大都取自人民群众所关心和熟悉的生活,同时由于作者多数出身于社会中下层,他们看问题,谈人论事,也都和人民群众好恶接近,所以戏曲小说,特别是杂剧成了元代趺学创作中最受欢迎的剧艺。前人把它和唐诗、宋词并称,作为一个朝代文学艺术的代表,许多作家也享受很高的荣誉。
诗词只是在少数文人学士之问传播,散文多经世、酬世应用之作,不像戏曲小说在大庭广众的勾栏中说唱演出。戏剧演出必须争取看官听众,故事须群众喜见乐闻。因为演员和少数作者都要靠此谋生。不像诗词作者并不以写诗作词为生,多数是公余闲暇,或家有钱财,舞文弄墨,自我陶醉或者发发牢骚而已。当然也有少数人把写作诗词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不过总的说来,戏曲小说真正能做到雅俗共赏,而诗词古文却只能在官场和骚人雅士中问流传,主要是士大夫独抒怀抱或互相唱和。
一般说来,元代文学中少数诗词、古文,多数小说、散曲、杂剧、南曲戏文等等中的一个共同东西,就是或多或少反映出来了那种同情民生疾苦和抗议民族压迫的忧国忧民思想。这个思想是蒙古统治阶级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和疯狂奴役劳动人民的必然产物。但是诗词、戏剧等除开这个共同点以外,也还各有其自身的特征。文学体裁的运用,和作家的社会地位自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体裁有雅俗新旧,采用某种体裁却和作家的身份地位以及文学修养有关系。传统的诗词古文更多的被社会地位高而持有正统思想的人所选用,至于戏剧小说本不登大雅之堂,写作者大半社会地位低下而思想受到传统束缚较少。这样诗词古文是一个情调,而戏曲小说另是一个情调。惟有散曲较为复杂,它和杂剧相近,只是体制长短不同,有曲子而无科白,仅供清唱,不能上演。思想内容有时和杂剧接近,有时和诗词接近。换句话说,诗词古文的总的特点是作者多半是社会地位较高,题材偏于酬世赠答、寻亲访友和离愁别恨。反映出来的是封建社会上层人士的生活情况。有时也出现一些反映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作品。至于戏剧小说的作者一般是“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人士,作品题材也偏于人民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民间传说和普通人民日常生活。这里,作为上流人士的怡情遣兴、怨乱伤离的诗词,和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的戏剧小说,不仅是题材不同,而在内容上也有很大的区别。诗词中,官场得失和人世悲欢离合成了常见的主题,而戏剧小说中,出现了一些敢于摆脱封建道德枷锁的叛逆人物,性格泼辣明快,却是诗词中少见的。这中问散曲的情况比较复杂,普通知识分子写,达官贵人也写,多数场合是供给伎女在筵席上唱的,也就沾染上一些不健康的情感。但叹世、归隐之类的作品大量出现,却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总之,元代文学创作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中个人得丧悲欢和社会生活面貌。而由于作者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和政治地位的差异,加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复杂关系,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分别表现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理想。其中用通俗的语言描述新生的事物并以新的道德标准评价生活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文学史上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
元代文学中诗词、散文、小说、戏剧等体裁的消长变化,就文学本身说,还表现为由篇幅短小过渡到长篇巨制,由作者个人抒情,或者评论、记事变为叙事和代言。单纯诗词、单纯散文体裁之外,有诗词有散文的混合体制戏剧、小说的大量出现,这种文化充分体现新的体裁的出现比起旧体诗词、古文便于塑造完美的艺术形象和容纳深广而复杂的社会生活。
此外,元代虽然为期只有百年左右,但由于岁月迁流,人事代谢,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此起彼落,历史不断前进,文学也跟着向前发展,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也表现不同的特色。
诗词只是在少数文人学士之问传播,散文多经世、酬世应用之作,不像戏曲小说在大庭广众的勾栏中说唱演出。戏剧演出必须争取看官听众,故事须群众喜见乐闻。因为演员和少数作者都要靠此谋生。不像诗词作者并不以写诗作词为生,多数是公余闲暇,或家有钱财,舞文弄墨,自我陶醉或者发发牢骚而已。当然也有少数人把写作诗词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不过总的说来,戏曲小说真正能做到雅俗共赏,而诗词古文却只能在官场和骚人雅士中问流传,主要是士大夫独抒怀抱或互相唱和。
一般说来,元代文学中少数诗词、古文,多数小说、散曲、杂剧、南曲戏文等等中的一个共同东西,就是或多或少反映出来了那种同情民生疾苦和抗议民族压迫的忧国忧民思想。这个思想是蒙古统治阶级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和疯狂奴役劳动人民的必然产物。但是诗词、戏剧等除开这个共同点以外,也还各有其自身的特征。文学体裁的运用,和作家的社会地位自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体裁有雅俗新旧,采用某种体裁却和作家的身份地位以及文学修养有关系。传统的诗词古文更多的被社会地位高而持有正统思想的人所选用,至于戏剧小说本不登大雅之堂,写作者大半社会地位低下而思想受到传统束缚较少。这样诗词古文是一个情调,而戏曲小说另是一个情调。惟有散曲较为复杂,它和杂剧相近,只是体制长短不同,有曲子而无科白,仅供清唱,不能上演。思想内容有时和杂剧接近,有时和诗词接近。换句话说,诗词古文的总的特点是作者多半是社会地位较高,题材偏于酬世赠答、寻亲访友和离愁别恨。反映出来的是封建社会上层人士的生活情况。有时也出现一些反映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作品。至于戏剧小说的作者一般是“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人士,作品题材也偏于人民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民间传说和普通人民日常生活。这里,作为上流人士的怡情遣兴、怨乱伤离的诗词,和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的戏剧小说,不仅是题材不同,而在内容上也有很大的区别。诗词中,官场得失和人世悲欢离合成了常见的主题,而戏剧小说中,出现了一些敢于摆脱封建道德枷锁的叛逆人物,性格泼辣明快,却是诗词中少见的。这中问散曲的情况比较复杂,普通知识分子写,达官贵人也写,多数场合是供给伎女在筵席上唱的,也就沾染上一些不健康的情感。但叹世、归隐之类的作品大量出现,却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总之,元代文学创作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中个人得丧悲欢和社会生活面貌。而由于作者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和政治地位的差异,加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复杂关系,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分别表现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理想。其中用通俗的语言描述新生的事物并以新的道德标准评价生活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文学史上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
元代文学中诗词、散文、小说、戏剧等体裁的消长变化,就文学本身说,还表现为由篇幅短小过渡到长篇巨制,由作者个人抒情,或者评论、记事变为叙事和代言。单纯诗词、单纯散文体裁之外,有诗词有散文的混合体制戏剧、小说的大量出现,这种文化充分体现新的体裁的出现比起旧体诗词、古文便于塑造完美的艺术形象和容纳深广而复杂的社会生活。
此外,元代虽然为期只有百年左右,但由于岁月迁流,人事代谢,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此起彼落,历史不断前进,文学也跟着向前发展,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也表现不同的特色。
第2个回答 2021-03-12
[古代文学]元代文学汇总 (4)
第3个回答 2011-03-25
元散曲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