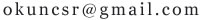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08
巫山县出土的商尊
1996年启动,是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该工程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相结合,设置9个课题44个专题,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条件。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该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计划”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该工程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验收。
编辑本段背景
夏商周断代工程
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其中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糊且又不一致,所以他便弃而不用,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年表。 第一个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学作系统研究工作的学者是西汉晚期的刘歆。刘歆的推算和研究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中,《世经》的主要内容后被收录于《汉书·律历志》。从刘歆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叶,又有许多学者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推算所用的文献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文献,所以很难有所突破。晚清以后情况有些变化,学者开始根据青铜器的铭文作年代学研究,这就扩大了资料的来源。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又为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进入20世纪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编辑本段立项过程
1995年秋,国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请在北京的部分学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宋健提出并与大家讨论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设想。 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5年底国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学院、社科院、国家教委(今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共七个单位的领导组成,会议聘请了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作为工程的首席科学家。 1996年春,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了一个由不同学科的21位专家形成的专家组,并拟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可行性论证报告在1996年5月得到了通过。 1996年5月16日国务院召开了会议正式宣布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启动。这一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共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与的专家学者达200人。
编辑本段工程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编辑本段研究课题
1.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 夏商周断代工程
2.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 3.夏代年代学研究; 4.商代前期年代学研究; 5.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 6.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 7.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 8.碳14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 9.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与总结。
编辑本段研究方法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现象和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学给予计算从而推定其年代;同时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并进行了必要的发掘,获取样品后进行碳-14测年。
编辑本段结论与意义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约开始于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都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前1046年。依据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年表和西周诸王年表。 如果该工程顺利的话,那么将有可能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给出了一个时间上的标尺,但目前看来,由于该工程的最终繁本报告迟迟未能通过,这个意义能否达到存在较大疑点。
编辑本段批评与质疑
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以后,其中结论已被不少主流的词典和教材采用,开始产生影响。 在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后,国外学者开始加以批评。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才刚刚开始,中国的考古技术和理论水平还有待更大的提高。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批评不绝于耳。某些国外人士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还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在2000~2003年进行了三次辩论。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便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但亦有人认为所谓的“国际学术界”一贯漠视中国本土研究成果,对中国历史没有发言权。 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封锁,网络上随处可以见到关于此问题的介绍与讨论,中国政府也为此展开大规模论争,提出支持自己观点的各种理据,支持工程学者深入研究。有些国外学者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努力,认为只要是中国政府支持的此类研究一定就有政治目的。有人就说,这些学者连最近发表的文字都说不清楚,他怎么可能对三代的年代行判别。而大陆不同意工程报告的学者也被这些国外学者加上“正义凛然”的标签,说成是“无力对抗政府”。 工程的成果是否失败,现在还没有强有力的论据证明。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例如张培瑜的研究,但工程内部却是存在争论。有些中国学者认为,此类工程的成果没有必要非得通过世界上各种具有“复杂背景”的学者的检验,只要在中国学术界取得共识就行,中国学者对历史的研究无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种目的的势力阻挠。
编辑本段工程的价值
首先,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了夏商周的一个大致年表对于今后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作为阶段性成果本来就不是最终结论,通过讨论有益于学术进步。其次,大量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使得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在技术层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多学科的共同研究有利于考古学这个交叉学科的发展。第三,人文社会学科学者作为国家级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在中国是第一次,其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最后,高规格的工程以及广泛的学术讨论,特别是大幅的宣传力度,对于普及历史、考古等知识也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编辑本段关于周懿王元年天再旦的质疑
在“东亚历史”[1]期刊(East Asian History)上,Douglas J. Keenan发表文章质疑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是西元前899年[2]。文章中对于工程研究方法中的错误提出了具体质疑。文中提到: ……一些最近的研究计划,包括被中国国务院接受的研究计划(指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的是一个在西元前一千纪早期的“天再旦”的记载。这些研究把这个奇特的记载解读成日出时的日偏食。这样的解读看起来似乎合理(黎明要开始之际,天色因为日食而暗下来,然后再日出),但却是不确定的。日出时把太阳表面遮住的部份大到可以让天色大幅变暗的日食是很少的。在西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确是有一次日出时日食,而这些研究计划把这个日食对应到该奇特的记载(指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计算显示,西元前899年的那次日食把主观亮度(人类观察者所感受到的亮度)减低的程度小于25%。为了证明这样的亮度减少可以给观察者有“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一些研究者对观察了1997年日出时日偏食的观察者进行了调查。然而,所有的观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不到10%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观察者没有“天再旦”的感觉),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超过80%的地方(这些地方有(指天再旦的感觉))。从这些数据,研究者作出结论,“主观亮度减少超过10%会造成“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这个结论根本毫无根据。实际上,飘过的云常常可以造成主观亮度减少25%…… 另外,该文也质疑了对于该次日食的计算的正确性。 另外,有人依据《日食路线图》作了调查,发现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带西端在山东省,陕西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郑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像。
编辑本段蒋祖棣对工程方法论的批评
2003年4月12日,在芝加哥就断代工程进行了一次学术会议,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祖棣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只有68.2%的置信度,“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编辑本段工程争议
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批评就不绝于耳。国际上有人评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还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学术上的批评也不断提出。“工程”的《简本》公布后,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2000年11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2003年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学者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而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有学者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1996年启动,是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该工程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相结合,设置9个课题44个专题,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条件。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该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计划”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该工程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验收。
编辑本段背景
夏商周断代工程
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其中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糊且又不一致,所以他便弃而不用,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年表。 第一个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学作系统研究工作的学者是西汉晚期的刘歆。刘歆的推算和研究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中,《世经》的主要内容后被收录于《汉书·律历志》。从刘歆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叶,又有许多学者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推算所用的文献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文献,所以很难有所突破。晚清以后情况有些变化,学者开始根据青铜器的铭文作年代学研究,这就扩大了资料的来源。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又为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进入20世纪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编辑本段立项过程
1995年秋,国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请在北京的部分学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宋健提出并与大家讨论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设想。 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5年底国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学院、社科院、国家教委(今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共七个单位的领导组成,会议聘请了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作为工程的首席科学家。 1996年春,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了一个由不同学科的21位专家形成的专家组,并拟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可行性论证报告在1996年5月得到了通过。 1996年5月16日国务院召开了会议正式宣布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启动。这一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共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与的专家学者达200人。
编辑本段工程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编辑本段研究课题
1.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 夏商周断代工程
2.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 3.夏代年代学研究; 4.商代前期年代学研究; 5.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 6.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 7.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 8.碳14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 9.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与总结。
编辑本段研究方法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现象和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学给予计算从而推定其年代;同时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并进行了必要的发掘,获取样品后进行碳-14测年。
编辑本段结论与意义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约开始于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都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前1046年。依据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年表和西周诸王年表。 如果该工程顺利的话,那么将有可能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给出了一个时间上的标尺,但目前看来,由于该工程的最终繁本报告迟迟未能通过,这个意义能否达到存在较大疑点。
编辑本段批评与质疑
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以后,其中结论已被不少主流的词典和教材采用,开始产生影响。 在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后,国外学者开始加以批评。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才刚刚开始,中国的考古技术和理论水平还有待更大的提高。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批评不绝于耳。某些国外人士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还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在2000~2003年进行了三次辩论。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便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但亦有人认为所谓的“国际学术界”一贯漠视中国本土研究成果,对中国历史没有发言权。 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封锁,网络上随处可以见到关于此问题的介绍与讨论,中国政府也为此展开大规模论争,提出支持自己观点的各种理据,支持工程学者深入研究。有些国外学者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努力,认为只要是中国政府支持的此类研究一定就有政治目的。有人就说,这些学者连最近发表的文字都说不清楚,他怎么可能对三代的年代行判别。而大陆不同意工程报告的学者也被这些国外学者加上“正义凛然”的标签,说成是“无力对抗政府”。 工程的成果是否失败,现在还没有强有力的论据证明。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例如张培瑜的研究,但工程内部却是存在争论。有些中国学者认为,此类工程的成果没有必要非得通过世界上各种具有“复杂背景”的学者的检验,只要在中国学术界取得共识就行,中国学者对历史的研究无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种目的的势力阻挠。
编辑本段工程的价值
首先,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了夏商周的一个大致年表对于今后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作为阶段性成果本来就不是最终结论,通过讨论有益于学术进步。其次,大量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使得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在技术层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多学科的共同研究有利于考古学这个交叉学科的发展。第三,人文社会学科学者作为国家级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在中国是第一次,其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最后,高规格的工程以及广泛的学术讨论,特别是大幅的宣传力度,对于普及历史、考古等知识也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编辑本段关于周懿王元年天再旦的质疑
在“东亚历史”[1]期刊(East Asian History)上,Douglas J. Keenan发表文章质疑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是西元前899年[2]。文章中对于工程研究方法中的错误提出了具体质疑。文中提到: ……一些最近的研究计划,包括被中国国务院接受的研究计划(指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的是一个在西元前一千纪早期的“天再旦”的记载。这些研究把这个奇特的记载解读成日出时的日偏食。这样的解读看起来似乎合理(黎明要开始之际,天色因为日食而暗下来,然后再日出),但却是不确定的。日出时把太阳表面遮住的部份大到可以让天色大幅变暗的日食是很少的。在西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确是有一次日出时日食,而这些研究计划把这个日食对应到该奇特的记载(指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计算显示,西元前899年的那次日食把主观亮度(人类观察者所感受到的亮度)减低的程度小于25%。为了证明这样的亮度减少可以给观察者有“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一些研究者对观察了1997年日出时日偏食的观察者进行了调查。然而,所有的观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不到10%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观察者没有“天再旦”的感觉),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超过80%的地方(这些地方有(指天再旦的感觉))。从这些数据,研究者作出结论,“主观亮度减少超过10%会造成“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这个结论根本毫无根据。实际上,飘过的云常常可以造成主观亮度减少25%…… 另外,该文也质疑了对于该次日食的计算的正确性。 另外,有人依据《日食路线图》作了调查,发现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带西端在山东省,陕西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郑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像。
编辑本段蒋祖棣对工程方法论的批评
2003年4月12日,在芝加哥就断代工程进行了一次学术会议,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祖棣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只有68.2%的置信度,“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编辑本段工程争议
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批评就不绝于耳。国际上有人评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还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学术上的批评也不断提出。“工程”的《简本》公布后,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2000年11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2003年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学者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而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有学者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11-03-05
我要是有证据我就不用来回答你了·我直接可以去争取国家级科研资金了!
相似回答